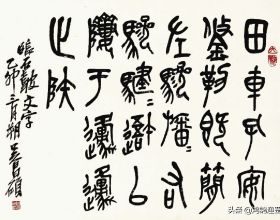秋天,是浪漫的結婚季。國慶假期,我連著幾日,參加了同學的喜宴,或嫁女兒,或娶兒媳。在眾多婚禮的現場,有一幕情景,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主持人說:“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送父親。”父親擁抱了女兒後,轉身緩慢走下舞臺。
我看見一襲潔白婚紗的女兒,回過頭來,依依不捨目送著父親的背影離去。那一刻,我被感動了,熱淚在她激動的臉上,閃耀著淚花,這淚花,是反哺跪乳的感恩,是朝夕相處的不捨,是一生濃濃的牽掛。從此父親是孃家,不再小手相牽,不再舉抱於肩,不再呵護左右,不再百般疼愛。新娘這顆激動的淚,也深深流進了我的心裡,我在現場差點潸然淚下。
我不是父親,沒有送女兒出嫁的體驗,但是此景,卻讓我想起了我的父親,想起了幾十年前的那次婚禮。
出嫁的是我妹妹。回憶起來挺寒酸的,經濟不景氣的年代,又趕上全國性的下崗潮。記得當時的婚禮標準,婚車上了三輛到四輛,就算挺洋氣的了,一色桑塔納開道,至於大奔、寶馬就甭想了,整個城市都沒有一輛,租都沒地兒,婚紗店也沒道具。
那年代根本不興預備餐,和衍生出的展望餐或回味餐,更不流行惡俗的婚鬧。結親那天,把大門一關,婚車還未到,隔壁四鄰就開始熱鬧起來。“結婚了,結婚了。”鄉情象爆竹一樣點燃。
“開門開門,接親的來噠。”
鄰居在屋外也幫著喊:“接親的來噠,開門開門。”屋裡也喊:“開門開門。”不過喊的卻不一樣:“紅包先行,敬哈門神。紅包不行,心意不誠。”一陣哈哈哈,一條白沙煙從門框上塞了進來。
接親時,我的任務是背妹妹出嫁。一進屋,妹夫就拉著妹妹,雙雙朝父母親跪下,行跪拜大禮。我看見老實巴交的父親,突然哭了起來,聲音越來越大,勸都勸不住,一邊哭,一邊自己用手揩眼淚。妹妹也含著熱淚,拉著父親,這倒是我沒有想到的。起初,我以為母親會哭,沒想到父親倒搶戲了。
“你爸當然哭了。”母親後來揭開了答案。原來,妹妹出生時,不止一個降生,而是喜得雙鳳。雙喜臨門,本來是家中大喜事,卻因突染疾病,囿於醫療條件有限,只保住了其中一個,而剩下這一個,也是從小身體孱弱難養,一路提心吊膽,讓父母擔心不已。
有一回夜裡,妹妹生病發高燒,赤腳醫生要幾根土方荷梗做藥引。父親便跑到池塘裡去撈荷梗,這一去不打緊,父親差點沒回來。他划著腳盆,在池塘裡深一腳淺一腳地划行。腳盆看似簡單,其實複雜去了,沒有劃過的人,常誤以為自己能劃。腳盆晃晃悠悠劃到池塘中央,父親夠著身子去抓荷梗,誰知重心一歪,父親就慌了,不知道怎麼調整平衡度。父親掉下去的時候,腳盆還在水面上晃悠著,不肯離去。不會游水的父親,先是撲打水面,漸而沉到水裡,露出一串串氣泡,像是向岸上發出緊急求救的訊號。
老天到底給了父親一線生機。一個路過的行人,跳進池塘,救起了他。喝了一肚子水,只有半條命的父親,差點讓襁褓中的女兒,和一大家子,做了可憐的戴孝人。
往事如鯁在喉,女兒這一跪,讓父親百感交集,一開口聲音就有些發顫,哽咽不住,眼淚嘩嘩的流著,竟然當著大家的面,失聲痛哭起來。鄰居開始勸他:“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當爸的怎麼能哭呢,熱熱鬧鬧,把妹丫頭送出嫁。”
母親揩眼淚,妹妹也哭起來。
我蹲下去,背起妹妹,起身朝門外婚車走去,送妹出嫁。說起來,心裡其實挺憋屈,挺難受的。我那時忙忙碌碌,一事無成,妹出嫁,也沒什麼賀禮,做哥的,沒什麼本事,只有臨出門的這一背,算是大禮,給妹妹踐行了。後來到了席上,一個人喝著悶酒,越想越難過,妹妹的喜酒,喝了七八杯,一顆心酸禁不住掉了下來。
如今,父母早已離去,我雖已成家多年,可作為丁克一族的我,註定此生,體驗不到父親那份嫁女的心情了。
我默默的用紙巾擦了擦眼眶,起身去趕下一個婚禮。
臺上,新娘含著淚,目送著父親的背影離去。(文/宗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