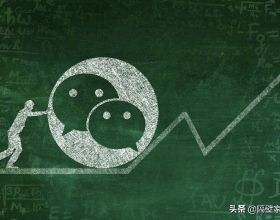"
香港跑馬地賽馬場,位於香港島中心位置,每到賽馬日,賽馬場上進行著一場場賭馬狂歡。視角翻轉,賽馬場地下則是另一翻景象。這裡住著一群來自全球各地的流浪漢,他們在此搭建屋棚,將生活攤開在地下通道。
10月27,香港賽馬日。傍晚,一輛輛載著名貴馬匹的箱式貨車,陸續開往香港跑馬地賽馬場,準備迎接夜晚持續四個小時的賭馬狂歡。
跑馬地賽馬場是香港第一個賽馬場,位列全球最先進的賽馬場之一,可容納35000名觀眾同時觀看比賽。它位於香港島的中心位置,又名快活谷馬場,馬場包圍在高樓大廈之中,夜色璀璨,景色迷人,是很多當地人夜晚觀看馬賽的首選。
場內駿馬奔騰,英姿颯爽,場外萬人喝彩,聲勢響徹夜空。然而,賽馬場下方則上演著另一番“人生戲碼”。來自全球各地的流浪者,聚集在這個大概150米長的地下道里,他們安家在此,生活被摺疊在這個繁華都市的狹長空間。
圖 | 馬場地道入口
無論跑馬場內多麼喧譁,聲音都能被地下道上方厚重的水泥天花板隔絕,彷彿是互不干擾兩重世界。
地下道打頭的一戶是娜琳家,她是泰國人,家有“開放式客廳”。一個陳舊而乾淨的藍色沙發,一張白色矮方桌,一把摺疊椅,它們緊貼著地道西側牆壁依次擺放。最令人矚目的是,白色矮方桌上有隻花瓶,裡面插著新鮮的玫瑰花。
圖 | 娜琳家開放式客廳
“開放式客廳”對面立著一臺冰箱,因為沒有外接電源,一直沒法用,成了裝飾品。客廳隔壁,是一個用木板圍成約3平方米的“小院子”,愛乾淨的娜琳特意安了一扇30公分高的小鐵門,在門口鋪一塊布當作地墊,進院要脫鞋。
與地下道里的其他流浪者相比,娜琳生活最講究,家當最為齊全,佈置也最亮眼。每每有人經過,都會忍不住多看兩眼。她不像是在流浪,而是在認真生活。
初次見到娜琳,她正坐在沙發上乘涼,看上去五十歲左右,身穿咖啡色短袖上衣,白色短褲,露出又黑又細的腿。看我走進地下道,娜琳向我微笑,眼角的魚尾紋略顯滄桑,她用帶口音的粵語和我打招呼。
我誇她綠植養得好,家裡很乾淨,真會過日子。她回:“我經常打掃,不希望影響到路過這裡的行人。”
八年前,娜琳帶著兒子從泰國來到香港謀生。她做過按摩師和保潔員,因為收入不穩定,付不起每月四五千的超高房租,母子倆早早成了“馬場地道”的住戶。一年前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她任職的酒店幾乎沒了生意,老闆大裁員,娜琳失業了。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包容性很強,但競爭壓力也很大。她每天都去找工作,因為年齡大,沒什麼學歷,廣東話說得不太流利,英語也很一般,於是一次次吃閉門羹。她兒子20出頭,同樣沒有固定工作。我見過他一次,戴副眼鏡,斯斯文文的,騎著一輛山地車在地下道里穿行。
目前母子二人的生活來源,一部分要依靠慈善機構。香港有很多慈善機構,大多是宗教組織設立的,也有私人創辦的,慈善機構用籌募來的資金建流浪者之家,但位置有限。所以他們經常定期到流浪者聚集點,派發食物和生活用品。
失業後的娜琳依然在地下道里積極生活。她每天會長時間待在地下道,為兒子準備一日三餐。她身後一米高的櫃子裡,整齊碼放著果汁、咖啡和調料,還有五顏六色的乾麵條團。爐灶和炒鍋架在長桌上,她常常用鍋煮麵條,再炒個青豆火腿腸。
圖 | 娜琳家的爐灶和炒鍋
這些食物有的是慈善機構免費派發的,有的是她兒子打零工掙錢買的。
住在娜琳旁邊的鄰居很神秘,我從未見過她。她用白色紙板圈了個院子,黑色蕾絲內衣晾曬在院子裡,每次經過那裡,我總在想,內衣會不會誘發流浪漢侵犯主人。但娜琳告訴我,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生活地下道里人,他們互不打擾,也互不關心他人。這不算冷漠,他們為了應對自己的生活,就已經花光所有力氣。
“至少生活在這裡很自由。”白髮蒼蒼的印度老婆婆對我說,她走路略微弓腰駝背,說英語絲毫不帶印度口音。她一邊把五六個盛滿水的塑膠桶擺放整齊,一邊告訴我,這是她從跑馬地外的公共衛生間裡接來的水。雖然只有幾百米的路程,來來回回好幾趟,她看上去已精疲力盡。
印度婆婆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已經忘記哪年來的,也不願透露此前的經歷,又是怎麼成為流浪者的。在地下道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果對方第一次不願說,那就永遠不可能知道。
印度西部是10月底過印度新年,共持續5天。白天,來自印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單身男子,會到距離地下道50米的印度錫克廟吃免費的餐食。錫克廟的免費餐食所有人都可以吃。夜晚,他們到錫克廟參加慶祝活動,載歌載舞。結束後,他們回到地下道,撐開各自的旅行帳篷,鑽進去睡覺。
那天我碰見印度婆婆,祝她新年快樂。她笑著說,有錢天天是新年,沒錢新年和自己也無關。那幾天錫克廟舉辦活動,印度婆婆一次也沒參加。
幾年前,我從內地來香港工作,賽馬場地下道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地。不賽馬的時候,跑馬場是個運動場,可以跑步,踢足球場,打曲棍球。下了班,我常途徑地下道,到跑馬場上跑步,因此經常會與住在這裡的流浪者們交流。
“馬場地道”的設計初心,是為了在喧鬧的賽馬日分流觀眾,並不是為了行人通行。除了每週三的賽馬日,平時少有行人路過。這恰好為流浪者提供了在此安營紮寨的有利條件,此地常年居住著不同國籍的流浪者,是香港露宿圈中小有名氣的“聯合國村”。
圖 | 馬場地道一角
這裡並非是個無人監管的安樂窩。香港警察會不定時到訪此地,抽查流浪者的身份證明,證件合法且沒有窩藏違禁品,就可以繼續居住。前提是,要自覺靠西側安家,面積大約佔據地道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約有一米二寬,足夠行人透過。
每逢酷暑、冬天或是颱風天,特區政府都會開放社群中心,讓流浪者留宿。但一年中這樣的日子為數不多,他們去過幾次便不願再去,彷彿地下道才是他們長久的歸宿。而且一旦離開,他們的領地很可能會被其他流浪者佔領。
“公園地道”緊鄰“馬場地道”,與其平行。比起“馬場地道”,它行人太多,而且長度相對較短,很少有流浪漢在這住。越南仔是唯一常年盤踞在此的流浪漢。
10月13日,颱風“圓規”逼近廣東沿海一帶,香港天文臺掛出代表風力第二大的8號風球,全港停工停學。戶外狂風暴雨,地道內也淅淅瀝瀝“下”著小雨。雨水滴落在越南仔的床墊旁,他毫不在意,依舊坐在床墊上,目視過往行人。
因為他是地道的老住戶,很多人都關注他。我拿出蘋果和八寶粥遞給他,他極不耐煩地擺擺手:“不要打擾我,把你的東西拿走。”我試圖瞭解他的意願就這麼被拒絕,之後再也沒能走進他。
2020年以前,越南仔“物料豐厚”,家當有沙發、床墊、鍋碗瓢盆和鞋架,他喜歡用衣架把十來件衣服和毛巾掛起來。去年年初,越南仔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但他的衣服和家當依然在。不明所以的行人和志願者,在他床鋪上擺了口罩,送他嶄新的棉被,甚至還有盒飯。
然而越南仔遲遲未現身。時間久了,他的家當每天都在減少,鞋架和衣服不翼而飛,炊具和餐具也不見了蹤影。有一天他突然出現,腦袋上包紮著繃帶,而他的家當只剩沙發和床墊。
沒人知道他消失的這段時間經歷了什麼,除了陳老伯。“他是被印度人揍了”,年過七旬的陳老伯神秘兮兮地告訴我。陳老伯是緬甸人,生活以規律和節儉著稱。一年多以前,陳老伯從位於上水的北區公園,搬到25公里外的馬場地道生活,每天早晨5起床,晚上8點睡覺。
圖 | 陳老伯
跑馬地一帶物價偏高,剪髮、自助洗衣房等都相對較貴。於是,陳伯每天用八達通老年卡花兩塊錢坐公交車,到25公里外的上水北區公園。他在那裡洗漱、做飯、洗衣服,做好飯再帶回馬場地道吃。
上水北區公園屬於新界地區,靠近深圳,但無他容身之地。他骨子裡認為,馬場地道才是他的家,“因為這裡白天可以睡覺,沒人管”。不睡覺時,他常捧著書看,從佛經到禪學,吸引過往行人的目光。這些書大部分是宗教團體免費送的,有時他也看免費派發的報紙。
陳伯生於緬甸,兒時父親離家出走,他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青年時他輾轉於昆明和瑞麗,曾在昆明蹲過監牢,1974年他回到緬甸尋找父親,又因偷渡被關進仰光的監獄。1988年被釋放後,他回到昆明短暫工作了幾年,1991年來到香港,靠打零工生活,直到無法做任何體力工作。
老人家強調,他談過兩個女朋友,都是原來在超市工作時候的同事。“為啥分手?”“她們嫌棄我流浪街頭。”他從不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目前他的生活並不算特別貧困,每月能領3800塊生果金過活,花銷大概在1500塊,還能存點錢。
“地道里會有人偷錢嗎?”“錢在銀行,偷不走,我前兩天新買的鞋子倒是被人偷走了。”
有時,陳伯的話天馬行空。我問他是否擔心新冠疫情,有沒有打疫苗?他說:“沒打,我對病毒有自己的認識,那是一種來自外太空的病毒。”最後一次聊天,他偷偷告訴我,香港一直有人盯著他。他說自己是軍事奇才,過幾年要申請去俄羅斯,在那才能發揮他的軍事才能。
保障流浪漢的生活空間,前提是不能犧牲行人的利益,不能影響通行,還要搞好衛生。地下道也有衛生保障,每週二和週五夜晚,都會有清潔工沖刷地下道的各個入口,另外還有每半年一次的大清洗。
早在兩天前,食物環境署和民政事務處貼出清洗地下道的通告:“清洗會沾溼隧道內的所有雜物,請立即清理屬於你的物品。”
圖 | 食物環境衛生署示
一條几十米長的水管,由地面伸進地下道,水流開始在牆壁和地面鋪展開來,肆意流淌。旁邊的政府工作人員,繼續勸說常年盤踞在此的流浪者們:拆掉包裹窩棚的帆布、門板和床單等物品,以防沾溼。
陳老伯正仔細摺疊剛剛收起的帆布。不遠處,阿誠護著自己用紗帳篷、單人床和紙板組成的“安樂窩”。
阿誠45歲,是香港本地人,有正經工作,也有穩定的收入。他是揀貨員,每天步行1公里,到灣仔的一家倉庫上班。一週開工五天,每天工作約十個小時,月入一萬三千港元。
像阿誠這樣有工作和收入的香港本地流浪漢,在地下道里比較罕見。他並非是租不起房,而是為了省錢,暫住在這裡。
大約一年前,他租住在油麻地約5平方米的劏房,劏房住戶密集,他擔心病毒傳播,索性搬離。搬到“馬場地道”生活,他覺得自己揀到了便宜,原先月租3500港元的劏房,不如免費的地下道住著寬敞。除此之外,他每個月還能省下400港元的通勤費。
圖 | 阿誠和他地下道的家
不久後他將擁有自己的房子,這是他眼前能看到的最大希望。“我排了六年公屋(類似內地的廉租房),還有兩年就能輪到了。”他還沒談過女朋友,計劃分到18平方米的公屋後(公屋面積大小根據居住人數來定),再談戀愛,娶妻生子。
阿誠老家在廣東羅定,爸媽早年來香港打拼。爸爸是西餅師傅,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弟弟在香港出生。15歲那年,阿誠從羅定來到香港與爸媽團聚,在香港唸書。因為英語跟不上,他從曾經連跳兩級的尖子生,落到與大學無緣的下場,早早步入社會。
而他弟弟卻很成器,考大學,當老師,結婚生子,人生一路順風順水。
其實也沒那麼順利,香港年輕人結婚生子的壓力不比內地人小。弟弟有了小孩,生活不堪重負,便帶著老婆孩子搬回父母家,住在一套50平方米不到的公屋裡。阿誠不願繼續擠在這個七口之家,選擇自立門戶。
從住公屋到租房,再到住地下道,對他來說並不是一種淪落,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每天晚上10點,阿誠總會坐在一把帶滾輪的綠色靠背椅上,專心致志地玩手機遊戲,直到深夜才睡。次日早晨8點起床後,他會溜達到跑馬地浴室洗漱,再換上一身乾淨衣服去上班。
“你住地下道會擔心被同事瞧不起嗎?”“不會,同事們的經濟狀況和居住條件都差不多。”
阿誠透露,當了50年西餅師傅的父親,有一筆不菲的退休金。“你爸爸這麼有錢,還讓你睡地下道?”“爸爸的養老錢和我沒有關係,我只是在這裡輪候公屋,又不是一輩子待在這。”阿誠強調,他的未來絕不會在地下道,語氣十分堅定。
每逢週三賽馬日,跑馬地熱鬧沸騰,馬場裡的賽道上,騎士策馬揚鞭。投注站里人頭攢動,不同膚色的人群搶著下注,阿誠偶爾充當其中的一員。賭博對他來說並不意味著對生活還有更多希冀,僅僅是一種社交方式。
“不賭馬、不買六合彩,就缺少和同事的共同語言,會被人瞧不起。”今年中秋節,六合彩推出的頭獎高達8000萬獎金,阿誠興高采烈地選了幸運數字,像往常一樣沒能中獎。“頭獎真有人中,可惜不是我,就當做慈善咯。”
大清洗過後,除了工作人員帶走無人認領的雜物,地下道又恢復了我初見時的模樣。每一次大清洗,地下道的“家當”都會消失一些,主人也不知去向,沒人會過問。很快,又會搬來其他流浪漢,家當沿著地下道西側依次排開。
無論地下道住了多少人,始終沒有過熱鬧非凡的氛圍,互不打擾是他們共同預設的生活方式。
颱風來的那幾天,他們一般都不會選擇外出,是地下道里人數最多的時候。有手機的流浪漢抱著手機玩,沒手機的則睡覺,地下道里會傳來此起彼伏的呼嚕聲。聲音連成一片,撞到頭頂上方厚實的水泥天花板,在空曠的地下道里迴響。
- END -
撰文 | 林曉寧
編輯 | 吳 尋
(摘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