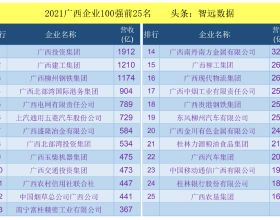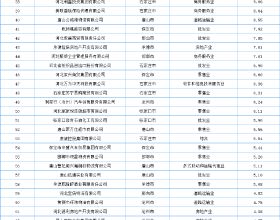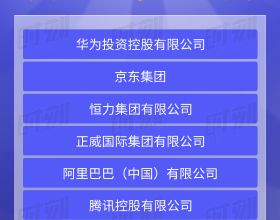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一七九六年二月九日),八十六歲的乾隆帝弘曆照例早起,於夜半子刻走進養心殿東暖閣,舉行一年一度的“元旦開筆”。這是一個私密的祈願儀式,為乃父胤禛所創,參與者僅皇帝一人。
此前兩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中,未見有其他王朝的帝王這麼做,隆冬時節,光是這份午夜起床就大不易。
皇帝開筆之處,在東暖閣明窗前,紫檀長案上,一應法物已擺設停當:象徵疆域安寧的“金甌永固杯”,注滿屠蘇酒;雕漆龍盤中盛放八趾吉祥爐和香盤,散溢著蘭麝之氣;專用的玉燭晶瑩剔透,要由當今聖上親手點燃;正中鋪展著御用黃箋,一側的筆架上,是那管皇帝專用的“萬年枝”。
又到了大清皇帝新年開筆的莊重時刻。
這是弘曆第六十一次為即將到來的一年祈福
這是弘曆第六十一次為即將到來的一年祈福,幾個時辰後他就要禪讓帝位,濡墨運筆,應是浮想聯翩。
元旦開筆,又叫“元旦試筆”“元旦舉筆”,本為流行於讀書人中的一種年俗,即在進入新歲之始,寫下心中對本年度的願望,多不外科場順遂、連捷進士之類。胤禛登基後政治局面複雜,內廷爭鬥激烈,外朝議論紛飛,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一個多月後改元雍正,新紀元的第一天,胤禛夜不能寐,於子時披衣而起,走進養心殿東暖閣,提筆書寫心聲,除“五穀豐登”“民安樂業”之類吉祥套語,更為主要的是對政通人和的殷切期盼。從那之後,誕生了一個程式極簡的宮中儀式——元旦開筆。
雖說是年復一年陳陳相因,乾隆帝對元旦開筆還是極其重視的,終其一生,持之以恆。
去年九月初三日,冊立皇太子並宣佈明年元旦舉行禪讓之後,乾隆帝即將顒琰領至養心殿東暖閣,講述元旦開筆的由來和意義,並演示一整套儀節。那是一個父子獨處的溫馨時刻,也是皇位傳承的一道序幕,多年後嘉慶帝追憶及此,仍是點滴在心。
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清朝歷史上唯一的禪讓大典即將舉行,弘曆的感受自會與往年不同。
老皇帝將筆毫在香爐上燻一燻,先以硃筆寫下“六十一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萬事如意”;再換墨筆,於左右各書八字:“三陽啟泰永珍更新”,“和氣致祥豐年為瑞”。仍舊是乾隆年號,仍是那延續了三十多年的二十八個字。
這之後,顒琰鄭重接過那管萬年枝,一筆一畫,將父皇所書內容恭謹照錄一遍。此事雖不列入禮典,卻是宮中迎新第一儀式,然後才是到奉先殿、堂子等處行禮。此刻的弘曆父子,還是皇帝與太子的關係(幾個時辰後便是太上皇帝與皇帝),以同樣的吉祥文字,迎接丙辰年的到來。
有意思的是,這兩份當年分別秘藏的御筆黃箋,歷經劫火,竟然儲存完好:乾隆帝在書寫時顯然有些手腕顫抖,筆畫時見潦草,“旦”和“良”幾乎粘連重合;顒琰所題則工工整整,端莊中略顯拘謹。所不同的僅僅在於年號,弘曆題為“乾隆六十一年”,顒琰寫的則是“嘉慶元年”。
同一時期出現兩個甚至更多的年號,在我國曆史上多有之,而父子交班、明確禪讓之後仍如是者,此為唯一一例。這當然是太上皇帝的意思,顒琰遵照父皇之旨書寫。不獨禪讓伊始,以後的三個大年初一,都是如此。
根據已有程式,弘曆與顒琰寫畢,會親手將吉語紙條摺好密緘,將所用法物一一收拾起,交與所司密存。內務府恭進當年時憲書(即大清曆書,因避弘曆名諱改稱)。
同一時期出現兩個甚至更多的年號,在我國曆史上多有之,而父子交班、明確禪讓之後仍如是者,此為唯一一例
兩處元旦開筆,兩本新歲曆書,一個新的、政治結構特殊的歷史時期就這樣開始了。
此時,被史學家稱為“偉大時代”的十八世紀正接近尾聲,工業革命帶給世界的鉅變已然顯現,歐美幾位大國之君的命運也是可嘆可嗟:
法王路易十六,已在三年前的大革命浪潮中人頭落地(馬嘎爾尼所攜帶的英王致乾隆帝信函中,特地提到此事,弘曆在詩文諭旨中雖無隻字提及,心中卻不可能沒有一點兒震動),新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血雨腥風,另一個皇帝拿破崙正在軍事和政治舞臺上初露頭角;
英王喬治三世,正被間歇性精神病所折磨,王室頗有幾分式微,而議會主導的英國已顯現出相比於君主獨裁的體制優越性,最先得受工業化帶來的實惠,綜合國力急遽增長;
俄國的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大帝,開疆拓土,雌心也勃勃,剛剛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了波蘭,目光已經開始掃視東方,卻在這一年的冬月遽然辭世;
獨立未久的美國仍在國基初肇、百廢待興的艱難過程中,離強盛還有很長的路。開國總統華盛頓堅辭第三次參選,要回他魂牽夢繞的弗農山莊,也為國家的民主體制開創一個先例……
此時距英國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還有約四十五年,歐洲列強互相攻伐纏鬥,尚無暇東顧,對於清朝仍可稱較好的戰略機遇期。設若大清君臣變革圖強、內外兼修,努力追趕西方列強的發展步伐,中國的歷史、世界的近代史或將改寫。在馬嘎爾尼的使華回憶錄中,記載了乾隆帝對英國最新軍艦模型的關注,不知這算不算一次開眼看世界?
“偉大時代”的十八世紀正接近尾聲,工業革命帶給世界的鉅變已然顯現
令人遺憾的是,禪讓時期的清廷,不管是上皇還是皇上,包括樞閣重臣,基本上缺少全球視野,缺少對西方世界的深刻了解,也缺少應有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暮氣常是與牛氣相伴生的。大清君臣動輒以“天朝”“天子”自居,不知或不願正視世界格局的鉅變,不知或不願承認列強崛起與自身衰微,無視“天外有天”的事實。
禪讓時期,朝廷的政治結構是複雜和微妙的。
《禮記·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說的是封建王朝的普遍規律。
乾隆帝早早就在設計禪讓,期望用最恰當的方式傳承帝位,應說有著一份難得的清醒。而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居於道德的最高點,做古今完人,成萬世典範,在其心中或超過區區皇位。弘曆曾認真梳理過中國歷史上的禪讓,對皇位傳承有著獨特的思考和實踐;其“歸政”之說的奧義、“訓政”之議的提出,也應一一辨析。
乾隆帝曾嚮往在禪讓後頤養天年,早早就在大內東區建好了寧壽宮,那是一個富麗堂皇的龐大宮殿群,是他設想的退養讀書的樂土。但越是抵近“歸政”之期,他思想和語言上的變化就越大。其間有對權力的留戀,有寵臣和珅等人順勢進言,而更主要的是國家出現了嚴重危機。
嘉慶元年的清朝,雖無大的外患,然內亂已殷:苗疆之變還未完全鎮壓下去,鄂川陝三省的白蓮教又復揭竿而起,東南沿海的海盜也越發橫肆無忌。這些都造成較大區域的災難,都與官府的貪腐疏縱和無能相關,又絕非此一二端所致。王朝的盛衰自有一種內在規律,以小喻大,清廷亦如曹雪芹筆下的賈府,赫赫揚揚已逾百數十年,外面的架子雖然未倒,內囊卻已經盡上來了。
嘉慶元年的清朝,雖無大的外患,然內亂已殷
弘曆特色的禪讓為期三年零三天。
如果說大清運勢在乾隆中期已盛極而趨衰,此時則是急遽跌落。對於這些,最高統治者並非懵懂不識。禪讓大典當日下午,已稱上皇的弘曆前往寧壽宮,在樂壽堂題寫了一首詩,中有這樣一聯:
付憂與子詎忘付,寧壽斯身敢即寧?
明明是一個喜慶盛大的日子,老皇帝的詩竟這般色澤沉鬱;明明付與兒子一個皇帝寶座,卻稱為“付憂”,並表示不敢完全置身事外。這才是真實的弘曆,才是他的心聲。
對於一個有責任感的帝王,皇位往往意味著擔當,意味著更多的操勞、更多的憂患。在詩中,上皇述說二十年前就已做好禪讓準備,也為歸閒娛老建好了宮苑,如今心願得償,卻不能忘記責任,不能把重擔都壓到子皇帝肩頭,也不敢去寧壽宮頤養天年。歸政,本是要“付憂與子”,安享晚年;而訓政,“大事還是我辦”,則應視為一種傳承和擔荷。
歷史永珍是繁複斑駁的,弘曆的性情做派常也如多稜鏡一般,然以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為主。翻閱史籍和檔案,尤其是讀其御製詩篇,能見出上皇時時憂心國事,最後三年生活得並不輕鬆。
乾隆寧壽宮戲臺
作為子皇帝的顒琰也不輕鬆。在顒琰心中,在他主持日常政務的過程中,父皇仍是那唯一的太陽。三年禪讓期間,父慈子孝,即使在筆記野史中,也找不到幾條父子猜忌的例子。軍政大事概由父皇決定,而釋出時多以皇帝的名義,這就是訓政,類乎“學習行走”,也可視作一種特殊的“授受”方式。顒琰才略平庸,然天性純孝仁厚,一直儘可能地陪伴父皇,儘可能地與父皇分憂。這裡面當然有敬愛謹畏的因素,而更多是出於孝心,發乎天然。
還有一個不能迴避的人物,就是深受上皇倚信,被稱為權臣和“二皇帝”的和珅。在英察果毅的乾隆帝治下會有權臣嗎?如果有,則乾隆晚期的和珅算是一個,其也的確有不少弄權貪賄之舉。禪讓的三年,和珅一步步到達仕途的頂峰,成為首輔和首樞,主管著六部中的吏部、戶部和刑部,呼風喚雨,固一世之雄也;而弟弟身死,愛子夭折,髮妻病逝,自己深受腿疾折磨,他也只能默默承受。和珅的寵遇和一路飛昇,主要來自他精通逢迎揣摩之道,也由於他一貫的忠誠與勤奮。此際則遇上一個極大難題,既要令上皇滿意,又不能冷落了皇上,和珅活得也不輕鬆!
和珅活得也不輕鬆!
天有二日嗎?
在上皇意識中自然不是,在嘉慶帝思想上當然也不是,在和珅看來則必然是。
而悲劇在於:和珅面對著父子皇帝,不能不以侍奉上皇為主,又要處處考慮子皇帝的感受,一僕二主,殫心竭慮,長袖善舞,八面臨風。他是一個能臣,也是一個小人,自以為世事洞明,自以為已經深結新帝之歡心,孰料上皇崩逝,緊接著就是那一聲晴天霹靂……(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