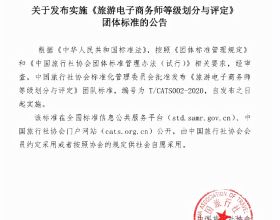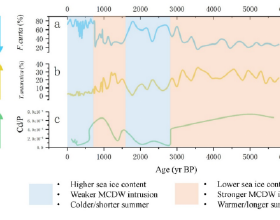這個冬天北京寒冷異常,寒流一路南下,連在南方的湖南也被寒潮臨幸了。
那天我剛坐到車上,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一看是父親打來的。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急促而嘶啞,大概意思是我二姑父因脖子上做過化療的地方奇癢無比,自己拿剪刀去剪,剪破了頸動脈,失血過多,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我等父親說完,聽他聲音不對,問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回答“感冒了”。我叮囑他注意休息、多喝水、睡前和醒後都要喝水,一定注意自己的身體……
二姑父去世了,再也見不到了。其實這些年,我都沒有見過他。回想三十年來,與他見面次數也不多。他有兩個兒子,與我年齡相仿。他大兒子叫勇、比我大,小兒子叫輝、比我小。勇性格內向、為人友善,輝性格外向、為人世故。他們都是很早就輟學接觸社會了,跟我的生活軌跡完全不同。等我上大學的時候,聽說勇做了倒插門的女婿,女方家在廣州做大米生意,生意做得不錯,至今婚姻牢固。而輝則很早就結婚了,物件是在新街的旱冰場溜旱冰時認識的,也早就離了。他還有一個收養的女兒,叫平,是我大叔送給他的,也已經三十出頭了,遠嫁了江西。他們仨我也很久沒見過了。
三十年前,姑父一家住在大水田村,家門朝南,門前是一片很大的水田,朝東望去是繁忙的京廣鐵路,鐵路向南是廣東,向北是北京。火車經過時聽不見對方說話的聲音,所以他們一家人說話都很大聲。朝西望去是湘江的堤岸,爬到堤岸上能看見滾滾的湘江水向北流去。
農村裡有些傳統的節日是會走家串戶的,比如中秋節、中元節。中元節各家都會擺上幾桌好菜,點上蠟燭,意在讓逝去的親人再回家看看,享用一頓家裡的好酒好菜,也順便招待一下還在人世間的親朋好友。如果趕上暑假孩子們不上學,年齡相仿的孩子湊到一塊,馬上變成了一個歡快的節日。我偶爾會去找勇和輝,總能一起幹一些新奇的事情。比如把釘子放在鐵軌上,讓火車壓過,然後從鐵軌邊上的碎石裡去找到被壓成鐵片的釘子。還有一次,我們去鐵路橋下面的小河裡去玩,勇找了一個充氣的輪胎,我們三個人都坐了上去。輪胎從河上游衝下來,帶著旋轉,撞上了岸邊,我沒扶穩,一個倒栽蔥從輪胎上掉進了河裡。河水也就到膝蓋這麼深,我當時感覺頭直接扎到了河底的淤泥裡,我條件反射一樣地迅速翻過身在河裡站了起來,腦袋上還頂著淤泥,只見他們倆坐在輪胎上發出咯咯的怪笑。
按照農村的習俗,二姑父被裝進了木製的棺材裡。家裡設了靈堂,請了鄉里的道士和腰鼓隊,敲鑼打鼓、哀樂喧天,熱鬧了好幾天。看到群裡發的訊息和影片,輝拿著話筒,音箱裡傳來《後來》的歌聲,輝的表情聲嘶力竭、沒心沒肺。這個影片是我二姑發的。在另外一個影片裡,我小姑和小姑父坐在靈堂的角落裡談笑風生,笑出聲的那種。這個影片也是我二姑發的。出殯時,十六個人抬著一口木頭棺材,也許是太沉,也許是太遠,抬棺人輪流出現體力不支,好幾次棺材都快掉地上了,看著影片的同時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到了山上,下葬了,一陣喧鬧過後,一群人一鬨而散,留下二姑父獨自守著家鄉的山和水,自己這一輩子也算是蓋棺定論了。
我印象裡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他們了,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給過一句問候。1994年奶奶去世後,孩子都長大了,關係漸漸淡了。這就是你問我太爺爺埋在哪,我回答不上來的原因。2008年,爺爺去世了,這個大家就慢慢散了。而二姑父的去世,是在提醒我,爺爺這個家早就散了。
爺爺出生和青年時代都是中國最混亂黑暗的時代,而且並無可以依仗的祖蔭。他的父親曾經經歷了怎樣的離鄉別井,已無從得知。所以爺爺有一身的本領,會做木工、會寫毛筆字、會拉二胡、會寫文章,完全不清楚他是在哪學會的。爺爺養育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他們都在建國後出生,每個人都在經歷自己的人生,不是在重複上輩人,每個人的命運也各不相同。他們都經歷了大躍進、三年困難、文革、支援三線、改革開放,時代在他們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這樣的時代並不能算是黃金時代,甚至連鍍金時代都不算。等到時來運轉時,他們都已經年過半百了。由於經歷特殊的時代,他們的文化程度都不深,而且既不是紅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也沒有具備特殊的才能,一輩子都很平淡,卻又看起來很曲折。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在還在世的哪些作家、藝術家、詩人,那些有能力用文字抓住一個時代的韻味、一個夜晚的芬芳和一首老歌的情調的人,或者能用一首歌串起無數的瞬間、精彩的回憶和幾代人的唏噓扼腕的人,掩蓋了絕大部分普通而卑微的人的光芒,彷彿他們都不曾來過這個世界一樣。
大姑作為爺爺家的老大,所經歷的也是獨一無二的。她遠嫁外地,丈夫已病逝。她有三個兒子,如今都已經不在世了,因為DP。她現在還在牢裡,也是因為DP。她是在去幫兒子進貨的時候被抓的,身上的D資一併被沒收了。兩年以後,市裡有個人到父親的魚塘裡釣魚,與我父親相談甚歡。閒聊間,父親瞭解到這個人就是主審法官,於是問起D資的事情,沒想到這個法官還挺爽快,答應父親幫這個忙。沒過兩個月,那筆錢打到了父親的賬戶上,父親把錢取出來都交給了大姑唯一的孫子。我只想說,這是一場夢,值得玩味的夢。
我從不隨便評判別人,是因為事物的表象往往和本質不符,很多事情看起來是一回事,實際上又是一回事。大姑嫁了工人家庭,光是這一點,就已經讓幾個妹妹羨慕不已。別人想要一個男孩卻求之不得,她卻連續生了三個男孩。回想起來,嫁給工人並不能實現階層躍升,生了兒子也並不能帶來幸福和滿足。期望自己的孩子能聲名顯赫,卻不如讓他們一生平凡寂靜更受用。
我小叔是爺爺家最小的一個,小時候得到的寵愛最多,哥哥姐姐也總是讓著他。他有一隻眼睛不好,小時候受過傷,成了斜眼。陌生人跟他面對面,總以為他不正眼看你,內心裡先鄙視一下。他腦子靈活,什麼掙錢他做什麼,當然除了不法的事情。他特別能生,生了三個女孩加兩個男孩,搞計劃生育的拿他沒辦法。他總夢想著自己成為富人,但他到現在也算不上。他的想法可能比我爺爺還老套,彷彿是從一百年前穿越回來的人。他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但不是精緻的那種,因為表達方式很直接,自己想要的,搶也要搶過來。我父親臉皮薄,老被這個小弟欺負,倒也不發火,表面上幾十年相安無事,其實內心裡並不平靜。
作為伴隨著改革開放一起長大的一代人,時代是我們身上永遠褪不去的底色。在我的記憶裡充斥著礦難、地溝油、三聚氰胺、強拆、南聯盟大使館、春運這樣令人壓抑的情結。現實生活,卻可能比這些更狗血。它給了我們太多的不究竟,竟長久無法解脫。
多想某天一覺醒來,媽媽在做飯,爸爸喊我起床,然後我告訴他們說:我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