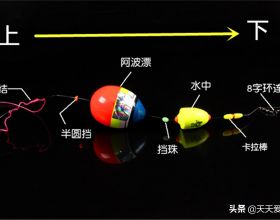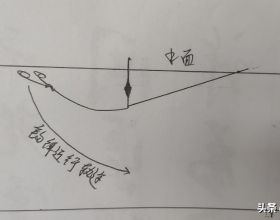(2016.10.13)
任憑冷雨來敲鐵窗。而漂泊的極致,便是將自己還原成一尊寂寞的雕塑。
是真的寂寞麼?難道不是來應一應眼前蕭瑟的風景?或許也有這樣的情懷。有鳥兒在低鳴,有溼漉的黃葉嗚嗚地墜落,有更加孑孓單薄的藤兒在窗外依舊捨生忘死地纏綿,有傘下的背影漸成絕跡。
好吧,你無法去阻擊一場春夢從三月走到末路,一如你無法活回青蔥的光陰。晚稻慘淡的綠著,山勢固執地畫完之字,太多的蘆葦失陷於累世的荒涼裡。沒有比幡然醒悟更痛徹人心的了。眉間的翳影重重疊疊地浮來浮去,宿醉的暗疾一日勝似一日,像一隻撞壁的蒼鷹,胸中的塊壘不需人懂。
楊朔說,“作為一個人,要是不經歷過人世上的悲歡離合,不跟生活打過交手仗,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意義。”想來大師的話是貼切而趨向委婉的,較為銳利一點兒形容,世界的另一面永沉黑暗。然而,會因為黑暗,花兒就不綻放嗎?會因為無助,人生就此而蒼白嗎?忽然間,憶起那個不斷奔跑的阿甘來,憶起淚流滿面的冉阿讓,及而屈原,清照,納蘭,詩僧曼殊,身心皆疲的三毛,向隅而立的張愛玲。
之後是鄭白城。那日坐在偌大的高鐵站裡,南歸的愁緒飄在心頭,抬頭看看湧動的人流,低頭握一握冰冷的票根,背後的中年女子莫名地嗤笑著,臨座的男人大咧咧蜷起左腿,彷彿置身於遼闊叢林,四望皆籬,明明在,卻望不透。這個時候,白城的一段文字發過來,他講最近常常有一種遁入空門的念想。這個痴子,怎不曉得空門不空,佛心本是人心啊。且又逃到哪裡去!茫茫塵世,小如須彌芥子,修行復修行,不在於披不披一身灰衣,不在於伴不伴一盞青燈。
他都明瞭,他只是想說,他只是想張一張緊攥蒺藜的手掌。可誰不想呢。千山萬水,大漠長天,人人都是苦行僧,唯一的區別在於,誰比誰更沉默一些。最喜歡在極深極深的黑夜,仰眺模糊一片的屋頂,不捨得慌忙入睡,哪怕再崢嶸,哪怕再飢餓,也不願將相依為命的憂傷放鬆。在微信裡存放著一些句子,有時翻看,會怔怔難言,“假設歲月無情\假設命運的痕跡有一些相似\假設樹葉漸漸地枯了\假設大雁又一度南飛\假設事如煙般散盡\假設雞司晨\犬守夜\而幾番陌路\憂患成真\此之謂浮生。”
哪裡敢賣弄!修辭的美左右敵不過一夕悵臥,敵不過晚來風疾。甚至連偶爾的膝痛都抵消不了,何來的造作與遊離。倦吶,倦啊!似一隻爬到車轍裡的蝸牛,似一隻箭傷發作的野鹿,再下一剎,再下一剎,最後是什麼樣的道盡而悲呢?抓蝨吞丹的阮籍去了哪裡,裸衣罵曹的禰正平尚能擊鼓否?投湖的王國維,伏軌的海子,你們且來應一聲!
江淮的秋事,多麼荒唐,推推搡搡,趔趔趄趄,教人分不清它的愛恨情仇。對面的山谷裡藏著一澗幽碧,些些水草已隱隱難活,在這疏離的濛濛雨幕裡,有誰會記得你摸過的柏,你坐過的石,你追過的殘月,你詠過的葡萄啊。每個黃昏,倒履上山,蟬的空蛻,流水的幽響,蝶在摹擬自己的影子,峰巒緊了一重再緊一重——那時時刻刻的天涯咫尺,只為了日後的變改初衷。
當然可以更粗曠些,點點滴滴,你道雨水擊下,某偏道那是無數的白鶴緩緩上升,你難道聽不見麼,鶴唳撕碎脆弱人心,所有行客將回到開始的來處,不會早一點兒,不會晚一點兒。曾經寄望於上帝遞過一枚利刃來,以斬盡恥於為伍的蠅營狗苟,可歲月如水消逝,上帝從來便躲在抓不住的下游,要信他,不如信自己!
“不行!說的是一輩子,少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一輩子……”在電影《霸王別姬》裡,說這句話的那個人,永遠地去了,只剩下冷酷的結局隨這雨水傾城。只剩下一個不相干的北人,挨著窗子,亂想胡思。反正就是那般,管之後做甚,說的是一輩子,忍著它來,那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