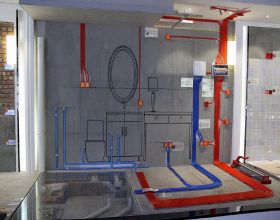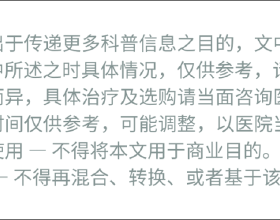熗菜(散文)
邢憲鵬
今年的小雪節氣,下了一場不小的雪。雪後放晴,妻子讓我去地裡撅些熗菜(這種叫法不正確,可大家都這麼叫,應叫蔓菁菜)。
吃過午飯,我提了一個摘蘋果用旳兜兜,禮泉果農每家都有的那種把蛇皮袋子攔腰斬斷一開二縫成的袋子,到我新栽的花椒園去。
疾行在路上的,躬身在地裡的,都是撅菜的人。
雪後空氣清新,沁人心脾。地裡一叢叢墨綠的葳蕤的蔓菁,似乎不俱嚴寒,仍生機盎然,惹人喜愛。
不到一小時,就撅了滿滿一袋子。
回來後,妻把菜摘淨,碼整齊,切成一寸長短,用水一淘,放在篩子裡空幹。又洗了兩個白蘿蔔,擦成絲備用。之後生火燒水,水滾後把菜倒入鍋中焯一下,七成熟時撈出,又放入篩子裡。等到菜的溫度降到不燙手而又稍熱,人稱沙溫的時候,把擦成的白蘿蔔絲倒入篩子,和菜攪拌均勻。
此時一股芥末的辛辣味道直鑽鼻孔進入胸腔,很是嗆人。
拌好後放入容器,熗菜就做成了。
下午做的熗菜,翌日早飯時就可以食用。
熗菜的製作工藝無疑是世界上最簡單的烹飪方法。當然這裡面還要注意一些細節,比如菜葉不能焯得過熟;焯好放入篩子要及時降溫,否則菜葉會變黃;拌蘿蔔絲時不能高溫,不然裝入容器會變成酸菜。
我們陝西禮泉人對熗菜的製作方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既不用問廚師,也不用查菜譜。因為廚師根本不懂,菜譜上也永遠不會記載。對禮泉的主婦們講熗萊的做法,就像叮嚀人要把帽子戴在頭上、把鞋子穿在腳上一樣,純屬多餘。
第二天早飯,妻抓了兩把熗菜。切碎,放上鹽、芝麻香調料和辣面,潑上熱油,拌好端上了飯桌。
吃著紅豆玉米糝子飯,就著熗菜,很是爽口。
熗菜是菜餚中的"下里巴人”,像缺乏社會地位的下層之人。它是永遠不和炒瓢打交道的,進不了餐廳酒店,入不了豪富朱門。從古到今,只有貧苦農民,冬春之季,端一老碗糝子、一大盤熗菜,在院裡、門口,或蹲或坐,有滋有味地吃著。果農賣果子時,包果子的婦女們的飯桌上總有一碟熗菜,這恐怕是熗菜經過的最大場面。
上層之人不知熗菜為何物,見了也不屑一顧。
熗菜的食材叫蔓菁,也叫蕪菁,兩年生草本植物。葉子狹長,有大缺刻。開黃花,果實細長。種子研細可做成芥末,是有辣味的調味品;也可以榨油。根是塊根,和蘿蔔一樣有肉質,人們叫它蔓菁或蔓菁根。
蔓菁屬於芥菜家族。人說龍生九子,各不相同。芥菜的子孫眾多,形態各異。既是自然進化的結果,更是人工培育的功勞。這些變種中有吃根的,如我們熟悉的大頭菜;有吃莖的如榨菜,四川涪陵的榨菜全國聞名;有吃葉的如雪裡紅,常做醃菜。蔓菁菜也是吃葉的,模樣和雪裡紅極像。雪裡紅是一年生,蔓菁是兩年生。
蔓菁品相不高,因而地位低下,和其他兄弟相比,自慚形穢。其他兄弟都是人工栽培,只有它是旅生一一古人稱植物未經播種而生的叫旅生。
漢樂府《十五從軍徵》中就有"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旳詩句。
這種品相低下的食材,只能稱之為野菜,因為沒有人去種植而自生自滅。但它的生命力卻極頑強,可能它自知卑賤,所以不向人們要求什麼。
不論土地肥沃或貧瘠,不論路邊或渠岸,只要有一粒種子就行。這粒種子不管是掉落的、風吹的、鳥啄的,只要有一粒種子就會生根發芽。
沒有人施肥,沒有人噴藥(自然也沒有汙染),它依舊不屈不撓地生長。
她可能會遭到行人的踐踏,牛羊的啃齧,鐮刀的刪刈,但只要根還在,就又萌生新的枝葉。
她"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蔓菁是有恩於人的。它的莖葉嫩時做菜,根有甜味,雖不好吃也能充飢。民國十八年,關中大旱,饑民遍野,餓殍載道,蔓菁救了多少人的命?先是莖葉,再是塊根,都被災民吃光,以至幾年很難見到蔓菁。於是在禮泉,有了一個流傳近百年、老輩人掛在嘴邊、現在年輕人已不再說的俗語:“再也沒有十八年的甜蔓菁咧”,比喻好事再不會有了。
我上小學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我也吃過蔓菁根。
鄰村有一塊近百畝的蔓菁地,飢餓的村民拿著鐵鍁在地裡挖了一遍又一遍。挖下的蔓菁根回家一煮當飯吃,個別餓得不行的人挖下隨即就生吃了。那時的蔓菁根又甜又脆,好吃極了。幾十年過去了,還記憶猶新。
蔓菁葉子製作熗菜,其歷史也相當久遠了吧。每年立冬前後開始撅(不能太早),一直到第二年的清明時節。快開花時,它的莖葉還可以做成酸菜。時間跨度長達半年之久,是食用期最長的野菜。
過去常吃熗菜,也是因為窮。現在人們生活好了,大魚大肉吃多了,吃些熗菜,用來換換口味。
熗菜這種無公害的綠色食品,對於防治"三高"類富貴病絕對大有裨益。
我村一對家境貧寒的夫妻,多食野菜,每年有六七個月以熗菜佐餐,卻都享有高壽,人們把秘訣歸結於常吃熗菜。
妻做好熗菜後,學習村裡好多人的樣子,給在西安打工的兒子一家捎了些。
在縣城教書的"小棉襖",週日開車回來看望父母,走時也帶了些。
兒女們都說熗菜還挺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