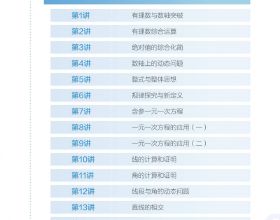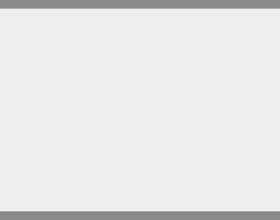整天在工廠裡待著,如果不是看到宿舍邊上的梧桐樹葉飄落到窗前,虛靈都不知道冬天到了。南方四季不分明,所謂的秋天在幾場秋雨中就溜走了,氣溫會突然驟降。不像在農村的冬天,清晨的稻草上會蓋上一層薄霜,經常會站在山坡或者田裡讓北風吹裂臉皮嘴唇。這裡的北風吹不進車間,只有在洗澡時感覺到水冰涼了許多,被子還是薄薄那床,加蓋上一件大衣就可以睡著了。手指不在磨破了,但是冬天的膠水還是會讓手指裂開,開始時裂一兩道口子,後來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十個手指都有裂縫,和指甲連線處的肉裂開更痛一點。拿筷子都會生疼,夾菜姿勢很彆扭。這個不算什麼,比起在農村時磨破的手去抓化肥的疼痛,這點疼痛可以用鄭智化的歌詞“這點痛算什麼”。鏡子裡的自己,白淨了許多,露出了清晰的輪廓,帶著稜角的額頭一直透著剛毅的氣息,眼神裡多了些圓滑。不時有同車間裡同齡女生過來問虛靈布料的位置,問他塗臉的百雀羚是哪買的,問他老家哪的,反正問題越來越多,虛靈只當這是因為他來廠裡時間久的緣故。但是,男的朋友實屬不多,除了開始帶他的老劉,只有後來同宿舍的建軍和他有一起說話上街。一切只因虛靈太內向,不愛主動和別人交流。
來這快一年了,聽說家裡的大妹紅梅和她村裡的閨蜜們一起去廣州電子廠打工了,可能是帶著怨氣,她不和他這個哥哥說一聲就走了。聽說繼父送她到縣城車站,她頭也不回地上車了,不願多說一句話。母親在田裡默默地勞作著,依然起早貪黑。她總感覺自己對不起所有家裡人。她不知道,也沒想過,有沒有一個家裡人覺得對不起她,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做著很大部分農村婦女一樣的決定,承擔著比別人更多的苦痛與酸楚,裡面有痛失前夫時撕心裂肺的痛,有決定讓大兒子復讀大女兒輟學時的無奈。現在兩個都離去尋找各自的生活了,她要繼續撫養和第二任丈夫華貴生下的女兒和兒子,只是這一次她不再選擇了,咬緊牙根,砸鍋賣鐵也要讓接下來兩個孩子讀完書。她倔強,她不屈服,她懂愧疚,這樣的性格決定了她比同村裡同齡的女人更顯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