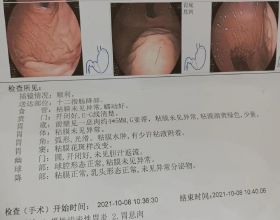這事兒啊,是我聽說的,據說好像,大概,也許,差不多,應該,可能是發生在民國那個時候。給我說這故事的人是我們老家的一個親戚----我太奶奶的表妹她二嬸子的堂弟的三哥的表姑父的外甥。輩分我不知道怎麼論,但人,我是見過。那個時候家境好,我還不大,我親姑姑結婚的時候,在酒席上見過。據我爺爺的六表哥介紹,說是這個親戚要從瀋陽回山東老家來,都是自己家實在親戚,讓給找個地方住。
不知道怎麼論的,反正我就多了一個遠房的爺爺。放了學我常常去他住的那間小屋。聽這個從大地方來的遠房親戚講講故事。
說是當時叫奉天,有個地方叫北市場。北市場上什麼人都有,三教九流,叫買叫賣的,耍手藝撂地的,甚至是招搖撞騙的,還有偽警察到處的欺負老百姓。北市場雖然嘈雜,但是卻很繁華,說白了,人氣兒催的。北市場往西有個地方叫於家窩棚,裡邊沒有一家姓於的,氣人不?於家窩棚從西頭數第一家,住著姓王的這麼一家子。老爹,老孃還有一個獨苗叫王擎壽。王擎壽是個變戲法的,沒事兒上北市場去耍手藝弄點兒散碎銀兩。老兩口在家靠著地裡的收成弄點吃喝,王擎壽耍手藝賺的錢就能存下。一家三口雖然不富裕,可是倒也過得相安無事。唯一讓老孃掛心的事兒就是王擎壽的親事,孬的吧,自己兒子看不上。好的吧,人家還嫌棄王擎壽。就這樣,親事說了沒有三十家也有了二十七八家,王擎壽二十好幾了,還自己耍單兒。說話有一年的三月份。天還冷得邪性,王擎壽從北市場收攤兒回家。東北的冬天那真叫冬天啊,雪厚風狠,三月了也沒覺得是春姑娘來,棉褲棉襖的更不敢脫。他糊的自己就剩倆眼正加急往家趕。路經過的一個小樹林裡傳來一群孩子的嬉笑,叫喊聲。還有個孩子像是拿棍子挑著這什麼東西。他一時好奇,走過去一看,好傢伙。原來是,幾個孩子在個老墳窟窿裡扒出一窩狐狸。大狐狸沒看見,三隻小狐狸被弄死一隻了,還有一隻半死不活,最小的那隻蜷縮著瞪著怯懦的小眼兒,絕望的看著這幾個孩子。王擎壽看了一眼本不想管閒事,可是又有些不忍。想了想對幾個孩子喊道:“你們真膽子大啊,不怕狐大仙夜裡去你們被窩裡抓你們?”幾個小點兒的孩子像是被王擎壽的喊聲嚇住了,可是挑著死狐狸崽子的那個孩子得十幾歲了,一臉的不在乎地回答:“俺們怕就不幹,幹了就不怕。咋的?你想找茬口啊?”
王擎壽一看沒嚇住幾個孩子,趕緊換了笑臉兒說:“說啥呢?跟誰倆呢?這不是怕你們惹上麻煩嗎?為你們好。不知好歹的玩意兒。”他一邊說一邊觀察著孩子得反應,見領頭的野孩子的目光沒那麼兇悍了,趕緊又補充說:“俺們村就有個小孩被狐大仙給迷了,前幾天死了。身上都讓狐狸給咬爛了,都是血,老嚇人了。”這時的幾個孩子看起來有點兒心虛了,王擎壽趕緊又加了加溫。他從袖子裡掏了掏,摸出一塊糖說:“看著啊!”說完往上一拋,雙手接住的時候,手裡已經是一捧花生了。幾個孩子一下就被吸引住了。他把花生分給幾個孩子吃,孩子都圍了上來。領頭的孩子扔了死狐狸,歪著頭一邊兒吃花生一邊問:“你咋變的?糖呢?俺們要吃糖。”王擎壽見有效果,笑了笑說:“不是我變的,是狐大仙昨晚給我託的夢,說你們要禍害它們,讓我來攔著點兒。我這有事兒,來晚了,你們還真給人家禍禍了?”別的小孩一聽王擎壽這麼說,都有點兒害怕,不約而同的看向那個孩子頭。領頭的野孩子見大家都看著他,明顯不想露怯,但是可能心裡也低估,他看了看其餘的孩子突然像是做了什麼決定似地說:“你想騙俺?俺不怕也不上當。”王擎壽笑了笑,對他說:“你那不還有沒吃的花生嗎?想吃糖不是嗎?你給我一個花生,我跟狐大仙給你換糖,狐大仙就在邊上看著你們呢!”。孩子們明顯是被嚇到了,東北農村這類傳說太多了,誰沒聽大人說過幾個啊。他們怯懦懦的往四周看看了,像是找狐大仙兒,又不自主的都往一塊兒湊了湊。王擎壽突然大喊一聲:“上眼”。接著雙手一揚,扔出來兩把糖。孩子們見了憑空落下的糖塊正驚地張大嘴巴面面相覷。王擎壽知道是糊弄住了,大聲說:“大仙說了,讓你們拿著糖趕緊走,不然今晚上鑽你們們被窩兒...”話沒說完,一群孩子,嗚嗷喊叫的就跑了,那還顧得上撿糖吶。見把孩子嚇跑了,王擎壽走到老墳邊,把剩下的倆狐狸崽子看了看。那個半死不活的眼看活不成了。剩下另外一隻怯生生的看著他,眼睛裡像是含著淚。他想想,把那隻狐狸崽子拿起來,解開衣服揣在懷裡。走了幾步停下想了想,又回頭把那隻被挑死的狐狸崽子放回了窩裡。看了看兩隻死狐狸崽子,自言自語地說:“不是我不想埋你們,這天寒地凍的,挖不動土啊。你倆啊,將就吧!”說完搖搖頭嘆口氣。轉身就走,走了幾步聽見身後林子裡有輕聲兒飄出:“好人啊!”王擎壽一個機靈,猛一回頭,什麼也沒有。彷彿是林子裡有稀稀嗦嗦聲,像是腳步聲,又像是風聲。他撞著膽子喊了一聲:“誰呀?幹哈地?”。沒有人回答。他眉頭緊了緊往林子裡又看了看,自語道:“聽差劈了!?” 然後自己笑了笑,搖搖頭往家走去。
王擎壽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樹林墳地忙叨了那一會兒讓他比平時回家晚了些。一進門看見老孃正在忙叨著收拾著廚房,老爹正在炕上吧嗒吧嗒的抽著菸袋。剛進門老孃正準備埋怨幾句,王擎壽趕緊地從懷裡掏出小狐狸,遞到老孃面前說:“回來晚了,看,這是啥?”老孃定睛一看看清楚是隻小狐狸。正要發問,王擎壽又從懷裡掏出一把糖說:“先吃糖,我講給你聽。”老孃一手託著小狐狸,一手接過糖,嗔怪的看了一眼王擎壽。轉身去了王擎壽的房間。王擎壽跟在老孃後邊也進了屋。一邊看著老孃拿棉花,找盒子安置小狐狸,一邊說了今天回家路上的經過。正說的眉飛色舞,吐沫橫飛,冷不丁聽見身後老爹的聲音道:“惹乎這些玩意兒幹啥?一股子狐騷味兒不說,你別惹了不敢惹的狐仙兒...”話沒說完,老孃就接過話茬說:“招惹傻?就是有仙家咱也是救他,咋還是咱招惹他呢?要是找上門兒也是報答咱們。”說完不等老爹回嘴,又接著說:“別磨嘰了,趕緊吃飯吧,本來就回來晚了,一會兒飯該涼了。”
飯菜上桌,三人坐定。老爹磕了磕菸袋,收到荷包裡。“啪啪啪,啪啪啪”的拍門聲從外傳來。那個時候三人都坐盤腿坐在炕上,圍著炕桌正舉著筷子正準備開吃呢。這幾聲拍門聲讓三人面面相覷。老孃嘟囔了一句:“這天兒這時候會是誰呢?”王擎壽放下筷子說:“我去看看”。說完下炕穿上鞋,又披上自己的大棉襖向外走去。月光如水,院子裡照得一片銀光。王擎壽一邊走一邊大聲對著街門問:“誰呀?” 聲到人到,院子不大,問話的時間還沒容外邊的人回答,王擎壽就打開了街門。
藉著月光,門口站著倆人,一個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另一個躲在老太太身後的雖然看不清臉,但也能分辨出來是個20歲左右的姑娘。老太太見有人開門,忙上前雙手合十祈求道:“哎呀小夥子你好哇!”王擎壽趕緊回答說:“你好,你們是?”老人見發問了,回答說:“俺們是山東人,沿著路要飯過來的,這不走到你家門口嘛!也沒有要到吃的,也沒有要到喝的,天也黑了。”說道這裡,她往身後一拉把躲在身後的姑娘拉倒旁邊,指著姑娘道:“這是俺孫女,我這歲數帶著她半夜趕路,也不是個辦法...”王擎壽藉著月光一打量這姑娘,當時就迷住了。這不是自己一直夢寐以求的姑娘嗎?這一下還沒說話就被迷得五迷三道了。老太太見王擎壽失神,面上掃過一絲兒寒光卻又換上笑臉輕輕呼喚:“青年,青年?”王擎壽這才回過神說:“哎呀,趕緊吧,先進來再說”說著趕緊地往裡讓兩人。
外邊的說話聲不大,屋裡卻也能聽見是有人進了院子。老孃跟著披上厚衣服也跟著到了院子。見王擎壽領著倆人進來,還沒有來得及問就被半推著進了屋。老爹又點上了菸袋抽著,他那穩坐炕頭端菸袋的姿勢彷彿是要讓來人明白他在這個家的位置。
四人炕前站定,往炕上看了看,又都看了看老爹。還是老太太先說話,把怎麼從山東逃荒一路怎麼來的不容易撿要緊的說了幾句,然後表達了要蹭飯,留宿的意願。老孃看著這倆人臉上帶著笑,心裡打著自己的小算盤。老爹還是抽著煙吧嗒吧嗒的不說話。王擎壽早就等著人家姑娘撒不開眼了。一個勁兒的咧著大嘴,心裡連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老太太說完,見一屋子的尷尬,趕緊拉了一把姑娘道:“叫人啊,”一邊把身上的破包袱往旁邊的凳子上放,一邊自來熟的滿臉是笑繼續說:“小地方來的,孩子害羞,讓大家笑話了。”姑娘卻低著頭沒有說話,臉上蕩著紅暈,也不知道是害羞,還是凍的。
老爹在炕沿磕了磕菸袋,又打量了一下二人。臉上掛上笑,說道:“哎呀!山東人就是老鄉嘛!俺們祖上也是山東過來的,趕緊上炕。先吃飯,今晚上就睡下了。有什麼事兒明天再說。這都開春了,卻還是冷的邪性。”說完這幾句,向老孃看了一眼,繼續說:“愣著幹啥呢?趕緊燒點熱水,再那兩雙筷子。”老孃滿臉是笑的回答道:“是,是,是”說著去扶老太太和姑娘,邊扶邊說:“你們先上炕暖乎暖乎,喝口熱水,不然從外邊進來一肚子涼風,容易肚子疼。”老太太千恩萬謝的的上了炕,伸手拉著姑娘也上了炕,姑娘還是低著頭不說話。老太太挨著老太太,姑娘做下首。王擎壽挨著老爹也坐定。桌上多了兩雙筷子,兩碗熱水。老孃端起一碗就往姑娘跟前遞,一邊熱情的說著:“看這閨女這個俊啊,哎呀,真好看。趕緊喝幾口熱水,天寒地凍的,暖和暖和胃,別傷了身子。”這邊見姑娘伸手接了水,喝了兩口,又熱情的招呼老太太說:“趕緊也喝兩口吧,溫度正好。我也不知道咱倆誰大,就不客氣叫你大姐了。大姐啊,趕緊喝幾口熱水,咱們吃飯。”眼見著兩人都吹著熱氣喝了幾口水,又遞上筷子,熱情招呼:“沒啥好吃的,趕上了就將就吃,咱東北人熱情。吃飽喝足睡一覺兒,明天咱們再說明天的”說著兩人結果筷子。老太太寒暄著,感激的笑堆了滿臉。姑娘還是不說話,低著頭默默地吃著飯。王擎壽兩隻眼一個勁兒的盯著姑娘,笑得嘴都要咧到耳朵後邊了,一邊給姑娘碗裡夾菜一邊說著客氣話:“你吃呀,多吃點兒,到這就是到家了,別客氣啊…”
主人客氣熱情,滿臉堆笑。客人小心唯諾,滿臉賠笑,一頓飯在熱鬧和尷尬又熱情中結束。王擎壽搬進了小廂房,而老太太和孫女睡在了王擎壽的房間。
半夜一片漆黑,燈滅人入眠。院子裡靜的只有月光的聲音。突然,廂房亮起了一點燈光。稀稀嗦嗦一陣地摸索聲後,燈光滅了。藉著月光卻見王擎壽穿著停當,輕手輕腳的開門走向自己原來的房間。接著老爹和老媽也摸了過去。隨著又一陣地稀稀嗦嗦聲,接著就是低吼和叫罵聲…
王擎壽房間的地窖裡,燈火通明。地窖四周的牆上掛滿了各種刑拘。地窖的中央立著兩根柱子。柱子上綁著一個四十左右歲的婦人和一個二十左右歲的青年男子。兩個人的衣服都被撕開,尤其是青年男子的褲子都被脫了。地上滿是乾涸的血跡,想必不知道有多少人喪命如此。老爹一身的短衣裝小打扮,彷彿年輕了十幾歲,早就沒了平時看上去的老態樣子。唯一不變的是手裡拿著菸袋吧嗒吧嗒的抽著。他站在牆角的桌子旁。冷眼看著柱子上綁著的兩個人。老孃也換了裝扮,身著一身屠夫的衣服,看起來早沒有了普通農婦的那股子憨厚勁兒。她臉上帶著一股邪魅的狠勁兒,掛著淺淺的笑。手裡拿著一把剔骨刀,那被王擎壽帶回來的小狐狸被她固定在桌子上。正準備著拿小狐狸先下刀。王擎壽左手拿著一掛女人長長的假髮,右手拿著一個水瓢,站在被綁的人面前。嘴裡罵罵咧咧,哪有白天那善良的樣子?
一瓢涼水下去,被綁著的兩個人都悠悠的轉醒過來。王擎壽對著男青年襠部就是一腳。“哎呀!”青年一聲慘叫又昏了過去。那少婦滿臉的恐慌,帶著滿臉的祈求哭著求饒。
老爹磕了磕菸袋,又續上菸絲,緩緩坐下,點菸。猛吸了兩口,隨著大口的煙霧噴出,老爹的嘴裡蹦出幾個帶著冰霜字:“說說吧?還要再挨一遍打嗎?”中年婦女帶著祈求的口吻說道:“俺說的都是實話啊,俺就是奉天本地的,住城西頭。和他...”婦人停住了,扭頭看了看年輕人,又帶著哭腔繼續說道:“他是俺遠房外甥,俺是老不死的仗著有錢,又納了一房姨太太。俺受不了寂寞,勾引了俺這外甥...”說著聲音低了下去。“他孃的,晦氣,俺還真以為是個大姑娘,這褲子都脫了...”王擎壽還沒說完,旁邊的老孃咯咯咯的笑了起來。王擎壽越想越氣,伸手捏住了男子的臉,打量幾眼,悠悠地說:“你別說,要是個姑娘還真俊。可惜...”王擎壽說著火氣又上湧“呸”得一口濃痰吐在青年人的臉上。“咯咯咯”老孃又笑起來:“是你色迷心竅,看見娘們兒就走不動道。一進門我就看出他像個男的。給他們遞碗灌迷魂湯的時候,一抬頭喝水,那男人的喉結就漏出來了。你是滿腦子女人赤條條的樣子,哪有心去琢磨?”“你知道不早告訴我?”王擎壽心頭火更甚,大聲嚷嚷著。老孃面帶嫵媚的白了王擎壽一眼道:“誰讓你朝三暮四...”話沒說完,她自己打了個寒戰。偷眼看了看老爹。王擎壽似乎也意識到什麼,也心虛地看了看老爹。“大哥...”王擎壽剛叫了一聲,想要說點什麼。老爹一揮手打斷了他,彷彿他剛才沒有聽到王擎壽和老孃的對話。老爹只是陰森看著被綁的女人問道:“你勾引自己外甥,威脅他殺了你自己男人。然後來個捲包會?故事已經講了一遍了。我要聽實話”說著偏臉看了看老孃,老孃點點頭。一刀從小狐狸的脖子切進去,血順著桌子一直的流到地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老孃舔了舔尖刀上的血,看看對面的女人,又瞅瞅還沒有死投的小狐狸,開始剝皮。“看見了嗎?”老爹拿菸袋敲敲桌腿,然後問女人“不說實話,下一個就是你。”“說”王擎壽突然的一聲爆喝下了女人一機靈,哭著說:“真是實話,俺們不是誰派來的,更不知道你們真實身份。俺們捐了錢就跑啊,路上怕碰見熟人就化了妝。本想女扮男裝,可是,”她又看了看自己的外甥,繼續說:“他咋裝扮都不像個老爺們兒,我們就乾脆假裝山東逃難的,他裝成個姑娘。俺自己裝個老太太。剛才俺倆躲在半路的小樹林裡。琢磨著不行天黑了再趕路,一路乞討到營口,坐船去天津。好巧不巧的,俺們看見這個心善的少爺”說著他委屈的看了看王擎壽。又道:“俺們就想著這數九寒天的夜裡跑別給俺們凍死,於是尋思著偷偷跟來。俺們還想假裝狐仙兒啥的,裝個神弄個鬼地,糊弄著,也許能在這住幾天。萬一有人追俺們,說不定就錯過去了。”“好娘賊,”王擎壽聽到這兒罵了一聲兒,“我說我把死狐狸扔進老墳的時候聽見有人說話呢!我還以為聽差了。原來那個時候你就想裝神弄鬼兒了?”說完過去怕怕扇了女人倆耳光。女人嚇得啊啊直叫。
“啪”,老孃把尖刀插在桌子上。桌上的小狐狸已經分成三堆,骨,皮,肉。老孃搓了搓手看了一眼被綁著的女人。轉身對著老爹說:“當家的,看起來他們說的是實話。咱們上次的買賣都過去三年了。早該過去風頭了。不該是探子,應該就是一對兒姦夫淫婦,這騷貨仗著自己的姿色不甘寂寞。勾引外甥殺了丈夫又玩兒了個捲包會。正好讓咱們碰見了。”老爹點點頭,看了看嚇壞了的女人說:“好,我信你。但是,你們捲來的錢呢?”女人見對方終於相信了,討好又帶遲疑的詢問:“俺要是說出錢在哪?你們放了俺?”“哈哈哈”老孃聽完笑了起來,一把拔出桌上的尖刀,又舔了舔刀尖兒。慢慢走到被綁的青年面前,突然發狂似的就往他身上捅去...。不知道捅了多少刀,血流了滿地,人已經死透了。女人被濺了滿臉血,早被這瘋狂舉動嚇得昏了過去。
一瓢水潑過,女人悠悠的醒過來。睜開轉眼的瞬間就看見老爹的兩道寒光盯著自己。女人一個哆嗦,還沒開口求饒,就聽見老爹冰冷的聲音:“說出你們卷的錢藏在哪裡,我讓你死的舒服些。不然,你看看那隻死狐狸吧,那可是活著剝皮。你自己選”女人聽完看了看早已經分成三堆的狐狸,又瞅了瞅旁邊那被捅成篩子的相好。眼裡突然留下了眼淚,她知道自己是必死無疑了。絕望的看了站在身邊的三個人,眼睛已經失去了生氣。“哈哈哈,哈哈哈”女人突然放聲大笑起來,眼裡滿是絕望的喊著:“死吧,死吧,反正是一死,那就誰也別想好,弄死俺吧!誰也別想那些錢了,都死,都死吧。”女人歇斯底里地喊叫似乎讓老孃和王擎壽都愣了一下。相互看了看,然後又都齊齊的看向老爹。老爹一臉的淡定,看著女人道:“裝瘋?”然後皮笑肉不笑的看了看王擎壽說:“你知道怎麼弄了,我們出去等你。”老孃看了看王擎壽,臉上帶著醋意的哼了一聲,不滿的向外走去。老爹卻嘴上掛著冷笑在經過王擎壽的身邊時,拍了拍他的肩。此時的王擎壽早就滿臉的淫笑,搓著雙手向女人走去…
王擎壽房間的炕前放著一張桌子,兩張凳子。兩邊分別坐著老爹和老孃。老爹還是穩穩的抽著菸袋。老孃在另一張凳子上坐著,手裡擺弄著茶壺茶碗,臉上卻掛著寒霜。“給,”老孃站起來,倒了一杯熱茶,遞給老爹。老爹看了一樣老孃,卻沒有喝。老孃坐回去似有意無意的給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來喝了一口,看了看老爹,扭頭盯著炕上的大木箱子。木箱子上平時都垛著被窩,此時被窩卻凌亂的仍在炕上。而開著蓋子的大木箱子裡,不時地傳出男人陰冷的笑聲,淫蕩,寒冷,猥瑣,狠毒...彷彿所有惡笑都從這地窖裡傳出來。老爹磕了磕菸袋,端起茶一口喝下去。“啊,啊,啊...”女人不知道在受什麼樣的折磨,呼喊的聲音由大慢慢變小,除了王擎壽的呼喊和叫罵聲以及得意的淫笑聲,女人似乎沒有了動靜。“再去燒點燙水,誰都要要涼了”老爹看了看老孃,話雖然是平常話,卻帶著不容反駁的口吻。老孃站起來,拿起燒水壺,不滿的說道:“想下去湊個熱鬧就湊個熱鬧唄,不用把我支開。”老爹一愣,換上笑臉說道:“你胡說什麼?”我下去看看,別沒問出藏錢的地方,再給把人先弄死了。”“哼”,老孃冷哼了一聲,提著燒水壺轉過身,卻沒有往外間走。“不用說那些,我懂你們老爺們兒那點事兒。這三年來,你那還有以前勾搭我的樣子?我也是自己找的,好好的日子不過,跟你們一起殺夫棄子不算,捲來的錢你藏在哪裡都不知道。還要裝窮過日子,朝不保夕,心驚膽戰的。見到有人多瞧咱們幾眼就怕是衙門的探子,整天這日子過的,都神經了。三年了,你也膩歪我了,我早看出來了”“你這是說的什麼話?”老爹站起來剛要解釋幾句。這時聽見大箱子裡有人要走出來的聲音。老孃瞥了一眼剛露出半個頭的王擎壽,提著燒水壺走向外間。
老爹再次走進地窖的時候,也吃了一驚。勉強透過長頭髮看得出是赤身裸體的一個女人,或者說是屍體平躺著。他走過去,圍著一動不動的女人轉了轉,這才發現,那把剔骨尖刀插在女人的咽喉,只剩刀把的一小部分留在外邊。老爹搖了搖頭,小聲地自言自語道:“失控了,還是失控了。不愧是王禽獸,真是禽獸。”說完,他彎下腰,把刀拔出來。看看了地上女人被撕成破布的衣服,拿起來擦了擦剔骨刀,順手揣進了懷裡。
老爹剛走出地窖,坐在炕前的二人止住了話頭。他一步邁出木箱反手改下蓋子,然後跳下了了炕。王擎壽站起來,叫了一聲,“大哥...” 剛開口說什麼,被老爹用手勢壓了下去。他就勢坐在炕上,不慌不忙掏出菸袋,續上菸絲,點菸。王擎壽尷尬的笑了笑,又坐回去。老孃端著熱茶送到老爹手邊,面帶微笑的說道:“兄弟剛才已經問出藏錢的地方了,你先喝杯茶。咱們商量一下,一會兒咱們仨去拿錢。你也把咱們以前捲來的錢都拿出來吧!咱們一把火燒了這個地方,遠走高飛。我是過夠了這東躲西藏的日子了。咱們去南洋...”。老孃還沒有絮叨完,老爹打了個手勢止住了她的話。他抽了幾口煙,看了一眼王擎壽。王擎壽正直勾勾的盯著自己。他又看了看了老孃,接過水,卻沒有喝。老孃愣了一下,轉身斜了王擎壽一眼,坐了坐回去。王擎壽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看了看老孃。老孃也倒了一杯,吹了吹,喝了一口。然後又給王擎壽和自己把茶續上。老爹一口又幹了手裡的茶,然後看看二人。緩緩的說:“咱們開啟天窗說亮話吧!”他吧嗒吧嗒的抽了幾口煙,看了看驚愕的二人,笑了笑繼續說道:“表妹,咱倆本是青梅竹馬,是你家那個老王八非要拆散咱倆。要不是我姑父貪錢,你也不至於嫁給那個老王八。我殺他,搶他,沒有悔意。至於你,”他看了看王擎壽,“你本是老王八家的長工,你們主僕二人那些事兒,我不說,不等於我不知道”。王擎壽和老孃聽到此處,同時站起來,似乎要發作。老爹還是淡定的笑了笑說:“別急,說這些呢,沒有別的意思。回想這三年啊,我對你倆又愧。如果不是我的介入,你倆不過是一對苟且的主僕。我這一攪合,都亂了。三年來,咱們隱在這個小破村。有錢不敢花,還得裝好人,扮善人的假裝一家人過日子。你們也夠了,我也夠了。一會兒,我帶你倆去把我藏的錢取了。咱們三一三十一,分了錢,你倆去你們想去的地方吧。我換個地方,買幾畝地,穩定下來,過過安生日子,我是真累了。”說完,老爹磕了磕菸袋,又滿臉微笑的說道:“別不信,我現在就帶擎壽去拿錢。”他站起身對著老孃說:“你就在家準備準備吧,一會兒回來,咱們分完錢把咱們儲存的火油都澆上。一把火後咱們都做個人。今天那份兒,別告訴我,我也不要。就當我送你倆的結婚錢吧!”說完重重嘆口氣,起身邊往外走邊說:“擎壽,我在院裡等你”。
王擎壽聽完老爹一席話愣住了,他看看了同樣發懵的老孃。老孃衝他點點頭輕聲說:“話都到這份上了,挑明瞭也好。你路上小心,到了地方,拿到錢,就把他做了!”然後蕩笑著拉了拉王擎壽的手說:“我等你回來”王擎壽點點頭,眼睛迸發出興奮的光。他猥瑣的在老孃胸前抓了一把說:“等我回來”。說完他一把扯掉了門簾子,向院子走去。
“啊,你他娘,啊...嗚嗚,嗚嗚,嗚嗚...”王擎壽剛走到院子就發出了慘叫。老孃一聽打了個機靈,趕緊竄到廚房,抄起菜刀幾步蹦到院子。只見王擎壽被老爹按在地上,一手捂著嘴,一手拿著那把剔骨尖刀不停的捅著,嘴裡還一邊嘟囔:“王擎壽,王禽獸,王擎壽,王禽獸...”而王擎壽早就沒有了掙扎。除了身體的抽搐,早就沒有進的氣兒了。老孃呆呆看著,老爹見一個黑影,佇立不遠。他放開地上的王擎壽,猛地站起來。手裡提著帶血的剔骨刀,刀上的血滴滴答答的,藉著月光分外的刺眼。他一步一步的向老孃逼近,老孃也反應過神兒來。“你個下作東西,搞偷襲?千算萬算沒料到你這手兒”“少廢話,你個淫賤禍,年輕勾引老頭子,老了勾引年輕的,今天我就殺了你這個騷貨。”說完他往前一竄,腳下卻一軟,晃了晃,倒了下去 ……
老爹感到一陣刺骨的寒意,晃了晃腦袋迷迷瞪瞪的睜開雙眼。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怕光,綁在地窖的柱子上。老孃站在他的面前,一手拿著水瓢,一手拿著那把剔骨尖刀。他無奈的搖搖頭,苦笑了一聲問道:“你們在茶裡下了藥?”老孃得意的笑了笑,扔掉水瓢,把玩著手裡的剔骨刀,悠悠的回答道:“知道還問?就算你再小心,還不是一樣著了道?”她得意洋洋的走上前去,摸了摸老爹的臉,用輕鬆而又惋惜的口吻繼續說道:“說說吧,看在你以前也是我男人的份上,只要你說出藏錢的地方,我給你個痛快。”老爹點點頭,“人算不如天算。沒想到咱們打算在同一天動手。”“咯咯咯……”老孃發出了清脆說完幾聲笑,說道:“三年啊,我忍夠了。你們倆一對兒都不是東西。我再忍下去都要瘋了”。說完她又大聲而放肆的笑了起來,直到眼睛裡笑出淚水。老爹默默的看著,眼裡帶著無奈和痛苦,見老孃笑夠了,溫柔地說道:“玉麗,你真這麼恨我?”老孃顯然沒有想到老爹會這麼稱呼她,彷彿一下失了神,不由自主地走過去,趴在老爹肩頭,像是想起什麼,輕輕地叫了一聲:“青表哥”。一聲‘青表哥剛叫完,突然這玉麗揚起手,對著老爹大腿內側就是一頓猛刺。一邊刺一邊喃喃輕呼著:“王青表哥,舒服嗎?舒服嗎?”
王青顯然沒想到玉麗會這麼對她,以為還有緩和的餘地,沒想到自己又失算了。玉麗將他襠下切的稀巴爛,舔了舔刀上的血,直勾勾地盯著王青。雙眼恨不得瞪出血來。她輕蔑的一笑,狠狠的在王青的臉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後換了一副溫柔地口吻說道:“表哥,舒服嗎?哈哈哈,哈哈哈……你以為我還是那個什麼都不懂的小黃毛丫頭?我就問你一句:錢藏在哪兒了?”事已至此,王青知道沒有翻盤的機會了。他忍著疼沒有暈過去,苦笑了一聲道:“好,我告訴你。你省了你活人皮扒皮的手藝吧。給我個痛快。”說完,他頓了頓,用力撐撐要垂下的眼皮繼續道:“天意如此吧!其實那筆錢我就藏在今天擎壽回來路上的老墳裡……”“你撒謊,”玉麗聽到此處突然舉起刀指著王青的鼻子喊道:“你一定是剛才偷聽到我跟擎壽的話了,你撒謊”。“咳咳咳,”王青聽到她這麼說也笑了,“我什麼也沒聽到,咳咳咳”王青臉上帶著不甘心的哭笑:“你這麼問,是因為剛才那兩個人也把他們捲來的錢藏在老墳塋了吧?天意,果真是天意,都是現世報兒。哈哈哈哈……”王青突然發狂似地大笑起來。玉麗突然衝過去對著王青就是一頓的猛刺。玉麗刺地越瘋狂,他就笑得越厲害,直到漸漸沒了聲音……
玉麗攤在地上,等了片刻,她頹然的站起來。茫然地環顧四周,地上除了血還是血。她愣愣發了一會兒神,像是打定了主意。她將四具屍體都拖在一起,然後走到角落裡,將一小桶一小桶的火油開始潑灑。十幾桶的火油都潑完,她又環顧了一下四周,臉上的神情變了變,向外走去。站在地窖出口的樓梯,她探出頭看了看,炕上,地上,被子上早就淋滿了各種油,甚至是菜籽油都淋的到處是——她不知道菜籽油能起多大作用,但是在她的印象裡,這些都能燃燒。她滿意的看了看,心裡盤算著:先點燃地窖,蓋上蓋子。到了院子再點燃屋子。她知道那個樹林子,也知道有幾個老墳塋。她彷彿看見自己美好的未來,不由得臉上露出了笑意。“刺啦”一聲,她滑著了火柴,臉上掛著得意的笑,將火柴扔進腳下的地窖。地窖裡的火慢慢著了起來,她滿意的看著火苗,伸手扒著木箱蓋子,一隻腳邁出,手一用力,剛要邁出另一隻腳。突然手腳同時打滑,人跟著滑進地窖的同時蓋子也被自己蓋上...腦袋咚咚咚地在樓梯上撞了幾下,她滑到了地窖,意識漸漸模糊,她心裡想著:“我要是別撒菜籽油就好了,不會這麼滑……”
頃刻間,一聲爆響,地窖蓋子被熱浪炸飛起來,火舌順著木箱噴出,房子瞬間也跟著著了起來。天早已朦朦亮,兩邊的鄰居也被地窖的爆炸聲驚醒,跟著好了起來:“著火了,著火了……”時間不大,周圍的居民都拿著家把什向這邊靠攏,叫喊聲,孩子哭聲,狗叫聲……一片嘈雜。只有一隻火紅的狐狸,趴在附近地牆頭,默默的看著這發生的一切。在火光的對映下,她的眼裡似乎有淚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