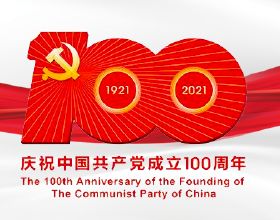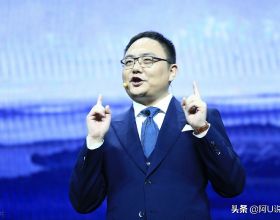我小時候在學校裡聽老師說,“讀書讀了十多年,考了個獨輪駕駛員”,覺著很好玩,一進家門就朝爹嚷,爹聽了臉上就布上一層霜。爹正用獨輪車滿載了一車黑紅飽滿的高粱穗子回家,後面跟著娘,娘腋下夾著一抱青草。爹問:“誰說的?”我說:“老師說的。”爹“啪”的賞了我一耳光,說:“老師是讓你記住要好好學習,否則你瞧,就要駕獨輪車。”我被打蒙了,兩眼是淚……晚上,我用絕食抗議無緣無故地捱打,爹幾次試圖給我玉米麵窩頭,我都憤然拒絕,爹便長長地嘆口氣,扔了筷子走出去。娘拉過我說:“你這不是揭他的傷疤嗎?你爹整整讀了十二年書……”從那時起,我知道一個男人也有受傷、脆弱的時候。我去勸爹,我說:“爹,吃飯吧,我會好好學習的。”爹突然拍拍我的肩膀說:“兒子,獨輪車不用你駕,你爹會駕好的。”
爹把駕好獨輪車當成自己的責任,他要像當年老百姓用獨輪車推出一個大勝仗一樣用車子推出一個好日子,推出我平坦的上學路。
我的家鄉屬於丘陵地帶,往地裡運土肥、播種、收穫都離不開獨輪車,所以這車子是家家必備的工具。有些人家的男人只知道用,不知道保養,每到三秋大忙時節,從山地裡來回推不上幾趟棒子車子就散了架,鬧起了罷工。還有的人家的車子,正載著熟透的穀穗吱呀呀唱山歌時,膠皮車輪嘭一下爆了,搞得狼狽不堪。爹的車子卻從沒有發生過這類“笑話”,這是爹的驕傲,爹說:“咱這車子,架子是楸木的,輪子的氣也充得不多不少,哪像他們呢……”爹每次推車下地前都要像飛機起飛前地勤人員仔細檢查一樣,把車子的細枝末節都過目一遍,緊緊鬆了的螺絲,給車輪的軸承上黃油,爹說:“這輩子還全靠它呢,不寶貝著咋行?”
可是就是爹如此寶貝著的車子還是和他開了一個心酸的大玩笑。那年,爹想為家裡起三間新房,自己老馬似的開始了“備料”,打地基用的石頭,村東的溝裡就有,爹就地取材,開始一車一車從溝底往上推石頭。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個星期天,我自告奮勇為爹拉車,爹很高興,車子上就多裝了兩塊大石頭。爹噗噗向手心裡吐了兩口唾沫,把車襻搭在後脖頸上,嗨一聲拾起車把,這樣我和爹便啟程了。爬一個很高的坡時,我使勁在前面拉,脊背幾乎和坡路平行了,爹也使出了吃奶的勁,當爺倆像弦一樣繃緊在山坡上時,突然嘎嘣一聲,車襻斷成兩截,爹還沒反應過來,身子往前一送,牙齒正磕在車子中間高起的平脊上,兩顆牙就飛了,車子倒在了路上,我回頭看著爹滿嘴鮮血,恐怖得大哭起來。爹安慰我說:“沒事的,只要你好好學習,將來開上四輪汽車,爹就不疼了。”我哭著說:“我一定要好好上學,長大了用汽車拉石頭,還拉你去北京玩。”然後,我看見爹捂著嘴點點頭,殷紅的血蚯蚓一樣從他粗大的指頭縫裡不斷湧出來……
如今,農村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家家種地都是機械化,播種機、收割機、輕便的電動車、大馬力的三輪農用車等等,連出行都有了各種牌子的轎車。遺憾的是,雖然日子早已像鮮花盛開一樣美麗,我也早已有了自己的轎車,卻一直沒有兌現帶爹去北京的諾言。後來爹突然逝去,帶走了我孝敬他老人家的一切機會。
我把爹曾經鍾愛的獨輪車安置在後院裡,每次回老家都去看看它。這時,目光裡又會出現爹彎腰弓背推著獨輪車負重前行的影子。其實,我們的好日子,不正是一輩輩人,不辭勞苦,奮力爬坡過坎換來的嗎?
責任編輯:謝宛霏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