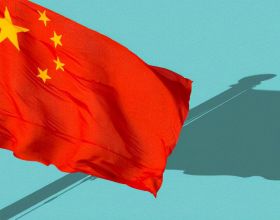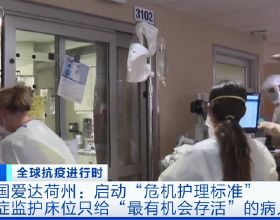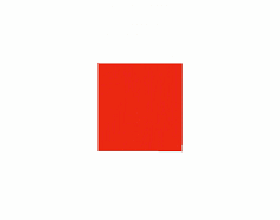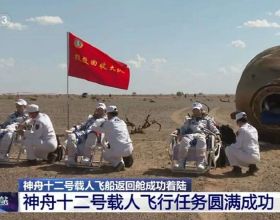嘉靖年間,明朝建立已經一百餘年,天下承平日久。在北部邊境,寧夏、宣府、大同等九個軍鎮牆高濠深,兵將眾多,擔負防禦蒙古部落侵擾的重任,被稱為“九邊”重鎮。
但從嘉靖三年開始,九邊之一的大同軍鎮,叛亂迭起,甚至一度勾聯塞外部落入侵,幾乎復刻唐朝中期安史之亂。為何相隔千年,邊疆軍鎮同樣在帝國中期爆發叛亂?這其中既有偶然性,也有歷史的必然性。
在北方邊境,北方蒙元勢力不斷入侵,劫掠內地,甚至深入京城周邊,明朝君臣不勝其擾。土木堡之變,讓明朝喪失大量野戰精銳部隊。隨著時間推移,明朝中期以後,邊境完全採取防禦政策,逐漸形成以“九邊”軍鎮為基礎的堡壘防禦體系。
朝建立以後,朱元璋吸取前朝教訓,大力整治國家軍隊,在全國建立大大小小數千個衛所,規定軍人作為軍戶,世代從軍,父死子繼。而不同於唐末的藩鎮,軍鎮都由文官巡撫、御史節制管理,避免邊軍尾大不掉,為害一方。但看似穩定的軍鎮防禦體系,實則暗藏動亂的禍源。
一是衛所軍戶制度延續百餘年,積弊叢生。以大同軍鎮為例,雖然文官巡撫掌握軍鎮上層權力,但始終透過總兵、都督等世襲武官控制兵卒。但世襲武將長期壓榨軍戶,刻薄嚴厲,不體恤底層軍人,對下毫無威信。
而塞外遊牧部落長年侵襲,軍戶長期擔負軍事鬥爭任務,作戰死傷相藉,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即使沒有戰事,又要負擔沉重勞役,築城浚濠,異常艱辛。平常,還需要應付軍官臨時差遣,為其耕田勞作、起屋架樑,幾乎等同於軍官免費的奴隸。軍餉剋扣更是常態,底層軍人僅能依靠祖上繼承的微薄軍墾屯田維持生計。
在被普通民眾鄙視的情況下,窮困軍戶大多隻能相互結成姻親,利益關係緊密,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涉及到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就容易誘發群體反應。這種落後的軍事奴隸體制,充滿了壓迫剝削,是導致叛亂的重要因素。
但反觀九邊軍鎮情況類似,卻只有大同鎮,從嘉靖三年至嘉靖十二年,發生大小叛亂暴動七次,延綿近十年。這其中,自然也有事件爆發的偶然因素。
二是大同軍鎮內部的偶然事件,直接導致叛亂不休。嘉靖三年,巡撫張文錦效仿宣府鎮,在鎮城外圍建立小堡壘,形成攻防體系,防止蒙古部落直接攻擊鎮城。但張文錦忽略了底層軍戶的想法,強制命令,直接從鎮卒中抽選二千戶,遠赴堡壘駐紮,造成恐慌情緒。
鎮卒普遍認為,遊牧部落入侵難以抵擋。遠離大同的高牆保護,在堡壘中駐紮,與送死無異。
因此,試圖向參將賈鑑請求,收回駐紮命令。參將賈鑑是當時世襲軍官的一個縮影,將普通底層軍戶視同豬狗奴隸,毫不體恤,限期完成五個堡壘的修築,稍有遲緩,便鞭打笞杖。根據尹耕《大同平叛志》的記載,參將賈鑑甚至在工期緊張的情況下,勒令軍戶開墾周邊荒田,作為日後自己的私家田莊,以便增加收入。
矛盾更加激化。鎮卒們在身家性命和朝廷法度間,果斷選擇殺死參將賈鑑,逃竄到周邊荒山聚眾自保。隨後,巡撫張文錦因為懼怕叛卒招引塞外遊牧勢力,派人招撫叛卒入城。但未曾想,被叛卒聚眾圍攻殺害。
第一次大同叛亂徹底爆發,是為“五堡之變”。隨後,在朝廷招撫下,逮捕處決了首犯四十人,叛亂平息。此時,大同叛卒只是鎮卒中一小部分,也僅僅是反對遷移,並不想發動長期叛亂。
三是叛亂的種子始終未曾根除,相互不信任導致叛亂再起。嘉靖十二年十月,大同朔風凜冽,天寒地凍。為防止遊牧部落侵擾,總兵李瑾提議清理大同鎮城外的濠溝,獲得大同總制大臣劉源清的同意。
歷史又再一次重複,李瑾並未吸取九年前的教訓,仍舊限期三天疏浚四十里濠溝,對鎮卒動則鞭笞。相同的情形下,備受苦楚的鎮卒再次聚眾叛亂。總兵李瑾被殺,巡撫潘仿被逼逃走。此時,總制大臣劉源清一意孤行,認為九年前五堡叛亂處置太輕,才導致叛亂再起。因此,劉源清派兵攻入大同南城,大肆殺戮。原本只是數十名叛卒鬧事,聚眾劫掠。但在屠城的恐懼之下,大同鎮卒被迫響應,關閉城門,反擊朝廷軍隊。
四是地方和中央之間溝通不暢,使得叛亂難以平息。總制劉源清派出巡邏隊,攔截大同鎮發往北京中央的奏章。
大同軍鎮內部難以得到朝廷直接指示,加深了對城破屠城的恐懼,只能加強防禦。而在朝廷的一再過問下,劉源清仍舊斷言,大同全鎮叛亂,沒有招撫必要,必須破城剿滅。國家行政系統效率低下,上下溝通不暢,讓這場叛亂遷延日久。原本數十人的暴動,一步步演變成整個大同軍鎮的大規模對抗,進而導致塞外遊牧勢力趁機入侵。
官吏苛刻,上下關係緊張,是叛亂的背景原因。不顧現實情況,肆意壓榨,危及士卒生命,是叛亂的直接導火索。而歷次叛亂中被殺的鎮卒,親屬故舊仍然在鎮城生活,復仇心理與日俱增,背叛與陰謀始終籠罩城市。
繼任官員試圖清算前賬,稍有動靜,屠城的謠言就不斷髮酵。官府與大同鎮卒間互不信任,由此導致降而復亂,是叛亂不止的深層內因。大同軍鎮在嘉靖年間的屢次叛亂,與唐中期安史之亂一樣,都是封建王朝中後期,社會矛盾累積、國家體制腐朽的突出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