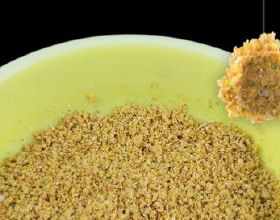三 不落夫家與矢志不嫁
夫家苦,母家樂,所以要不落夫家。關於身在夫家之苦,《吳小姐憶母怨夫四季解心》唱道:
自從二九離閨閣,多少艱難到至今。嫁夫指望憑高貴,點想人家把我當泥塵。鳥陣投羅難脫網,百般無一遂平生。
以文堂《十思起解心》:
四思起,怨過天知,不堪回首個薄倖男兒。妻憑夫貴從來事,恨我才郎不三思。自古嫁夫真受氣,拍壁無塵實惡持。家計蕭條無所倚,丟奴日夕冇心機。一日三秋從古語,難望鍾情快樂時。
而未嫁做女之時則是“在家萬事有心機”,尤其金蘭相處之樂:
曾記得在家逢日午,同群姊妹樂芳辰。春景同遊芳草地,夏賞荷香納悶心。秋飲黃花新美酒,冬來白雪共聯吟。
七思起,在家時,結拜金蘭個位彩姬。二人日夕同觀戲,拖■攜手甚開眉。今日嫁郎分兩地,點能聚首見相知?
為了能與金蘭相知長聚,已婚女子遂不落夫家,所謂“儂本無情郎自苦,來是空言去絕蹤”。而面對“有妻不若無妻,之子宛然處子”的現實,丈夫們總要盡力加以改變,其結果則是因人而異。《新婿上廳》中,寒酸的新女婿到岳家請妻,受到岳父母的冷落譏斥,憤極,表示妻若不回就將公堂相見。妻子氣昏在床,醒來後與金蘭泣別道:
我立心割捨迴歸去,拚條殘命死在佢手中央。人生自古誰無喪,免在外家連累天含娘。為然恨到知我歸陰府,姐你親到我屍前另一注香。
金蘭好言寬慰:
願你夫妻同保全,自然到時地久天長。
《拆外母屋》中,丈夫雖貧但有會友相助,岳家雖富但岳父已亡。夫妻成婚已有3年,妻子卻一直
偏戀金蘭不顧羞。貪圖結交個的同年友,盡把唱隨情義付水東流。
每天“孤枕冷清清”的丈夫忍無可忍,便率一班會友各持磚石來到岳母門外,將屋瓦砸壞。眾鄰圍觀,均言男方有理,勸說將他招贅入門。岳母訴說了自己無兒的苦處,表示願意,事情也就算是得到了解決。不過贅婿並未完全放心,暗想道:
等待數天和半月,若無實事另行求。然後請差來押佢,勿怪我短情薄義結冤仇。
而在《打爛■》中,丈夫則是獲得了一個完滿的稱心遂意的結局。開始見自家丫環去請妻而妻不返,他“氣難當,登時發怒走歸房”。心想此婦“開口就話相知留挽住,難道攪家潑婦垂惠得過才郎?”就一怒之下把臥房裡的■箱氈帳打爛,岳家知道後怕出事端,便將女兒送回。見妻子已返,丈夫倒也能剛柔相濟,枕蓆之間鸞鳳和諧,
久別同歡暢,今宵情景都垂好過做個晚新郎。
不落夫家有不同的情形,最徹底的是終身不返,有的幾年、十幾年後特別懷孕生子後則返,還有的則為時更短,歸寧稍久即返夫家。所以這一現象是有風俗基礎的,即各地普遍存在的回門歸寧之俗,此俗與程度不等的金蘭契誼相結合,也就造成了時間不等的不落家。
自梳不嫁比最徹底的不落夫家還要決絕,她們根本就是拒絕婚姻。本批龍舟歌雖無關於自梳的具體描寫,不過從《玉嬋附薦金蘭》、《玉蟬問覡》等篇所表現出的金蘭情誼來看,她們的心目中毫無男子的位置,即便不儀式性地自梳也很可能會終身不嫁的。戲與曲的形式比較接近,以文堂刻廣州地方小戲《奶媽二做偵探》中的不嫁女這樣自敘道:
想起十九歲個年,老母監我嫁。個只衰鬼豆,睇來鬼都怕。手指似蕉蕾,我情願守生寡。故此出省城,詐話探契媽。立實副心腸,一實搵工打。老公唔駛嫁成個,一味系散■。契番個相知,得閒磨磨嚇。
此女是去做梳頭女傭,即媽姐,這是清末民國間自梳不嫁女樂於選擇的一種謀生方式。
矢志不嫁者還有出家為尼的,這與金蘭契不同,行為者不但拒絕男女之情,而且拒絕女女之情,不過她們對異性的厭拒同樣適用於金蘭女。《秀容掃琴南音》中,陳氏秀容年已二十三歲,她把出嫁成家視為“人在囚籠”:
我想嫁郎至好為官宦,富貴由天不過日月咁川。重有嫁著淡泊個鈞上與求乞賞,個場悽楚你話幾咁交關?
見父母將自己的親事定下,她
憂多食少芙蓉變,惱傷蘆梢保命在全。山茶白膳難沾食,淚滴藍蹄灑落肩。日開夜閉無言語,猶如啞仔食著黃蓮。
為求解脫,秀容“一心指望投清靜,意欲削髮為尼入寺門”。當然,出家為尼也不是不可以和金蘭契相結合。此種情況可以發生在愛友亡故的金蘭女身上,為了將曾經的感情永遠留住,出家食齋倒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玉蟬嘆五更》中玉蟬即曾自思道:
自系愛友歸陰奴亦淨守,花前月下懶去行遊。意欲捨命伴隨嬌左右,獨系慈顏蒼老唔知向己誰周。不若等待慈親歸世後,為尼入寺把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