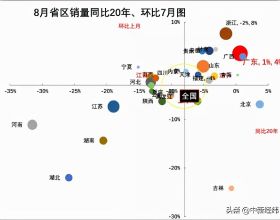一
潁河是一條發源於河南省,流入安徽省的不大不小的河。一個村子三面臨著潁河,陽光一照,河水銀光一閃一閃——叫銀河村。
潁河環繞村子而過,有一種宜人的美,也使村裡的孩子門有一個夢似的童年。寬大的河谷裡繁茂的樹木,高而密的蘆葦,深深的青草。天將黑時,每個孩子推著一輛用軸承做的小推車載著沉甸甸的青草,排成一長隊,“嘟嚕嚕”極威武。潁河沙極多,夏日孩子們每天割草都去水裡洗澡,然後光著身子躺在沙灘上撅著小雞曬太陽、玩沙,極舒服。若河對岸也有孩子們,一方就先挑釁道:“河那沿的孩兒,靠你姨!”對方就接腔了。罵著罵著就用坷拉、石子,互相砸起來。如遇水淺,強的一方就攻過對方去了,將對方直追到對岸河谷之上。在這種快樂的打鬥中,也確實磨練出了他們一些人中的梟雄膽,確立了他們的“領袖”地位,為他們長大後當村長、支書打下了牢實的基礎。水牛就是典型的一位。他勇猛、利索,壞點子又多。他曾在他姥孃家將他姥孃的尿盆底偷鑽一小窟窿,使他姥娘晚上的尿一滴不剩都流到床上。
有時兩方的孩子們都在水中洗澡,發生矛盾,人少的一方吃了虧,但大人忽然出現,人多的一方便嬉笑著躥到岸上抓起各自的褲頭,一邊嘴裡連聲罵著一邊拼命往河谷上跑。
最重要的是這條潁河養著銀河村人。潁河使銀河村的田地常年肥沃,莊稼年年豐收。銀河村裡的再窮的戶也不愁吃喝。現在是新社會,人人都有責任田,誰也奪不走。
水牛一幫孩子長大當了村支書,剛好趕上全國各地爭相建大樓,這裡夢一般的林場、蘆葦、深草便都不見了,出現了沙場。隆隆的機器響著,兩岸只會下死力的壯勞力赤著膀子為賺一點血汗錢汗流著,沙就盡了,成了一個個大坑。河對岸的河坡裡已栽上了整齊的果樹,銀河村如果效仿,彎彎的三四里的寬大河坡準能富了銀河村人的腰包,可有誰管呢?人家支書早富了,說:“村裡人就是真都窮死了,也窮不著俺。”
孩子們不割草了,牛羊都有家裡其他人牽出來放。他們的任務是捉幼蟬,捉住了賣給小商店,兩個一毛錢,收入挺可觀的,現在城裡人山珍海味吃膩了。或到河對岸人家的林子裡捉斑鳩,五元錢一個,收入更好,兩岸的孩子們已不打架了。
二
走上河谷,順著田間小路不上一里,就是銀河村。打這裡路過的外村人都誇這裡的樹極多,枝連枝,杆扯杆,鋪天蓋地,鬱郁蒼蒼。美麗的樓房河非樓房然而依然高大的出前簷房掩映其中,好一幅恬靜富裕的鄉村圖畫。其中村東一戶新宅院裡有兩棵大白楊格外突出,其高其大如鶴立雞群。這兩棵大白楊不是這戶人家的,是前任支書水牛的。然而誰又敢動這兩棵大樹呢?上元村他的乾親家黑天的小樹長在路中央,誰又敢動一點皮呢?黑天是這一帶黑社會的大頭子,人提起來就害怕的主兒。
像現在只講究外包裝的商品一樣,村裡的好房子都建在村子周圍。當然大都是些富戶。其中有村幹部、半邊戶、商人等。當然最漂亮的要數現任支書大林的樓房。佔面積最大的要數水牛的。他一個宅院佔兩個宅院的面積,雖不是樓房,但寬大闊綽的大平臺房更顯威風。灰米石罩牆,遠遠看去雲蒸霧罩的,如盤踞著一條龍。水牛家有條德國大狼狗,大林家大門樓裡邊也拴著一條純種而訓練有素的大狼狗。他們敞著大門不在家,誰人也不敢越過一步。那伸著血紅的大舌頭徘徊的在大門內的大狼狗看著你,嚇死你。現在土頭土腦三十多歲的婁義正愁眉苦臉地蜷縮著身子蹲在大林家門外。他是來找支書打官司的,支書年輕漂亮的老婆極不耐煩地說不在家。他來好幾次了,支書明明在家……。吃得肥胖的大林此時正躺在床上養膘。他正苦思冥想著怎樣才能和村裡一位青年作家搞好關係。這位作家可是市委裡都有人的,要不怎麼會成為作家?可是那作家對他總是不即不離。
婁義終於等出了穿著大西裝,瞪著眼的支書。支書怒道:“走吧,要不是這樣,扇你的臉!”婁義說你隨便,說著他們倆就一路驚飛著雞,踢開著豬隊,一起往村中走去。
他們越往裡走,房子越矮、越差。村子正中還有不少土牆破瓦房,大概他家就在那裡。
村中心有個大池塘,供村人洗衣裳用。每天有花花綠綠的姑娘、媳婦、半老太婆圍在那裡。水中心有群大白鵝和鴨子在遊。有棒槌聲傳得老遠。池塘裡的水大都是下雨的積水,真旱時,就從河裡引來。
村裡人極羨慕河北岸化莊村的村道:“看人家的村道,大道小道,橫道豎道,筆直筆直,看咱村……走著走著就找不到路了。房子蓋得七歪八扭,也不知怎麼規劃的,就這說拆誰家的房子,就得馬上……。人家化莊村道旁還有下水道,一下雨,水就流走了。看咱村,一下雨就吵嘴打架,因為水流不出去。”婁義就是為這種事找支書的,他家的房子快被泡塌了。婁小刀家總是墊得那麼高。
三
村裡的頭面人物、聰明人,不叫頭面人物、聰明人,叫“光棍兒。”這光棍兒當然不是光身漢的光棍兒。光身漢叫老實蛋、眼子頭、沒成色。村裡的光棍兒有現任和前任村幹部、賺了錢的商人、中學教師、小學校長、半邊戶和會兩下拳腳身手不凡有一定勢力的地皮流氓無賴。光棍兒的大小由他們的本事、聰明程度而定。光棍兒越大就越懂禮節,村裡的紅白喜事都請他們去陪客或主事。
水牛和大林是頭號光棍兒。現在水牛的光棍兒似乎沒大林響了,因為大林是現任支書。大林剛當支書時,水牛為自己在村裡的地位稍降,很是憤恨,連結他的舊黨曾想把大林轟下臺去,到處張貼大林貪汙的款項名目及數目,和大林打官司。大林上了臺必然要提拔他的人。水牛相好家的電工給撤了,大林的小舅子上了。小舅子愣頭愣腦的,都叫他村舅。每當村舅晚上去村東頭,水牛一夥就在暗處用磚頭砸他。他氣得衝黑夜大叫:“我可不興來你們村東頭了!”這時候他不敢罵,雖然他在村廣播上罵民眾雞巴、球。因為他知道欺負他的是誰。大林在武力上不敢和水牛碰。水牛多武啊,從來都是打架的班頭,十里八村乃至全縣都是有名的,世稱一隻虎。水牛當支書時,一天在他家喝酒,大林和電工忽然鬧了起來。起初大林很橫,躥著要打電工。水牛惱了,掂了杆獸槍就照準了大林,大林一下子就懵了。
大林不是在村裡長大的,是在他外婆家,一回來,就進了村委,村裡人都說他上邊有人。
大林和水牛不知何時就和好了。村裡人都見他坐在大林的摩托上,大林帶著他,他們倆很是親熱的樣子。
這也許是他終於找到了穩固他社會地位的法門。他也像水牛一樣認了一個黑社會大頭子,足以和黑天抗衡的乾親家。這乾親家還是一個鄉的副鄉長。據說是因為他太橫,鄉里管不住他,才給他這個頭銜約束他的。
水牛當支書時極闊,那時鄉里的小汽車還極少,就是鄉政府也……他就用八千元錢買了輛八成新的“小麵包”,漆得雪白雪白,很新。他坐裡面去鄉政府開會,都還以為是什麼大官來了呢。水牛腰裡極有力量,搞過村裡好幾個女人,有小媳婦,也有大姑娘。有人看見就他和一個媳婦在茅廁裡就搞上了。他去電工家找電工媳婦,電工一見他去,自己就出去了。村人暗裡都說,電工還為他看大門,那是臭電工的。
有一點還是好的,如有外村人和銀河村人發生矛盾,水牛總是儘量護著他的臣民。
水牛也是因為打架下臺的,因為那一次他打的不是家兒。後來好不容易搬動了縣長趙大恆,才擺平此事。但據說為此連黨籍也給開除了(其實沒有開除),還上了電視以示警告。
水牛常微笑著對人說他當支書時也有一點功勞,那就是他將村小學從村北拆建到了村南,然而其中的鬼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因為村南有座廟,他想讓廟裡的神靈保佑他當一輩子支書,地位永固。況且他拆的村北那棟樓還不破舊,稍微一修就會相當漂亮。
學校拆建後,村裡一些光棍兒迷信的親孃老婆們在那裡跳大黃旗燒香,引逗得小學生們一下課也學著打躬作揖——那廟就在校園裡面。
四
婁厚德是以最仁義厚道著稱的光棍兒。生產隊時,他在村裡做會計,最是精明會算計,他在村裡輩分相當高,五十來歲就有小孩子叫他太太(高祖父、目的通稱),村裡人都讓他三分。
自古以來夫貴妻榮,光棍兒的老婆自然也是光棍兒。婁厚德的老婆也是這樣,說起話來像狗咬架:“撞!撞撞!撞撞撞!”極霸道。彷彿她說出來的都是真理,別人都得聽她的。其實她連什麼是理都不知道,她還偏愛給人出主意、管閒事。叫喚的狗並不能咬人,咬人的狗不叫喚。水牛的老婆就不這樣說話,人家說話總是、慢聲細語的,可是水牛當支書時,好多事都是她背後……
婁厚德祖傳家底厚,一家人也都很勤勞,屬於踏實能幹的人。平時很仔細,他老婆從來不吃饃,衣袋裡總是裝些紅薯幹,餓的時候就掏出一塊。兩口子都不愛坐凳子,怕磨爛褲子,不管去哪裡都蹲著。他們又極愛面子,兒子結婚時,待好多好多客,肥雞子大鯉魚,比哪家的桌席都好,把平時積攢一揮而空。
婁厚德在外面是光棍兒,那麼在他的家族內就更不用說了。子侄輩大事小情都找他去請教,老一輩遇事也找他。他也常為此而洋洋得意,更不希望家族內有人比他強,他自己以為也不會有。他也希望他的家族內誰家的資訊他都知道,有利可獲時就可以插一腳,人家事情失敗時,他可以敏捷地往一邊一閃,說沒他的事,還是人家不中用。他自家的資訊從不外傳,遮得很嚴實。就是 村裡其他人家的事情,他也是千方百計去打聽,從中取利。看哪家有點冒尖的苗頭,他就上了。因此他們兩口子總是顯得鬼鬼祟祟。他在外交上採取的是對自己至親不看不顧,對不太親的和外人特別是光棍兒設法籠絡的策略。因為他的至親,不用怕會丟掉,親的畢竟是親的,凡事也離不開他,如他的殖民地一樣。別人就不同了。他和村裡的光棍兒,有點冒尖的戶差不多關係都很好。他們兩口子最討厭他們的親侄子婁小刀,說婁小刀算啥光棍兒,賴皮光棍兒!婁小刀是四號光棍兒。
他對婁義這種人就不同,因為他看婁義這家人那一身身窮酸氣、窩囊氣,一輩子也沒有一點用。一次婁義的老婆不小心讓自家的羊吃了他家田裡的菜,婁義老婆喊著他老婆嬸子,他老婆還是拽著人家的羊一邊狠打,一邊百不中聽地混罵。
按說婁厚德是水牛的人,平時又與大林沒什麼來往,但是有一天一個無賴光棍兒家為生孩子待客,大林喝得酩酊大醉,婁厚德扶他回家。一路上大林深怪婁厚德,幾乎哭了說婁厚德看不起他,婁厚德兒子結婚都沒有給他說一聲。那一天大林從婁厚德家大門前過,看見水牛也在那裡,還有穿得嶄新的作家。可是婁厚德都沒有叫住他讓進去歇會兒——作家是婁厚德的堂侄孫。
婁厚德心裡熱乎乎的,自己能被支書這樣看重,人家畢竟是支書。
五
時有哪家的牛“呣——嗎——”一聲,鉤天掛地,以顯示濃厚的鄉村氣息。
銀河村的街很清靜,有時一兩個穿著時新的年輕人騎著新車或提著包步行進村,就有長者親熱地與他們招呼:
“抓錢的回來了?”
“回來了,抓啥錢啊。”年輕人禮貌地下車,謙遜地說。
村裡有許多年輕人都在河北岸的化莊村或城裡打工。村裡人都羨慕死了化莊村人,嫁閨女都願往化莊村。化莊村人賺錢的門路多,支書會管理,只一河之隔就不一樣。人家村有毛髮廠,冷飲公司,而他們銀河村……。銀河村人也知道找門路賺錢了。讓他們明知道考不上學的孩子都下學,出外打工去。銀河村人都不希望他們考學沒希望的孩子念太多書,唸書多了太正經,太正經的孩子沒出息,還不如讓他們學得既調皮又搗蛋,這樣的孩子長大能當大光棍兒,像水牛,還有村長。村長小時候都叫他“驢糞蛋”。因為驢糞蛋外光裡不光。
村裡卻有一位年輕人,整日坐在他的小平房裡讀書,目不窺圓,剛興打工的時候,他是最先的一個,可一段時間後,回來依舊坐屋裡讀書,足不出戶。以後也時不時地出外打一段時間工,跑一點什麼事。他出來時打扮得總是整整齊齊,文質彬彬,無論怎樣看都與村裡其他年輕人不太一樣。讀者諸君猜對了,他就是支書日夜想接近的作家。
村裡人起初都不知道他是作家,更不知道他整天關在屋裡幹什麼。人家都出去掙錢了,他卻秀妮兒一樣。有人笑說秀妮兒,秀啥呢秀,秀針呢?後來許多人都知道了他是作家,但淳樸的村裡人也不知道作家到底是幹什麼的。
最初知道他是作家的當屬精明的支書大林,然後是常去支書家巴結的四號光棍兒們。
原因是村裡裝了電話,裝在支書大林家。大林家自己不但有BP機,而且還有大哥大。他家的大客廳極闊,矮櫃上兩個瓷花瓶一米多高。當然支書家的電話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去打的。作家是因為急事,又不願去鄉政府所在地掏錢打,他兜裡也實在羞澀,並且也遠。就涎著臉去了支書家。支書老婆當然不高興,兩家又從沒打過什麼交道,可都在村東住,何況作家總是體體面面。幾次電話後,支書就知道了他是作家。並且聽出來他竟還和市委……。以後支書在鄉政府開會又聽另一個村的支書說他曾在外村給學生講過一節課,還推薦一個學生的作文登了雜誌。以後作家去支書家打電話,支書兩口子便笑臉相迎。作家的電話自然多。
可是作家總是打完電話就走,從不說自己的事,大林作為支書也不好追著人家去問,苦惱得大林……
村人看作家常去支書家,打電話極順,作家在他們眼中便也成了大光棍兒。婁厚德兒子結婚時,作家在車上卸嫁妝,水牛在下忙接,一改過去睨著眼看人的習氣,笑說:“潁文卸的我會不接?”作家的名字叫潁文。水牛也知道了他是作家。
作家的父親生產隊時在村裡當團委書記,後來當教師,但性情老實、軟和,為村裡的三號光棍兒。水牛當支書時,他家辦事也很難。
作家根本不願當什麼光棍兒,更不屑與這些光棍兒為伍,把他們視為貪官汙吏,流氓土匪……看來水牛大林只能是野地裡烤火,一面熱了。
作家家辦喜事,他們趕緊將大禮送上。作家打長途電話,大林趕緊用鑰匙扭開,放在那裡等著。作家未婚,大林的老丈人馬上到婁厚德家聯絡,要為作家……
…………
一天半夜裡,婁義從支書家出來,踉踉蹌蹌走在村街上吆喝:
“咱們銀河村——,咱們銀河村——,咱們銀河村都是老綿羊——。咱們銀河村——,咱們銀河村功勞可不小——。咱們銀河村——,咱們銀河村——,咱們銀河村——”
聲嘶力竭,瘋瘋癲癲,哀哀泣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