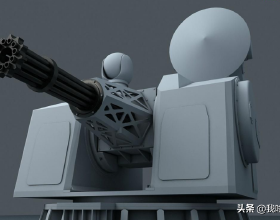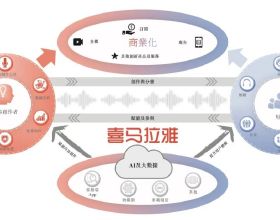導語:
留守,本意為居留、駐守、看管的意思,現在把許多因丈夫出去打工而留在家中照顧老人和孩子的婦女成為留守婦女。提起留守婦女我們的印象裡多是一個無助、孤獨的形象。
隨著我國現代化程序加快,大多農村富於勞動力為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都選擇了外出打工,可是妻子因為孩子的拖累,加之老人需要照顧而不得不留在家中。這些留守在家裡的婦女,自己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精力,忍受著寂寞和孤獨,有時還得不到理解,她們的身心在漫長的歲月裡,有可能會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現實社會中是繞不過去的。
我曾在鄉鎮工作了10多年,在這些年中,我接觸過許多的留守婦女,我知道她們的心酸,也懂得她們的苦悶,但我實在也幫不了她們多少,只是盡心盡力地為她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們不在乎苦,也不在乎累,只是那份孤獨難以釋懷,讓我們走進他們之中,看一看她們都有些什麼想法。
一、36歲的小梅說,丈夫離開家已經兩年多了,過去每年都是春節時回來待上半個多月,這兩年有疫情響應號召,春節也沒回來,雖然心裡怪想他的,可這也沒有辦法,我已經習慣了,只不過這次時間有些長了。
小梅和丈夫結婚十二年了,如今女兒正在讀小學四年級,家裡離不開人。兩人是打工時認識的,結婚後,小梅就沒有出去打工,留在家裡照顧老人,生了女兒後就更不能去打工了,現在在家裡開了一個小百貨,維持日常開銷。
其實,作為留守婦女,小梅相對生活還是很不錯的。丈夫打工會準時把工資寄回來,她在家有自己的小攤子,雖然掙得不多,維持日常開銷還是足夠的,所以她沒有因為錢的上面發過愁。她的煩惱在於村裡的風言風語,她開的小商店,人來人往的,難免多接觸一些人,對待來買東西的客人,勢必要熱情一點,有的人來得勤了,有時會說上幾句玩笑。可時間長了,就傳出了一些謠言,說小梅和誰誰好上了,這個她實在是受不了,可是生意還不得不做。
小梅無奈地說,這些不是我能管的,我只能做好我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謠言總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當談起丈夫,小梅說,他在外面也是很辛苦的,我出不去,就把家照顧好,誰家不都是這麼過來的,現在就是實實在在過日子,把女兒養大才是最主要的。
二、楊凡是從外地嫁過來的,人長得漂亮,身材也好。8年前,楊凡跟著丈夫去了四川,去做生意,後來由於被人騙了,本錢都賠進去了,無奈之下,只好給人打工。
後來因為懷孕,回了老家,丈夫和一位老鄉去了廣州,想要在那邊合夥辦個物流。臨走的時候對楊凡說,等那邊安頓好了再讓她過去。可是這一去就是三年,始終沒有回來接她。
她說,“我和丈夫在城裡做生意的時候,我的丈夫對我特別寵愛,我覺得我很幸福,那段時光雖然短暫,但我體驗到了什麼是快樂。楊凡回憶過去臉上露著甜蜜的笑容。但面對現實,還是難以掩飾蒼涼和尷尬。
現在這裡的土地大多退耕還林了,地裡的活計並不多,其實不算很累。楊凡說,心裡的苦悶主要來自心理和生理上,丈夫不在家,又與丈夫缺少交流,在心理上沒有安全感。在生理上,長時間地壓抑自己,常常感到孤獨。
三、33歲的素娟,留守在家也是8年了。她的孩子現在讀二年級了,從孩子出生的時候,她就已經留守在家中,從那時起,她每年和丈夫在一起的時間絕對沒有超過20天的時候。
當我問起她是否想念丈夫時,她的臉上帶著笑意,她笑著說:“想啊,特別是在農活忙的時候,很想他回來搭把手。”雖然她笑得很溫馨,可我還是看出在她眼中還是有那麼一種哀怨。
33歲,獨守空房,雖能坦然面對,也是一種無可奈何。她說,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會想起遠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內心的孤獨還有難捱的寂寞總會讓我翻來覆去。白天還好,可以找些事來做,在人前的時候,還要裝成很淡然的樣子,其實,心裡是苦的。
四、45歲的雪姐也是一位留守婦女,只不過她忍受的時間更長,她自己也說不清究竟有多少年了,反正從生下兒子開始,到現在兒子都談婚論嫁了,她說現在對丈夫已經麻木了,她說要不是每年春節他該回來,我幾乎已經忘記他了。
這話看似是玩笑話,可是在雪姐心裡有著一種不甘,要不是有家庭維繫著,丈夫和陌生人又有什麼區別啊。嫁過來這麼多年,真正在一起的時間又有多少呢,恐怕是很可憐的。即使回來,在一起時雪姐還是有些抗拒丈夫的。
結束語:
人是有感情的,夫妻結婚後都想朝夕相處,時時刻刻在一起。但是為了生活,夫妻雙方天各一方,一年相見也就只有短短的幾天,這夫妻感情怎能長久維持。也正如雪姐所言,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對於留守婦女來說,真正苦點累點無所謂,真正苦惱的是不能長久相伴。在家庭生活中,誰都渴望一家團聚在一起,誰也不想忍受分離之苦。甚至有的忍受不了孤獨,搞起了婚外情,但婚外情的代價太大,如果被發現,家庭就會變得分崩離析,最終讓令自己和丈夫都受到極大的傷害的。
對於留守問題,到底有什麼好辦法徹底解決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