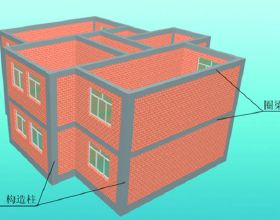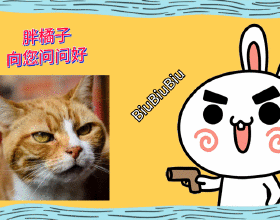1953年4月中旬,江西省公安廳給鉛山縣公安局下達密令:加強對殘匪黃道生的追剿力度“如難活捉,可以擊斃”。
不是江西公安部門小題大做,而是這個黃道生太難抓了。
黃道生有個綽號叫“三不到”。穿釘鞋走石板路,聽不到聲音。飛簷走壁如履平地,看不到身影。
一柄18斤重的銑山刀所向披靡,抓不到。銑山刀是當地人的叫法,當地百姓每年都要使用一把長刀,把杉樹或茶樹林中的雜樹、野草銑掉,所以叫銑山刀。只不過黃道生的銑山刀有些特別,連把帶刃有一人多高,18斤重,鋒利異常。
有一次黃道生恐嚇百姓,用他的銑山刀,接連將6棵碗口粗細的杉樹一刀兩斷。
黃道生是鉛山縣永平鄉橫溪村人,自幼頑劣異常,不喜讀書,卻喜歡舞槍弄棒。他家是當地有名的地主,有數百畝的竹林,黃道生是家裡的獨子,他父親對他寵溺異常,光是教武術的老師,前後就找了十來個。
黃道生相貌兇惡,身高體壯,但行動十分靈活,十幾歲就有了個“草上飛”的綽號。
黃道生十六七歲時,跟隨父親到上海經營竹木生意。
當時的上海灘魚龍混雜,沒過多久,黃道生就加入了青幫,很快成為青幫頭目張嘯林手下的金牌打手。並得到張嘯林的賞識,年紀輕輕就成為青幫的頭目。
張嘯林被林懷部暗殺以後,樹倒胡孫散,黃道生也帶著這些年積攢的不義之財回到鉛山老家。
黃道生回家後並沒有安心過日子,他把從上海灘學來的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都用在自己鄉親們身上。
開賭場、煙館、放高利貸、敲詐勒索,搶男霸女,無惡不作。
鉛山一帶盛產銅,黃道生又開始插手銅礦,一度逼得銅礦停產數日。黃道生這回算是捅了馬蜂窩,官府決定對他實施了抓捕。
國民黨鉛山縣縣長楊擺了個鴻門宴,邀請黃道生,在宴會上直接把黃道生給抓了。
結果當天晚上黃道生成功越獄,隨後他提著一把銑山刀血洗銅礦,砍死砍傷20多人。
楊慶珊一怒之下查封了黃道生名下的煙館、賭場。
黃道生夜裡找到楊慶珊,試圖和他理論一番,沒想到再次中了埋伏。
楊慶珊擔心黃道生再次逃走,用鐵絲穿透他的肋骨綁在壁板上,用繩子把他的手腳綁得結結實實,還派了4個人嚴加看守。
結果還是被黃道生弄破壁板,掙脫繩索逃走了。
楊慶珊在鉛山只幹了一年,他的繼任者名叫歐陽樊。
隨意楊慶珊的離開,隱匿半年多的黃道生重出江湖,歐陽樊比楊慶珊要高明一些,他沒有再繼續追捕黃道生,而是用招安的方式,給黃道生弄了個保安聯防隊副大隊長的頭銜,官雖然不大,可也意味著黃道生那些見不得人的生意都已經合法化了。
1949年5月鉛山解放後,黃道生與國民黨軍統上饒情報組組長雷乃公,國民黨永平縣鎮長姚琴等人沆瀣一氣,蒐羅地痞、流氓、慣匪、潰兵二三百人,編成“閩浙贛邊區遊擊團”。
黃道生名義上是特別行動隊隊長,實際上就是這群烏合之眾的總頭目。
“遊擊團”成立的第一天,黃道生就帶人回到他的老家,把村裡的鄉親召集到一起,當著大家的面,用他的銑山刀,把一個外鄉的小商販砍頭祭刀,並威脅說:哪個窮鬼敢分我家的房屋和田產,就和今天這人一樣,腦袋搬家,全家殺絕。
村裡人都知道黃道生心狠手辣,土改時無論工作隊怎樣做工作,就是沒人敢動黃家的東西。
黃道生對進步群眾和地方幹部恨之入骨,張嘴閉嘴稱他們窮鬼。閩贛邊區許多山區鄉鎮,都曾遭到過黃道生的襲擾,至少有20多名進步群眾,慘死在黃道生之手。
多行不義必自斃,1951年春天,在當地駐軍的打擊下,黃道生的“閩浙贛邊區遊擊團”被一網打盡,就連那個名義上的“”團長”,軍統特務雷乃公也做了俘虜。
美中不足的是,黃道生隻身逃脫了。
黃道生在武夷山中躲了幾個月,感覺風聲沒那麼緊了,又悄悄地潛回鉛山。在湖坊、橋北、陳坊、汪二以及弋陽一帶,與當地悍匪丁柏江,張克光勾結在一起,準備繼續為非作歹。
不料計劃敗露,5月的一個夜晚,鉛山公安機關發起突襲,把這夥圖謀不軌的匪徒一網打盡,張克光等40多名骨幹被生擒活捉。
只有匪首丁柏江,黃道生趁亂逃入鉛山、弋陽交界處的橫塘山區。
其後公安機關一直沒有放棄對黃道生的追剿,可是這廝太狡猾,被他屢屢逃脫,並數次作惡。
當地百姓對黃道生恨之入骨,又談之色變,私下裡稱他是“殺人魔王”。
轉眼一年多過去了,罪大惡極的黃道生,依舊逍遙法外,嚴重影響當地的治安和正常生產。
公安機關倍感壓力,江西公安廳於1953年春季,下達剿滅殘匪黃道生的命令,並提出“如難活捉,就地擊斃”。
鉛山縣公安局與當地駐軍聯合,組織一支剿匪小分隊,由縣公安局偵察組長王書賢帶領。在黃道生可能藏匿的地方,進行拉網式細密搜尋。
但這種搜尋無異於大海撈針,兩個多月過去了,剿匪小分隊還是沒有任何線索。
在鉛山、弋陽兩縣交界處的湖坊鎮,鎮上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古橋,在古橋兩側河畔上,商賈雲集,林立著無數的商家買賣。
6月中旬一個上午,剿匪小分隊化裝成外地客商,來到湖坊鎮,轉了整整一上午,也沒發現有什麼蛛絲馬跡。
中午時分,兩個偵察員到河西街的一家小飯館裡用餐。飯店的老闆很熱情,一直張羅著給兩位偵察員聯絡生意。
正在這個時候,從外面走進一個挑籮擔的男人,40來歲年紀,面板黝黑。這個人綽號叫烏皮,與飯店老闆是老相識。
烏皮籮擔裡裝的是牛肉,打算賣給飯店老闆。
飯店老闆打算壓一壓牛肉的價錢,便對烏皮說這是瘟牛肉。
烏皮一聽這話就急了,對天發誓說這就是上好的牛肉,家裡老婆生孩子,沒錢買油買鹽,只好把牛殺了。
飯店老闆還是有些不相信,說一條牛怎麼會就這麼少的牛肉。
烏皮說是條小牛犢子,殺牛的時候沒有綁結實,結果牛犢子跑了,追上去捅了幾刀,才把牛殺了。
飯店老闆又跟兩位偵察員打招呼道:“您們二位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看看這是不是瘟牛肉?”
年紀稍大的偵察員姓朱,戰友們都叫他百事通。老朱看了看籮擔裡的牛肉,很自信地笑著道:“是新鮮牛肉,只是殺牛時手法不對頭,所以顏色看上去有些發暗,但絕對不是瘟牛肉”。
飯店老闆一心想和兩位外地客商做大生意,為了顯示自己不是奸商,他很爽快地把牛肉全買下來。
烏皮對老朱感恩戴德,要了酒菜,和老朱對飲起來。
和老朱一起的偵察員姓張,就姑且稱他小張吧。
小張見烏皮喝酒不讓他,有些賭氣的買來兩瓶老酒,給烏皮倒滿一碗酒,然後他端起酒碗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這個人喜歡交朋友,我先乾為敬。
老朱知道小張酒量很大,便笑著在一旁看熱鬧。
烏皮幾碗水酒下肚,話就開始多起來:他說他家住在離湖坊十八里的土壕溪坑,是大山上的獨戶人家,家裡有老婆和一個在手上抱的兒子。他感覺種田太難太苦,想做生意養家,今天有幸結識了兩位外地客商,希望老朱和小張以後多幫襯一下。
烏皮彷彿有別的心事,不便明說,他沒敢喝得酩酊大醉,就起身告辭,並向飯店老闆買了菸酒火柴,順便把兩位偵察員的飯費也結了。
小張看著烏皮晃晃蕩蕩出了門,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沒想到他這麼爽快,倒顯得我小肚雞腸了”。
飯店老闆撇了撇嘴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二位老闆,你們是外鄉人,我才告訴你,我們這裡有個土匪頭子黃道生,這個烏皮就是他的狗腿子,黃道生被解放軍追的東躲西藏,不敢露面,烏皮就替他下山採買東西,你們二位看這牛肉,正經人家誰家捨得把小牛殺來賣肉,再說這殺牛的手法也不是用刀捅死的,這肯定是黃道生用他的銑山刀,在牛欄裡把老百姓的牛犢子給殺了”。
飯店老闆很健談,又絮絮叨叨和兩位偵察員說了許多關於黃道生的傳說,其中有真有假。
兩位偵察員明知飯店老闆話裡有水分,卻也不便當面揭穿他。
最後飯店老闆也感覺到今天自己說得太多了,有些緊張地提醒道:“我說的這些話,你們一聽就可以了,千萬不要對別人說起,免得招惹麻煩”。
老朱認真地道:“我們做生意的只談生意經,今天我酒喝多了,老闆剛才說了些什麼,我都沒有記住”。
在飯店老闆感激的目光中,老朱和小張也出門去了。
對兩位偵察員來說,這真是無巧不成書。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一直苦於沒有線索的剿匪小分隊,終於有撥雲見日的感覺,當天晚上他們聚在一起,商量怎樣透過烏皮這條線索,把黃道生揪出來。
要保證萬無一失,就不能操之過急,以免打草驚蛇。剿匪小分隊做了充足的準備,直到一個月後才開始行動。
7月中旬的一個下午的傍晚時分,烏皮正在山壟的田裡耘苗,突然看到三個農民打扮的人,從三個方向向他包抄過來。
烏皮感到情況不妙,丟下手中的農具,轉身就跑,可是他剛跑上田坎,又有兩個農民打扮的人閃身而出,擋住他的去路。
烏皮強做鎮靜,陪著笑臉道:“各位朋友不要誤會,我烏皮也是江湖上的人,在家姓潘,出外姓……”
烏皮的話還沒講完,就看到五六支黑洞洞的槍口,一起對準了他。一個人走上前來,給烏皮帶上手銬。
在附近山上的一片密林中,烏皮見到了剿匪小分隊隊長王書賢。
據烏皮交待,他和黃道生是老相識,曾經在黃道生的賭場裡看過場子,後來黃道生做了土匪頭子,烏皮不想幹這掉腦袋的營生,開小差溜了。
去年5月的一天晚上,黃道生隻身一人來到烏皮家,狼吞虎嚥地吃了頓飽飯,然後拿走了一領草蓆,一捆稻草和一床棉被,臨走留下5塊大洋。
幾天後黃道生去而復返,要一些鍋、碗、米、油、鹽等生活用品。
烏皮說家裡缺糧,黃道生有時給錢,有時弄些小牛、小豬,甚至是一串石雞,叫烏皮拿到附近集鎮上賣掉,換所需的東西。
而且黃道生還刻意囑咐烏皮,一個市鎮一個月最多允許去一次。
烏皮想直接要錢,黃道生說烏皮平時日子一直很拮据,突然大手大腳的花錢,會引起別人的懷疑。
另外黃道生還警告烏皮,膽敢出賣黃道生,就小心他一家滿門老少的性命。
剿匪小分隊又問烏皮,知不知道黃道生住在哪裡?
烏皮搖頭說不知道,每次黃道生來都神神秘秘的,走的時候還不允許烏皮去送行。
根據烏皮的交待,剿匪小分隊制定了捉拿黃道生的計劃。
7月19日下午,老朱等三名公安人員化裝成裁縫,埋伏在烏皮家中。為了防止意外,老豬讓烏皮的老婆抱著孩子躲了起來,只留烏皮一人在家應承。
晚上9點多,偵察員小張感到有些口渴,他穿著背心短褲,他拉著鞋,來到廳堂喝茶。剛斟滿茶水,猛然間發現,廳堂上首靠牆的凳子上,坐著個身高體壯,滿臉橫肉,手持銑山刀的人。
小張心裡說,看來這個凶神惡煞般的傢伙,就是黃道生了。
此時黃道生也看見了小張,厲聲問烏皮道:“你家裡來了什麼人?”
烏皮道:“是我家請的裁縫,頭幾天你不是說要添幾身衣服嗎?”
黃道生冷哼了一聲,沒再說話。
烏皮接著問:“你吃飯了嗎?我給你準備酒菜去”。
黃道生道:“我吃飽了,不吃了”。
小張心裡緊張,但他故意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將空茶碗放在桌上,腳步從容地回到堂屋後面的小屋裡,輕輕地提醒另外兩名偵察員老朱和小候道:“那個人來了”。
按照事先制定的緝捕方案,老朱和小候從廳堂正面只取黃道生,小張從後門繞出去,在前門堵截。
結果忙中出錯,老朱和小候每人一支衝鋒槍,壓子彈上膛時,出現的輕微噪音驚動了黃道生。他沒等見到人,就跳起身往大門外面跑。
老朱和小侯隨即從背後開槍,此刻小張已經出現在大門外。
黃道生一愣,就在這個時候,老朱已經衝了上來,但他沒有注意腳下的門檻兒,被絆倒在地,離黃道生不足三米遠。
此時黃道生也蒙了,無論是撿丟在腳下的衝鋒槍,還是回手給老朱一刀,都會讓整個抓捕行動出現變數。
可黃道生已經慌了,他縱身一躍,翻過一米多高的菜園竹籬,又長了翅膀般,很輕易地跳過兩米多高的圍牆,逃出院外。
老朱和兩名戰友追到門外,看到烏皮的老婆抱著孩子躲在一棵大樹後,慌亂中也沒想到她怎麼偷偷地溜回來了?
老朱問烏皮的老婆:“黃道生逃到哪裡去了?”
烏皮的老婆指了指十幾米開外的一棵大樹,嚇得渾身哆嗦的說不出話來。
月光下,黃道生雙手摁著銑山刀,背靠一棵大樹,面目猙獰地站在那裡。
黃道生背後就是一片密林,為了防止他逃到林中去,老朱用衝鋒槍對著黃道生的兩條腿打了兩個點射,黃道生這才直挺挺地摔在地上。
老朱和戰友們圍上去,只見黃道生左胸和腿部共中了六槍,已然斃命了。
黃道生雖然死了,但他這兩年中躲在哪裡,還有他多年搜刮來的鉅額財產藏匿在什麼地方,都成為未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