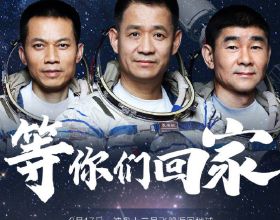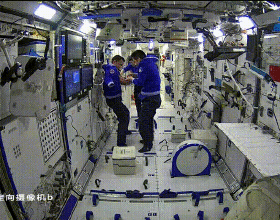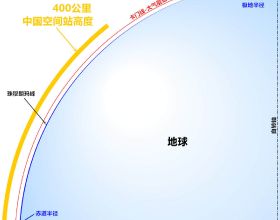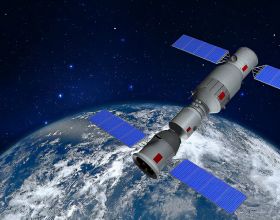物道君語:
在你心裡,壎長什麼樣?雞蛋的橢圓形,還是普通的梨形。
在古代,壎不止吹,還有藝術壎,如人面壎,作為一種壎藝留存至今。幾千年後,也有一個人把壎做成各種形狀,像流水,像高山,像竹林,還像貝殼,像魚......更改變了壎的音腔結構,使之不僅可以吹古曲,也可以吹流行曲。
他是當代壎藝家,張駟。
賈平凹的《廢都》裡,夜晚城牆頭上會傳來一段沉緩悠長的音樂,嗚嗚如夜風臨窗。一個叫莊之蝶的人說:“你閉上眼慢慢體會這意境,就會覺得猶如置身於洪荒之中......聽見了一顆露珠沿著枝條慢慢滑動。”
這便是壎聲。
壎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距今7000年前的半坡遺址上,就發現了它。壎還曾經進入了宮廷,作為敬天祭拜的禮器,不過時間走著走著,在明代失傳於民間。
所以距今二十多年前,相當多人對壎是陌生的。於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幾個人學壎、吹壎、推廣壎,乃至改變壎。
因為他們發現,世上樂器大多唱娛樂,演奏華麗的東西,壎不張揚,也不華麗,發的是土聲,地氣。如同在一個紛繁複雜的社會里,有人鋒芒畢露,有人獨處靜思。
這其中的一個制壎人,便是來自大連的張駟。
他來自一個“陶藝世家”,如今他在大連的山裡,已制壎四十年,從找礦石巖彩,到突破造型,校準音節,使音域寬泛,把壎做成了一種藝術品,部分收入博物館館藏。
張駟1955年出生,父母和哥哥都做陶,作為家裡最小的孩子,受父母寵愛,他們不想張駟也走這條辛苦路。
不過採訪裡,張駟說到,小時候經常鑽進家裡的饅頭窯,給大人們遞出做好的陶器,那時就覺得神奇,“同樣是一灘泥,玩的泥巴會裂開,但這些燒一燒就結實,還有模有樣,有聲有響。”
當然其中受過父母反對,他下過鄉,考上大學,學的卻是自動化,後來進入企業工作。中途好像幡然醒悟一樣,回過頭來,重新開始,做壎。
但沒有基礎,只能悶頭幹,從一把土開始。採訪後的一天,正值初冬,66歲的張駟在大連的山谷裡找礦石和巖彩。
相傳古代制壎人也在秋天取土,調合成泥,但根據現在的氣候,這個時間要再冷一點。一場雪落,張駟這才進行野外採集。
“這個時候的土地沒有生靈了,是淨土。”一掊土也有生命,春夏兩季忙著給植物輸送養分,只有等到秋才能休息。這時的土質乾淨了,做出來的壎,聲音才比較通透,甚至像水一樣清。
不過除了泥土,張駟還要找古人用來畫畫的巖彩,給自己的壎上色。
那一次採集,半山腰上他找到了兩塊半透明的石英,上面粘連著薔薇色的泥土;找到了肌理如絲緞的綠泥石,燒製時會形成晶體;還有最常見礦石是赭石色、木灰色、咖色、褐色......
古人在《考工記》裡說:“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與人工釉色不同,自然的泥土,在窯變中的幻化,可能性很大。
有驚喜,如天空落幕後放鬆的藍,如深山清泉的灰白,水月白;也有笨拙,像沉穩的松綠、草綠、灰綠.....張駟坦言,這些色彩在陶壎上燒製出來,很難被人喜歡。
就像石頭灰濛濛的色彩,像冬天的不驚豔,不同華麗的東西總是容易抓人眼球,沉靜的色彩總要經過歲月才能欣賞。
不過說來也奇,那些我們熟悉的半坡彩陶,馬王堆賦彩濃郁的帛畫、漆畫,敦煌的壁畫,是古代人用巖彩做的畫的。而在幾百或上千年後的今天,我們看著它們,既熟悉,又新鮮。
張駟的壎,好像也是這樣,放在桌上你看它不驚豔,可是就放著,時間過著,沉默中折射出了不同的光。
張駟提到:“壎是人類第一件從無到有創造的樂器而不是製造。比如竹笛在竹子上做出來,而壎是一把土創造。”其實,壎音也是土造。
野外採集回來,張駟就把礦石砸得大小差不多的一塊塊,煅燒到800度,使礦石變酥,最後就像照顧小朋友一樣碾成粉末,為壎做泥。
之後需要在自然中陳腐發酵差不多一年時間,才可以用來捏壎。壎上頭有孔,是吹奏的口。壎身還有7到10個孔,用來按指法。
不過素胎壎做好後,張駟不著急鑽孔調音。而是先拿來塑膠袋,把素壎套上半封著,因為土有收縮力,如果幹得太快,就會龜裂,只能等它慢慢來。
一般三天時間,素壎半乾就可以鑽孔。但不能一次鑽完,畢竟這時的土只是半乾,後續還能收縮,如果鑽大了,土再收縮,孔更就大,聲音就上不去,吹出來可能像鴨叫。
只能時刻觀察,幹到一定程度,就去吹,試音對不對,不行繼續調音。一次又一次,直到自然條件下,孔洞大小穩定後,那麼就可以入窯了。
這個鑽空調音的過程,張駟算過日子,大概12天。記得《三字經》裡說:“匏 [páo] 土革、木石金,絲與竹,乃八音。”其中“土”,便是壎。壎既成於土,便土聲,有地氣。
燒窯之餘,張駟歇息下來,拿起壎,在曠野邊上吹,嗚嗚咽咽,還挺像賈平凹在《廢都》說的,如泣如訴,聽著傷心,聞著落淚。
這似乎不大像土的厚重。可什麼是土聲,張駟也說不出來,只覺得一切準備妥當,心情放鬆,只需等著窯燒三天三夜。
就像這個季節,繁華落盡,土地也在休養生息,又如人的慾望蕪雜也隨之褪去,生活是喧囂浮華也落去,心沉靜下來,安享當下。
不得不疑問的是,張駟是怎麼知道土的收縮力有多大,又該調多大的孔,得乾燥多少天?
沒有別的方法,就是一把一把土捏,一爐一爐燒,一件事情做多了,留心了,自然就會知道。
就這樣,張駟做了近40年,獲得過陶瓷藝術家獎,金獎、銀獎,到現在擔任中國陶瓷協會常務理事,或到大連的一些大學上陶藝課,或帶徒學陶。
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你這樣作壎有必要嗎?”是他做異形壎。常見是壎,是雞蛋的橢圓形。張駟還喜歡做牛圖騰壎,鳥圖騰壎;也做表意壎,高山流水壎,如歌如意壎,待時壎......
這些異形壎,用途不在演奏。因為形狀、開孔的位置發生改變,指法也會有相應的變化,作為制壎人,張駟會吹會指法,對於其他學壎的人,這是不利的。
而在古代也有異形壎,唐三彩陶壎,紅陶刻花壎,人面壎……這些都是裝飾多於吹奏。所以張駟意不在此,在於探索壎的藝術性、現代性。
他改變壎的音腔結構,使得它既能吹古曲,也能吹現代的流行曲,能吹高音。
這讓我想起了二胡,曾經當它是捱呀捱呀的要淘汰的樂器,可一路過來,聽它拉起了《起風了》,拉起了《化身孤島的鯨》,它走進了我們,走進了現代,再想起已然不覺它很老。
很多古老樂器的命運,似乎都是如此,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只能淘汰,消失。這有時不能埋怨時代,因為每一個當下都是要進步,自然就產生了新的樂器,新的審美。
更為要緊的,有沒有一些人,因為熱愛壎,而想要改進壎,讓它走進現代,走進我們。而這些需要代價,就有所必要。
只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好在時光的腳步每一寸都有價值。春夏秋冬,一個接著一個季節過去,不怕緩慢,只要堅定,孜孜不倦地,自然會有結果。
就像這土做的壎,它吹著大地的飄零與茫茫,也吹去等待的來年與春天。
文字為物道原創,轉載請聯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