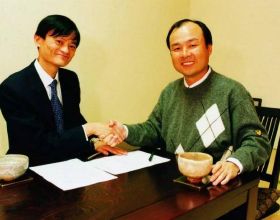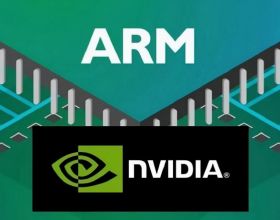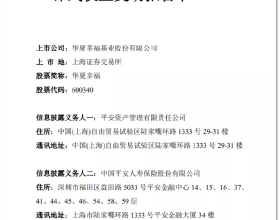大荒舊聞錄 · 告狀記
作者:關文傑
我去佳木斯了,那可真是這一帶的大城市呀,繁花似錦的,在我眼裡。離開北京太久了,看到高樓大廈都不適應了。
雖然這是一趟負重之旅——我買了四個大號鐵皮水桶、一大包各種調料、幾把勺子鏟子笊籬什麼的炊具。看著不多,要說也沒多沉,可那都要我自己扛回連隊呀。
不管怎麼說,好久沒聞到城市的味道了,看著滾滾的松花江,江面上不時駛過的汽艇帆船,江橋上隆隆駛過的火車,都讓我激動萬分。這是現代文明的標誌呀,我在連裡感受的都是村裡的氣息,與幾十年前並無太大的差別。
這是我當上士以來,也是我下鄉以來第一次進城。
到了佳木斯,我先到劉英俊墓前照了相,橫的一張,豎的一張,一是對英雄的敬仰。二是好久沒照相了,逮著機會趕緊多拍幾張。
然後就是大吃一頓,今天還能能記得的就是點了個“攤黃菜”,也就是攤雞蛋,酥白肉,就是炸肥肉。別看沒啥新鮮的,當時吃起來那就是御膳啊。
吃飽了喝足了,我又去洗了個澡。到兵團快兩年了,基本上保持了兵團戰士的傳統,“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幹搓,星期日休息”的習慣,還沒洗過真正意義上的澡呢。
昏暗的浴池裡,瀰漫著水蒸汽和人體搓洗下來的汙物混合的特有的味道。這可不像北京和平里浴池,還有張床,有個茶几,衣服可以放到自己專屬的櫥櫃裡鎖上。你要是手頭寬裕,還可以要壺茶。雪白的細瓷茶壺茶杯,看上去就那麼幹淨,不由得你不來一壺,續水還不要錢。只要你招呼一聲,那個有著嚴重疝氣的老頭就會把茶送到你的床前。
當然,你要是來的不是時候,沒有床了,要麼你多花兩毛多錢要個單間,要麼你就“脫筐”,就是把衣服放在大筐裡,沒有床,洗完了走人。
佳木斯澡堂的規矩是,你脫下衣服後捲成卷,用自己的腰帶捆上。交給服務員後。服務員會用一個頭上邊帶鐵鉤的長杆,把你的衣服卷掛在天花板上。一進浴池,你就會看到高高的天花板上,滿屋頂琳琅滿目的衣服卷,有的圍脖褲腿沒卷好的,還會長長地垂下來,像掛在樹上的幡兒,很是不雅。
這是我今生僅見的情景,至今難忘。
洗得乾乾淨淨的,我得去採購了。記得一小插曲,我在買水桶的時候一下拿不準買多大的了。誰知道平時看上去差不多的水桶,原來還分各種尺寸,雖說每天都用水桶,可是一到商店,大大小小的水桶還真是一下分不出個所以然了。
於是,就想打電話回連問問。找到商店的辦公室借電話,人家還真不錯,把電話給我了,三老大姐或者大媽盯著我打電話。
也是該著露怯,兵團的電話都是手搖電話,按著插簧搖搖柄,用了很久就習慣了。我拿起電話,習慣性地按著撥簧就開始撥號。
大姐看到了就笑話我,說“你那能打出去嗎?手得鬆開呀!”
旁邊另一位大媽說了“鄉下人都這樣,屯迷糊打電話就得按著。”
你看,一不留神,我成屯迷糊了。
澡也洗了,屯迷糊也當了,事情到此本來就完了,剩下的就是我扛著那些採購的東西,長途跋涉,累個半死,好歹把炊具扛回了連隊,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問題就出在我在錯誤的日子、買了張錯誤的車次、上了錯誤的車廂、趕上了錯誤的座號上了。
我上車的時候天還下著小雨,車上人不多,車廂挺空的。叮裡咣噹,我扛著水桶、拎著炊具、掛著調料的總算上車安頓下來了,看著整齊的站臺,就要離開美麗的佳木斯了,竟然還有幾分依依不捨。
就要開車的時候,我這個車廂上來一群軍人,都是現役軍人,這些軍人各個軍裝帽徽鮮亮。十幾個人魚貫進入車廂,一位老者在先,但其他人都會不時地過來,圍著這年長者轉。
沒走幾步,那年長者走到我這排站下了,就坐在了我的對面。還沒坐穩,就不時地有人在低聲地與他耳語,看上去是向他請示彙報啥的。
這些人腰裡鼓鼓的,槍繩不時被甩出衣襟。我也是小江湖了,一看這老者就是個當官的,估計還不會很小,要不不會有這麼多隨從。
咱可不敢、也不願巴結當官的,裝作沒看見,我扭頭看著窗外的秋景,任那些當兵的彙報吧。
“小同志,你這是上哪呀?”稍傾,可能是屬下彙報完了,那老軍人開始和我說話了。
“到佳木斯出差去了。您呢?”我反問。特意說到是“出差”我的意思是我也不是盲流。
“我們也是出差,到新華。”老頭看上去挺隨和“聽口音你是北京人?是知青嗎?”老軍人問。
“是呀,您眼力不錯。”老頭眼神不錯,一下就看出我是北京知青了。
這之後我們就開聊了,老頭挺健談的,從我是北京哪個學校的、多大了、家長是幹啥的、哪個團的、哪個連隊的、幹活累不、生活能否適應……問了一大堆,話裡話外對兵團很是熟悉。
此刻,我已經大概知道這位該是兵團的領導,起碼是師以上軍官,肯定不是二師的,因為他說從新華還要去寶泉嶺,那是我們二師師部。
這人肯定還是個老革命,估計還打過仗。因為我說我們經常緊急集合,每人拿個棍子上山,假模假式的搜山抓特務。這樣不但影響休息,忙乎半夜,天亮了還要下地幹活,累得半死的事後,他說:我剛當兵時也拿個大棒子。說完自己還笑了半天。
這人一沒了距離,說話就容易走板。
說實在的,我多少也有點成心告狀:那毫無意義的半夜裡的緊急集合、不讓睡覺去聽指導員講空洞的政治報告、放著機械不用,讓我們高喊“小鐮刀戰勝機械化”在大田裡拼命、為了省糧食我們吃捂了的棒子麵、瞎指揮修建的水利工程變成了一條條幹溝子……我是想到哪說到哪。
也是我這人肚裡憋不住話,也是那個時代真是缺少這樣的下情上達的渠道,趁這機會還不趕緊給那些瞎指揮的人上上眼藥?反正老頭也不認識我。
我說得很投入,那都是咱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啊,不編不造,實事求是。那時候哪裡知道江湖險惡呢,想到哪裡說到哪裡,老頭聽得挺認真,表情也嚴肅起來,還不時問這問那的。
留了個心眼,車快到新華時,我不想在團部和老頭一同下車。我估計團裡一定會有人來接車的,那樣會被來迎接的團首長看見,那豈不暴露了我和首長同車的行蹤了——新華車站很小,最多算五等站,誰下車那可是一覽無餘的。
我決定提前一站在鶴立下車。從鶴立回連隊,雖說比新華要多走幾公里,但鶴立是林業局的地盤,進山拉木頭的車多,進山的路正好經過八連附近,也許能搭上順風車。
“你們連離團部有多遠呀?”老軍人問。
“40裡地吧。”我說。
“那你這東西怎麼辦,有車嗎,要不要送你一下?”他挺真誠地問。
“不用了,我能行。”剛才那一通發洩痛快是痛快了,那不就是告狀嗎?我可不傻,還不趕快走,哪敢讓他送呀,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啊。
出了鶴立鎮,路上都是泥,一步一滑。我索性脫了鞋,光著腳,扛著桶,拎著包,擦著汗。下雨路不好走,泥濘的路上連個車影也看不見,搭便車的可能完全沒有了。
一路艱辛,我回到連隊。
後來覺得,人在沒指望的時候,忍耐力倒是可以發揮到極致,幾十裡地,負重前行,我也回來了。
到了宿舍,剛把溼透了的衣服換上,還沒來得及躺下歇會,老薑進屋了。還是慣有的一臉神秘,依然是那麼未卜先知的感覺“回來啦,路上碰上什麼人啦?”
簡直奇怪了,我剛進屋呀,他怎麼……
還沒來得及問老薑咋回事,“上士,指導員叫你,馬上去”門外有人喊。
一頓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威脅利誘的談話後,看著指導員氣急敗壞的樣子,我才知道,就在我篳路藍縷走在泥路上的時候,團部的電話就打過來了。團首長指示,按兵團首長要求,八連領導班子黨支部一般人,要馬上改進工作作風,求真務實,不搞花架子,愛護士兵(也就是知青),改善伙食,調整勞動與軍訓的關係,合理安排作訓……
捱了頓狗屁呲,我才知道,火車上遇到的那個老頭,是兵團首長段政委(也許是政治部主任,叫什麼我記不清了)。
事後我也沒感到什麼壓力,據說是段政委專門指示過,要正確對待群眾意見,不許打擊報復,不許穿小鞋。
很久後才知道,小鞋還有“玻璃”的,哈哈。
不久我也不幹上士了,再不久我又調到東大甸子住帳篷,修水利去了。無邊無際的沼澤地裡,那裡蚊蟲鋪天蓋地,那裡鋪下就是水,那裡的水是鐵鏽色的,那裡的大土筐有二三百斤重……
如今段政委不知還健在否,如果還在,也不知道他還能記得不,1971年在列車上和一個小上士的偶遇。
老知青家園 今天
作者:關文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