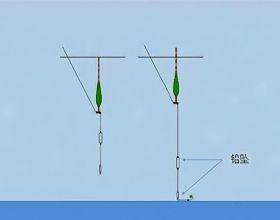2019年夏天,我獨自登上了一艘遊輪,開始了時長一個多月的湄公河遊輪之旅,途經六個國家。在這段旅程中,我認識了一些同行的旅人,日本人,越南人,中國人,歐洲客,各色面板,各種語言。
夕陽像是揉碎了灑在河面上,暈黃的河面泛著孔雀藍的色澤,船漸漸行駛向河的深處。
我是中國的少女,跑到這條越南的河上。白棉布的裙子,一條馬尾辮子。因為乾燥,我臉上的面板泛出細小的皮屑。
我還年輕,也很美麗,愛情對我是理所應當。
我回過頭看到一個金髮的英倫男人舉著紅酒的杯子對我微笑。他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你真美麗。”
“你也很帥啊。”我抬起頭盯著他的眼睛,那是種寶石藍的顏色。
他是我的男朋友,我們在這條船上認識。一個女人對男人的色慾就像喝水一樣自然,若是擁有他,挎住他的肩,慢慢走在街邊,會引得多少女子側目而視。我偷偷地笑起來。
這年,我20歲。
我想起了我的母親。除夕的街頭風大寒冷,我牽著母親的手,走在下過雪的街邊。
我抬頭看到大片大片的雪花旋轉飄落。街邊有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揮舞手中的彩色熒光棒,小臉凍得通紅,咯咯地笑出聲來。我拉著母親的衣服,問她:“我為什麼沒有爸爸?”
母親抱我起來。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缺陷的,你不要在意啊。你是我的,和任何人沒有關係。”她親吻我,混著香水的迷亂氣味。我們相依為命,在飄雪的街頭。
那年,我7歲。
我喜歡坐在船艙食堂一個靠窗子的位子上,在吃飯或者喝咖啡的時候可以抬起頭看到河邊的景色。
一個東方男人在我對面大口大口地吃麵包,盯著我看,沒有邪意。他的眼睛告訴我,他是個純潔且與世無爭的男子。
他叫片桐秀介,來自東京,是一名運動員,近期休假,到越南旅遊。
秀介的船艙就在我的隔壁,每晚會傳出聽不懂的英文CD的聲音,緩緩地像一匹緞子在黑暗中撕裂。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daring,kiss me!
我敲他的門,問他這是誰的歌。
“宇多田光。”他說。他是漂亮的東方男人,有精練的平頭,穿寬大的白棉布襯衫,和藍色印著英文布貼的廉價牛仔褲,微笑迷人。
我和他一起進屋,一起聽歌,一起在黑暗中對視,感覺綺麗美好。
母親沒有愛情,沒有男人的親吻,沒有安慰,沒有擁抱。她只有我而已。
但她不會擁抱我,不會親吻我。
我渴望任何一種形式的愛,因為那會有親吻,擁抱。
我20歲。
英國男人的面板散發出一種蒼老陳舊的氣息,像是黴變的味道。但他的眼睛嘴唇還有金色的頭髮是漂亮的,我喜歡他的嘴唇,像是在用牙齒咬一隻熟透的奼紫蘋果。我盯著他寶石藍的眼睛,伸出手撫摸他的短髮。
他是我的男朋友,但我很清楚我們之間沒有愛。相處在一起,僅僅是需要對方。
我羨慕秀介,因為他是靠體力工作。雖然勞累但情感純真。
晚上,秀介請我吃飯,點在這裡算是奢侈的西餐。我很開心,激動了一整個下午。秀介是費了心思的,覺得這算是一場正式的約會。我換上從集市買的繡花蕾絲裙子,吊帶可以露出細嫩的肩膀,裙襬像是魚的尾巴,會隨著腳下的步子掠過赤裸的小腿。
我準備好一切,對著鏡子微笑。我還年輕並且美麗,愛情於我理所應當。
秀介坐在餐桌旁,他點了兩份牛排,若干甜點,魚,小盤香菇,一瓶紅酒,還有一些類似牡蠣的海鮮。
“你今天換了衣服,”他說,“給人不一樣的感覺啊。”
“那你覺得哪種樣子好看呢?”
“你人美麗,不會因為衣服而變化。”
我搖晃手裡的高腳杯,仰起頭喝一口,然後大聲笑了出來。
秀介有一臺舊的CD機,他喜歡宇多田光的歌,《fly me to the moon》。 這首歌的名字很美,是在月球上播放的第一首人類的歌曲。我喜歡宇多田光的嗓音,磁性,渾厚,帶有天性的落拓不羈,給人以遐想激越的空間。
秀介微微咬著嘴唇,臉色緋紅。我喜歡這樣一個青春明亮的男孩。
“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嗎?”他問。
我很想笑,我伸出手撫摸他的臉頰,像絲緞一樣的光滑。其實在很早我就應該猜到他請我出來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他所認知的愛情。我覺得他是個傻子,為我準備食物,然後表白,渴望我的愛。真是浪費。
“我考慮一下。”我說。
“我會等你。”他說。
七歲的時候,家在江南,住木製的老式閣樓房子。我喜歡穿白棉布的裙子,繡著金線團的紅色繡花鞋,小小的腳不穿襪子,塗上粉色的指甲油。在爬樓梯的時候,故意弄出很大的響聲,“吱呀”——“吱呀”。我童年時候的那段歲月像一部昏黃的膠片老電影,緩慢轉動,沒有波瀾。
母親獨自開一家旅店,精明能幹,為人耿直善良,喜歡幫助窮人與流落到這裡舉目無親的人。我喜歡她的打扮,自己做的旗袍,微燙著捲髮,鑲著兩顆小小珍珠的耳釘,用的香氣味獨特清醇。她是個難以言喻的女子,不需要依靠男人生活,亦不會為男人改變,不會因為家庭而面目全非,營營役役。她是她自己的,不屬於任何人。因此,我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都不會見到我的父親。他給了我生命,但我們的人生都與彼此沒有關係。
我會像每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睜大眼睛問母親,“父親在哪裡?”
母親會微笑,手搭在我的額頭上,對我說:“你是我的,和任何男人沒有關係。”
我的母親是我的一切,她的人生是我的宗教,我是她生命的延續,我們是彼此血脈相造最親的人。
直到她患乳腺癌去世。在醫院走廊,在她進手術室之前,我握住她的手不說話。她的手心寒冷乾燥。然後看著她被推進手術室,她再也沒有下手術檯。
母親死後,旅店被親戚們賣錢捲走,我被送進孤兒院。我對於孤兒院的記憶,是脾氣暴躁的老師不喜歡我,給很少的食物。上她的課時,我會偷偷跑出來,在操場上獨自行走,臉上掛著髒的淚痕。還有一棵種在孤兒院鐵門旁的大榕樹,枝葉繁茂,碩大翠綠的葉子在陽光下翻飛舒展。我會在中午和夜晚甩掉鞋子,三兩下便可以攀到樹頂。兩條小腿赤裸地垂下來,露水微涼,夜空的星辰明亮。我的裙子洗得發黃,馬尾辮蓬鬆凌亂。我有幾本海明威的書,我滿腦子都是奇怪的幻想。
我在樹上睡著,夢到母親就坐在我旁邊的樹枝上,她還是幾年前的美麗樣子,有熟悉的香水味道,只是有了黑的長髮,像黑色的瀑布在她的肩頭垂下。她把手搭在我的額頭。她的手,柔軟而寒冷。
“你要找個好男人好好地愛一場。”她對我說。
其實,我瞭解她的寂寞,她在想念父親。男人也許是不喜歡女人只是需要女人,但一個女人喜歡一個男人,愛得豐盛濃烈,那麼她一輩子將只有一個男人在心底。
“你要找個好男人好好地愛一場。”她對我說。
這是她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這年我10歲。
“你母親很愛你。”英國男人的手搭在我的額頭,他用手背掠過我的面板。
“是。”我回答他,又問,“我想擁有豐盛而濃烈的愛情,你會不會成為一個這樣對我的男人?”
“你缺少父愛,想要一個大你很多的男人來愛你,而我只是貪戀你的年輕與美麗。我們的愛,只是一場交易。”他說。
這不是愛,我深刻了解,愛是一件奢侈的事,不是每個人都承擔得起。但沒有愛情有激情也是好的。
我伸出雙手抱住英國男人,開始親吻他的金髮、眉心、眼睛,像是在吮吸他面板上所微發的陳舊氣息。他也抱住我,一雙手臂強大有力,像我童年時看到別的夥伴被他們的父親擁抱的時候他們體會到的感覺。
秀介給了我一張照片。一個美麗的女子,穿粉色的蕾絲裙子,裙襬有細碎的櫻花圖案。她站在一座新橋上,面對著波濤洶湧的大海,海風迅疾盛大,繚亂她的長髮。她回過頭,對看鏡頭微笑,臉色蒼白,微笑迷人。
“這是我的女朋友。”秀介說。
“她很美。”我笑。
“可是她已經死了。”秀介頭垂下去,帶著哭腔。
“為什麼?”
“她和我躺在天台上,她問我是不是真的愛她。她不信我說的,要和我猜拳,說輸的人要先從這裡跳下去,然後另一個也要緊接著跳下去。她輸了,頭也不回跑到天台柵欄那裡,衝著我微笑,然後跳了下去。我親眼看到她落到樓底的大理石上。我本以為這是一個玩笑的。我知道,我對不起她……”
說到這裡,秀介再也忍不住,跪倒在甲板上,把頭埋在手心裡,哭了。
我低著頭看他,沒有想過給他任何安慰,我討厭赤裸暴露在別人面前的眼淚,那是恥辱。
“秀介,”我說,“我們不適合。”
他抬起頭,滿臉都是淚水。我沒有跪下來遞給他紙巾,因為我覺得讓他一個人哭下去,對他是好事。
我到船頭抽一種越南產的煙,廉價。味道乾澀,苦辣,讓人頭昏眼花,有嘔吐的感覺。
河兩岸的村莊,有簡陋漂亮的木屋在燈光中閃現,居民結伴在河邊散步。長有碩大翠綠的葉子的熱帶樹木,綺麗詭異的花,黃色的大眼睛的不知名的動物,貓頭鷹的叫聲,以及溫柔的風。
英國男人在背後抱住我,熟悉的唇掠過我的脖子。我回過頭,用手指抵住他的唇,對他說:“我如果跳下去死掉,你會不會陪著我一起跳下去?”
“這根本不可能,我們不要考慮這樣的問題好嗎,darling?”他又開始親吻我,我沒有拒絕。
我想秀介一定會說,他會陪著我。我相信那是真話,即使那是假話,我也願意那樣被欺騙。
“我們去玩吧。”英國男人抱住我,把我帶到船上的一個小酒吧。酒吧裡,我坐在角落的一個位置,喝冷的扎啤,抽乾辣味道的煙。英國男人坐在對面,他的面容因為過於白暫,在酒吧變幻的彩色燈光中變得猙獰扭曲,像是一種野獸。
我笑笑,端起酒杯扭過身不再看他。
不遠處的吧檯,秀介在喝酒,加冰的威士忌,臉頰緋紅。看到我,他的表情在急劇變化,我確定他是看見了我。他搖晃著身子,擠過人群,走到我面前,我可以感覺到他在疑惑亦或是憤怒。
“他是誰呢?”秀介指著英國男人。
“這不關你的事。”我回答他。
英國男人對一些人情世故很瞭解,他很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並沒有打算引起衝突。所以他只是坐著,埋頭喝酒,裝成一個外國人聽不懂漢語。
“他是誰?你拒絕我是因為他嗎?”秀介質問我。
這該是一場被電視劇演爛的劇集,暗戀一個女人的男人,遭到女人拒絕後,在另一個地方撞到女人和她的情人在一起,男人會來質問,然後有一場衝突。
但實際上,最後沒有任何衝突。秀介平靜下來,我們各自回了房間。
這條船在湄公河上的路程已經接近半個月,我認識了秀介與英國男人,以及一些同行的旅人,我喜歡同簡單淳樸的人交談。
一個面板黝黑的越南年輕男人在船上做清潔,他會給我講他的工資,低得驚人,但我沒有吃驚。他說他的故鄉在鄉下,他愛他的故鄉,但在這裡更容易找到工作,可以賺更多的錢,貼補家用。他說他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他說這些時,會微微笑起來,露出亮得逼人的牙齒與瞳孔。
一個披著碎花蕾絲紗巾的越南婦女,體態豐腴,黑,扎雜亂的越南髻。她經常帶著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在甲板上曬太陽,那個孩子很喜歡我,因為我會送他好吃甜膩的糖果與巧克力。孩子只要有糖就會快樂,他們不會對人生索取過多。
我似乎已經習慣了孤獨與漂泊。獨自在夜行的船上泡一杯咖啡,倚在窗邊,單手抽菸,看到外面月光下,就這樣醒著看窗外,獨自過一夜。
秀介的房間在播放宇多田光的Passion,宇多田光的磁性嗓音,令人溫暖。
我已經三天沒去看他,覺得再見到他是對他的一種傷害。每晚可以聽到他房間裡傳出斷斷續續的哭聲,他是個懦弱的人,可以哭泣便是幸福。
我小時候一度希望有人可以注意我,可以呵護與保護我,於是我故意傷害自己,在身上留下細小或粗大的傷痕,因為破傷風的感染甚至差一些死掉。母親守在醫院的床邊,徹夜不眠,拿著溫度計不斷地給我量體溫。那次住院持續半個月左右,我病好後,問母親為什麼會對我這麼關心,她的手打在我的額頭上,說:“你是我的,我不會讓你死的。”
那一年我7歲。
秀介蜷縮在牆角,手搭在一盆熱水裡,手腕上有粗大血紅的傷口,血液不斷地汩汩湧出。他因為瞬間失血,臉頰嘴唇變得蒼白,額頭上滲出汗珠。
“你來了。”他在昏迷中抓住我的手。他手心裡的冰冷令我心疼,我害怕任何一條生命在我手裡流失,那是不可饒恕的原罪。我抓住他的手腕,用牙齒撕下白棉布裙子的一角,系在他傷口上。我找到船長。船被迫臨時靠岸。我翻出秀介的護照,以及一些美金。我一直陪著他。他問我,如果他活下來,我可不可以嫁他。我強忍住淚水,對他說:“可以。”
小時候我讓別人看到我的血液在傷口中滲出來,但我現在才明白,傷口展現在別人面前,是恥辱。
我回到船上,午夜的風使我感到寒冷。我緊緊抱住自己,破碎的棉布裙子在風中綻開。我抬起頭,看到船上被驚醒的乘客。英國男人看著我,穿一件卡其色的格子睡衣。
一連幾天我沉浸在那個血腥的夜中,睡眠是種煎熬。我一閉上眼就會看到秀介在牆角呻吟,手腕不斷有血滲出來。英國男人陪在我的身邊,牽住我的手一直到我睡著,給我特別可靠的感覺。
我想我會逐漸愛上他的,一個女人只要牽住一個男人的手,如果可以在那個男人手心裡得到愛與溫暖,不管這個男人是誰,都會愛上他。
清晨的時候,英國男人微笑著開門,端著一個棕色的木托盤,有一杯加方糖的咖啡,兩片芝士,煎單面的荷包蛋,一小片香腸。
大束的馬蹄蓮,雪白的花瓣上面有散落的水滴。他找了一個大玻璃杯子裝了一些水,把花擺在我的床頭櫃上。
我好幾天沒有好好吃東西,吃飽後臉上又漸漸有了血色。我立刻跑到鏡子前,塗了口紅,用了一點香水。我對著鏡子看自己,我明白我還年輕並且美麗,愛情於我理所應當。我回過頭摟住英國男人的脖子,問他,我可不可以嫁給他。
他微笑著,眼角有細小的魚尾紋,用手撫摸我的頭髮。“不可以。”他說。他看著我,突然笑容消失,他也許明白了我這不是在開玩笑。我是認真的。
他的手停下來對我說:“你知道的,我已經老了。”
兩天後我開始收到秀介發給我的簡訊,裡面細膩地描寫了他這兩天的生活,還有一些內心感受。他說,醫院的環境不好,醫生態度也不好,傷口略有感染有時候會很痛。開始後悔自己做的傻事。他也明白,我答應嫁給他不是真心的,只是為了敷衍他。
他發了一個笑臉,說,“祝你幸福,如果你不幸福受到欺騙,任何時候都可以回頭,我會在你身後等著你回頭。”
一個人若是尋到一個永遠守候在自己身後的人,是幸福的。真愛也不過如此。
接到簡訊後我本來想好許多感激的話來回他,但覺得虛偽,於是就只發了“謝謝”給他。
幾乎成了慣例,他每隔兩天發給我一條簡訊,寫他的生活與感受,我看完後不會回他。因為我明白我們不可能在一起。如果回他就是給他希望,給他希望然後讓他絕望這是極其殘忍的。
最後一條,他同我說,“今天精神很好,去了一趟醫院的花園,看到一叢開得豐盛純粹的花,摘了一朵碗口大的粉紅色花朵,想送給你。”
這並不是一個溫暖的夜。天下起大雨來,我趴在視窗向外張望,雨打在甲板上升騰起一片霧氣。
我整理出秀介的一些行李,幾件白襯衫,兩條破了洞的藍色牛仔褲,一些獎牌。大行李箱裡還有一個精緻的紅木盒子,我開啟來看,是一些日文信件與幾張發黃的彩色照片。照片上一個少女倚在一棵櫻樹下,黝黑的長頭髮垂下來,微笑迷人。照片後面有一句日文——“我愛這個櫻樹下的女孩。”
這是秀介的女朋友。和之前的那張照片一樣,黑色的大眼睛裡有憂鬱的光。她把愛與誓言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
雨漸漸停了,當晚清冷。我夢見秀介微笑著站在簡訊裡說的那片花園中央,伸出手,摘了一朵開得最純粹豐盛的粉紅色花朵,舉起來,說要送給我。
湄公河的這次乘船旅遊到達了目的地,船進總站了,叮叮噹噹的鐘聲響起。人們大多在昨晚就將行李整理好了,一到站,鐘聲響起,各色的人從船艙裡走出來,提著大大小小的旅行包。人們擁擠在一起,各種語言,各種聲音在我的耳邊迴盪,我倒覺得自己是座孤島,世間一切的聲音都與我沒有任何關係。
我提著兩個大的旅行箱,一個是我的,另一個是秀介的。英國男人一下船我便跟住他,“我沒有地方可以去的。”我追上他和他說。
“是,我知道。你不用擔心,我到現在還是愛你的。”
越南的大街很熱鬧,面板黝黑的亞洲人看上去總是親切的。有騎著平板三輪車的賣水果的小販,用一頭繫著塑膠袋的樹枝在驅趕蒼蠅,肥胖的黑黑的越南婦女,背上有她們的兒子靜靜地睡覺,幼小可愛。擺地攤,鋪一塊黑布賣假冒的古董。人聲喧鬧,忽然起伏的大聲咒罵。垃圾,油炸食品,水果,鮮花,汗液的味道混合發酵。
我們拐進了一家旅店。晚上我草草吃完了一盒泡麵,英國男人喝了酒,臉頰微紅,呼吸中帶著酒精的味道。他走過來,用手撫摸我的頭髮,俯下身子吻了我的眉心,我自小渴望這種帶著酒精氣息來自成年男人的親吻。
“我愛你,但你知道我們不可能在一起的。”
“是,我很清楚的。”
“我有未婚妻,我到越南是為了和她舉行婚禮的。因為她喜歡這個國家。”
我沉默,沒有回答,大腦中有一片白茫茫麻木的疼痛。
“對不起。”
“不用,不要向我道歉。”我說。“你的未婚妻是幸福的,有一個男人肯陪她到一個遙遠的國度舉行婚禮,我想見見她。”
他點了點頭。我想我如果苦苦糾纏,他也許會安排我以後的生活,會給我一些錢,彌補對我的虧欠。但我累了,不想再糾纏下去。
三天後。英國男人結婚了。新娘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不會說漢語。是個好女人,英國男人應該去珍視她。
我收拾好行李趕去參加他們的婚禮,他們剛好完成儀式車返回旅店。新娘金色的長髮與潔白的蕾絲一角搭在車窗外,在風中輕輕地飄動。我沒有看見英國男人,也明白那將是永別。
我提著旅行箱去長途車站買了一張單行車票,然後安靜地坐在車廂裡等待汽車發車。我看見外面的世界漸行漸遠。我似乎終於可以安然地說一聲:再見,英國男人。英國男人,即使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永遠不會知道。
我去了秀介的醫院,醫生告訴我,秀介因為傷口感染與破傷風已經去世,屍體已經火化。醫院聯絡過日本大使館,使館也聯絡過秀介在日本的家人,一直沒有回應。
我去太平間取出秀介的骨灰,廉價的木頭盒子上面用越南文歪歪扭扭地寫著秀介的名字,還有他去世的時間。那正是我夢到他的最後一個雨夜。那個夜晚我知道他真的是來和我告別與相約的。
我沒有哭,真正的痛與傷不需要多餘的眼淚。
10歲那年,我參加母親的葬禮,穿著白色醜陋的衣服。我被一大群人圍著,手裡捧著母親的骨灰,大人們嘈雜的聲音使我的聽覺麻木,我當時也沒有哭。
秀介的墓在鄉下,在臨近湄公河的一片稻田附近。我把他的行李和他一起葬了。
黃昏,我走在稻田的田埂上,看到成片的稻田與零星耕作的農民。路上沒有人跡,只有鳥聲清脆,田埂旁有一叢花開得豐盛濃烈,碗口大的花朵在風中招展,散發著蜜糖股的香甜。我坐在田埂上摘了一朵開得最純粹的粉紅花朵,別在頭髮上。惻然微笑,看到遠處秀介的墓,在夕陽中漸漸消失。我想這時候,秀介會笑,因為我踐行了他的最後一個夢境。
在人世,我唯一一份不用回報的真摯的愛完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