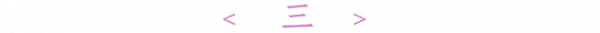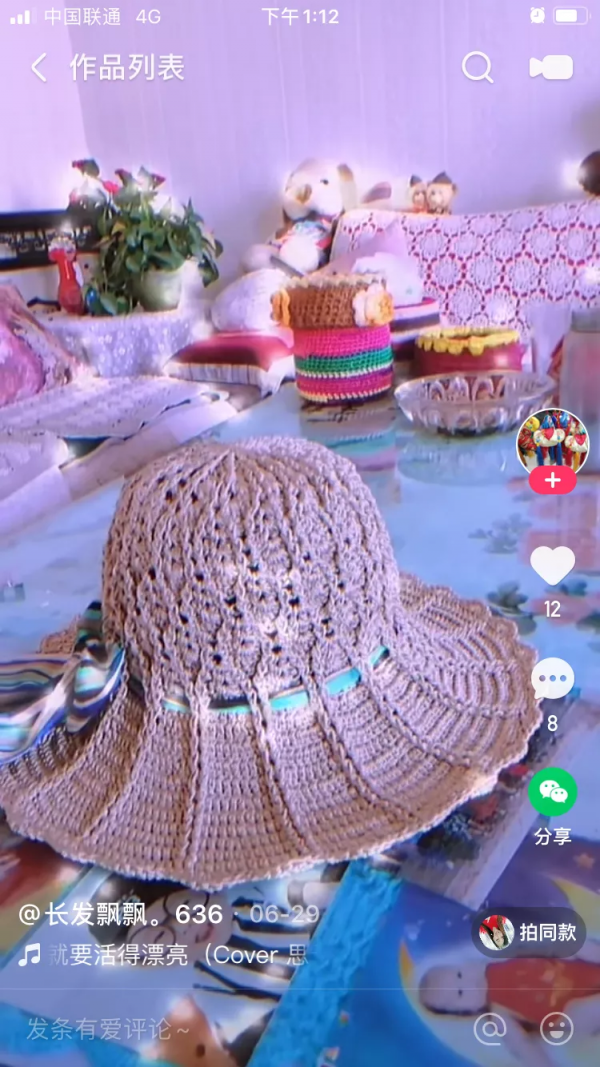2008年夏天,村東頭的春梅喝敵敵畏死了。
彌留之際,她忽然抓著婆婆的手說,“我不想死,我想活”。但短暫清醒後,她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
春梅想不開的原因是丈夫根兒的“杳無音訊”,倆人結婚不到一個月,根兒就去了礦上打工。春梅暈車不能一起去,後來有了女兒,更是整天守在家裡等根兒。
她想念丈夫,讓村裡關係好的、讀多書的作者堂嫂幫忙寫信,但接連寫了兩封,都沒有回信,也聯絡不到丈夫,思念成疾,再加上村裡人風言風語,連婆婆也說她得了花痴。
“對於鄉村人來說,沒什麼事兒,不年不節,又不是春忙秋種,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那絕對是浪費錢。
而情感的交流與表達,更是難以說出口的事情,他們已經訓練出一套壓抑自我的本領,性的問題,身體的問題,那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事情。
中國有幾億這樣的流動大軍,如果要考慮這些小問題,那不是太麻煩了嗎? ”
春梅死了,依舊沒人回答這個問題,甚至沒有人知道該如何作答。
而這只是《中國在梁莊》裡,作家梁鴻所記錄的其中一個發生在鄉村留守婦女身上的真實故事。
提起鄉村問題,人們的目光多聚焦在身體孱弱,孤苦伶仃的留守老人,以及從小跟父母分離,要早早學著長大的留守兒童。
但實際上,我們常常忽略了另一個弱勢群體——鄉村留守女性。這個群體內心的真實感受,在現代社會發展程序中,一直處於一種失聲狀態。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留守女性的人數日漸增多。
此前中國農業大學一項研究顯示,全國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萬留守婦女。
在丈夫們缺席的時間裡,這些女性要撐起一個家,照顧老人、小孩,甚至負責家裡土地的勞動。她們的身體是艱辛而疲憊的,而最艱難的是她們不被理解,也從未被看到。
現實生活中,有千千萬萬跟春梅一樣的鄉村留守女性,她們面臨著情感上的空虛,一條一眼望到頭的人生軌跡。
出生,出嫁,相夫教子,照顧公婆,好像只要按照這個路線好好活著,無病無災,就能算過得“不錯”了。
而家裡的男性出去打工後,只留下老人、女人和孩子,在缺乏防範的情況下,也引發了一些連帶問題,包括治安隱患。
從1993年到2009年,一名叫戴慶成的男子,在安徽省臨泉縣的鮦城、白廟兩鎮及相鄰的河南省沈丘縣,先後強姦婦女116人,其中未遂38人,搶劫91起(基本與強姦重合),盜竊23起。
而一些媒體對於這起惡劣的強姦案,關注的不是打工潮下農村治安難題,而是,強調“受害者大多沉默”,甚至把發生這麼多起案件的源頭,歸因於留守婦女的愚昧、怯懦、法律意識薄弱,這種譴責讓人心驚。
或許聽起來比較荒誕,但真的有受害女性給自己的丈夫打電話說明了此事,丈夫二話不說,從外地回來,結果是暴打了妻子一頓,然後覺得她不乾淨了,自此以後再沒回過家。
受害女性們,說或不說,身邊的人和環境都沒有給予足夠的保護和尊重。
而那些沒有受害的村民,大機率是表面上痛斥強姦犯,背地裡要傳一些風言風語,說受害者的壞話。
而鄉村中,喜歡傳八卦、潑髒水的又不僅僅是女人,還有一些覬覦留守女人的閒漢、二流子。
既得不到社會和情感的支援,又飽受輿論壓力的鄉村女性的艱難,無人知曉。
電影《系紅褲帶的女人》講述了一個真實事情改編的故事。西南邊陲的大山深處,漂亮的雲秀嫁給了阿旺,阿旺結婚時借了一個村裡二流子張二的錢。
張二催著還錢,想借機接近雲秀。為了早點還賬,阿旺決定去打工,雲秀想讓丈夫放心就係上一根紅褲帶,以表忠貞。
之後,雲秀在家中照顧父母,懷孕後也是如此。在辛苦的時候,是鄰居家的老實男人橋貴幫助了她,在她差點遭到張二強暴時,也是橋貴及時阻止。
但施暴者反咬一口,傳起雲秀和老實男人的壞話。人言可畏,連老實的公公、婆婆都開始懷疑起雲秀,他們都期盼著兒子回來。
八年過去,有人甚至傳言阿旺死了,雲秀一定會改嫁橋貴等等。這期間,張二依舊各種使壞,雲秀想依靠丈夫,但丈夫根本不在身邊。各種事情堆積下,由失望變成絕望,她也發現自己逐漸愛上了別人。
當她對橋貴說出那句“我要跟你過”的時候,是想要勇敢追求新生的,但沒想到八年沒有訊息的丈夫居然回來,而一直恪守著底線的橋貴因“朋友妻,不可欺”不告而別。
電影的結局是雲秀與阿旺離婚,她獨自帶著女兒種蘑菇過活。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電影中反覆出現過的——“我的命怎麼那麼苦啊!”
電影中的紅褲帶
這個故事也體現了鄉村留守女人的困境和難處,她們要做高強度的體力活,還會有很大的精神負擔。缺乏安全感,婚姻也不穩定。
雲秀能夠離婚已經是一種出路,還有一部分沒有生存技能,養不活自己的農村女人,不是不想離婚,而是不敢離婚。
而鄉村留守女性中,還有一類人在日復一日的消耗中,安於現狀,失去了進取心,她們的世界越縮越小,只有眼前的那一方小小天空。
36歲的田嬸子,讀過初中,剛過20歲就嫁了人,婚後生了兩個女兒,現在大女兒15歲,二女兒13歲,孩子住校,週末回家。丈夫在外地當電焊工,一年只回來兩次。
此前,田嬸子也外出務工,但因婆婆前幾年出了車禍,癱瘓在床,她回鄉照顧。丈夫每月寄回生活費,她也在園子裡種些青菜,兩年前,婆婆去世,她終於擁有了一部分私人時間。
而她目前最大的心願是生個兒子,閒暇時就玩手機,看快手,刷抖音,也會跟丈夫影片聊天。
村委會、婦聯都曾找過她,做個辦事員,但她感覺“自己就是個擺設,啥事情都沒做……”,最後,也就不去了。
於是,她的身邊沒有朋友,沒有子女,沒有丈夫,終日為伴的是一部似乎連線著外部廣闊世界的手機,但實際上,她的生活中只有自己。
鄉村留守女性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不安,艱辛,如同一潭死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們的青春、人生就緩緩逝去了。
這種生活的根源,充滿了無力與無奈,而它們恰好是最蹉跎人的地方。
那麼,如何突破困境、改變現狀就成了很多人關心的事情。
50多歲的麻芳英,在快手上直播賣手工藝品,每月還有200多元的額外收入,她獲得了家人所不能給予的成就感。
麻芳英的針織作品
56歲的蘇敏,決定逃開那段丈夫會拿起凳子砸她的婚姻,選擇自駕遊遠離家庭而在網路走紅。
她臉上的笑容變多了,整個人的狀態也變好了,得到了無數網友的關注和鼓勵,還接到了廣告,這樣的蘇敏是閃閃發光的。
最近對我觸動比較大的是,在紀錄片《無窮之路》中看到的一群佤族女性,她們一直生活在雲南阿佤山,佤族是“直過民族”,直接從原始社會過度到現代社會,所以思想很落後。
當地女性地位低下,很多女性連上桌吃飯的權利都沒有。她們也不能出去打工,很多人一輩子也沒看過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讀過初中的葉萍想要改變這種情況。
她想利用孟連位於咖啡黃金種植帶的地理優勢,帶領佤族婦女種植咖啡豆,建立咖啡合作社,“改變我們這一代女性”。
“城市的女人能做到的,我們也照樣能做到,我們也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不要看別人臉色過日子。”
於是,經過10年的辛苦耕耘,葉萍和相信她同村姐妹真的做到了,依靠種植精品咖啡豆,收入增加,家庭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她們自己賺錢自己花。
一個曾經連咖啡都不知道是什麼的女人,最後種出的咖啡豆連續三年拿全國性的大獎。
葉萍品嚐咖啡
這種改變無疑是令人振奮的,但改變的過程卻也艱辛、漫長。種咖啡豆的第一年就遇到霜凍,根本沒有什麼收成,第二年又遇到國際咖啡豆市場遭逢低價,接連不斷的打擊,別說靠種咖啡豆賺錢,葉萍反而是貼錢給那些相信自己的農戶。然後自己想辦法提升種植能力和咖啡品種的鑑別。
所以,這條路真的很難。
葉萍和她帶領的鄉村女性,何以堅持了十年?葉萍說,“不是因為希望才堅持,而是咬緊牙關堅持才看到希望。”
《人物》採訪曾經上過《半邊天》節目的鄉村女性劉小樣,她在旁人看來稍稍有些不一樣,“有飯吃、有衣穿就很好?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
20年過去了,我們發現她前後經歷了四次“出走”,但並沒有成功。
去過北京參加節目錄制,去過縣城當售貨員,去過貴州打工,也去過西安跟女兒同住,但她的這些嘗試都沒能幫她抵達那種“充實的生活”,反而開始接受心理治療。
沒有人理解她,丈夫,家人,村裡人等等,全都覺得她是個不找邊際的、異想天開的女人。
我覺得劉小樣,正是那些被困住且想要改變又失敗的代表。
鄉村留守女人的命運,需要從一個個微小的改變開始,去勞動,去賺錢,去改變現狀,去嘗試區別於當下的人生。
但她們的文化程度、生活的環境都限制了部分表達的能力,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城市女性們為自己發聲,卻極少聽到關於她們的內容。
即便有劉小樣這樣的女性,也無力對抗整個結構。因為自主改變是一部分,而其他人的關注與幫助是關鍵的助力,很多困難,需要放在整個時代,去追問社會才能得到解答。
要傾聽,要看見,更要理解和支援。
因為她們,也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