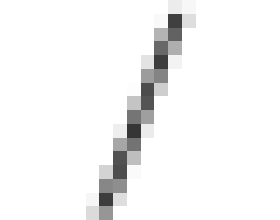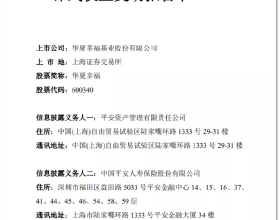來源:光明日報
【聽醫者講述】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深入研究傳導性耳聾和耳硬化症,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與內分泌科、神經外科一起書寫“垂體瘤”手術切除的奇蹟。他首創的懸雍垂顎咽成型術,讓睡眠呼吸暫停病人“舒服地自由呼吸”。他成功研製了國產單通道人工耳蝸,在國內首先開展人工耳蝸植入術,讓全聾病人從無聲世界重回有聲世界……作為我國著名的耳鼻咽喉科專家,王直中始終以事業為樂,樂在其中。
王直中教授學識淵博、睿智風趣,採訪中時常談起他對當下熱點問題的看法。他對病人的愛是發自肺腑的,他反覆強調,醫生要一身正氣、全心全意對病人,始終把病人放在首位。
1946年,我考到了同濟大學醫學院。教耳鼻喉學的李寶實老師對我影響很大,他為人很好,講課很有意思,加上耳鼻咽喉學的內容很豐富,往上可以到顱底、垂體,往下到口咽部,還可以到耳咽管,所以當時我想,以後我也要當耳鼻喉大夫。
畢業分配要填志願,三個志願我都填了協和,就是下定決心要來協和。1951年9月,我正式到協和工作。
耳鼻喉科初創時期,醫生耳、鼻、喉三方面的疾病都看,比較全面。在我做科主任的17年間,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人工耳蝸,二是喉癌病人的發聲重建,三是垂體瘤。
到耳鼻喉科我先做的是喉,那時候喉癌很多。慢慢我發現,一部分喉癌病人可以只把半喉切除,這樣還保留一個聲帶,經過發聲重建,聲音還可以出來。中耳炎我也研究了一段時間,搞鼓室成形術。由這個開始,我又搞了人工耳蝸,從耳結構一直搞到耳神經。
20世紀70年代,我和醫科院基礎所的陳仁塙一起研究人工耳蝸,有一點成果,原理其實就是把一個助聽器放在聾人的耳朵裡,他就聽見了。但我們研究的裝置有點大,術後耳朵旁邊容易留下傷口,所以第一例病人做完後,因為不習慣,就要求拔掉了。
最開始做人工耳蝸,病人不少,我們說做完以後可能只聽見聲響,聽不到說話聲,有些病人就放棄了。但其實在當時,能聽見聲音就很了不起了。我們先在成年人身上做,結果發現效果並不好,因為成人的神經細胞退化得太厲害。對比後發現,小孩的神經細胞還是活躍的,於是研究重點就慢慢地轉移到小孩身上去了。先對聾啞兒童進行測聽,檢查他們的聽神經殘留多少,然後根據聽神經的情況安裝分離式的人工耳蝸。
當時的人工耳蝸貼在耳朵外邊,一直震盪,實際上就是把一個共鳴器放在耳朵那兒,因為耳聾的人聽覺神經還在,如果安裝了振動器,調整好頻率,就可以聽見聲音。後來就是埋植型的,埋在骨頭上,增加骨傳導。再後來,就是在骨頭上打釘子,釘子上加個助聽器,各種各樣的人工耳蝸就都出來了。所以說,幫助聾人改善聽力,還是大有可為的。
由於要做耳聾的研究,就要知道耳聾的發病率是多少,所以我們到聾啞學校去,看看聾啞兒童到底有多少,也參加他們的教學活動,各方面都瞭解一下。另外,我們還進行了家庭走訪,主要是北京地區的調查。後來,上海、廣州等地也參照北京的方式進行了調查。最後發現,受傳染病、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的聾啞發病率比國外高得多。另外,一些先天性疾病得不到及時治療,也是致聾的重要原因。我們把這些資料向相關管理部門彙報後,也成為衛生部門工作的一個參考。後來,全國還成立了一個聾啞學會。在擔任中華醫學會耳鼻喉頭頸外科分會主任委員期間,我們搞學會活動、國際交流,還在各省市間舉辦學術會議、指導工作。當時每年至少要開一次全國的耳鼻喉科學術大會,透過全國大會的帶動,各地區的學術會議也熱鬧起來。這樣一來,中國耳鼻喉科的學術水平就整體提高了。
由於耳鼻喉科的患者比較特殊,有的說話說不清楚,有的聽不見你說話,還有很多時候是家屬來幫病人說話,所以醫生得加倍努力讓患者瞭解自己的病情。我總強調,對病人不要有偏見,要耐心地跟他們說話。我認為,對於醫生的培養,最重要的還是醫德。協和的辦院理念是要待病人如親人,要看一個大夫有沒有前途,就看他對病人的態度。如果病人一進門跌了一跤,你上去扶一下,那是好大夫;如果看病人穿戴不好,從心裡看不上病人,那說明醫德有問題。我對學生也是這麼要求的,學醫首先要全心全意對病人,一個醫生好不好,任何時候都會表現出來。有一次查房,科裡一位年輕大夫跟在後面,我看他嘴巴一動一動的,就問他在吃什麼,結果是在嚼口香糖。我說,查房為什麼吃口香糖?他答不上來,說他錯了。我說對,你就是錯了,查房的時候吃口香糖,說明你心不在焉,那你不必查房了,到門口待著去吧。我這樣糾正了他的錯誤,其他人看到他被懲罰,以後就沒人敢在查房時吃口香糖了。
我認為,醫療、教學和研究要三合一。搞醫療不搞研究,那醫療就沒基礎了;搞醫療、搞研究但不搞教學,那就後繼無人。所以要把這三方面都搞好,其中醫療是最重要的。醫生還是要把病看好,要看病,就必須多讀書,不鑽研是不行的。英文書、德文書,要看原版,所以一個醫生的外語必須好,有了掌握語言的能力,才能進入開放的世界。此外,醫生要一身正氣,否則歪風邪氣就來了。如果一個年輕醫生能在吃飯的時候還忘不了病人,那就差不多了。
(本報記者田雅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