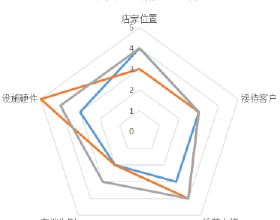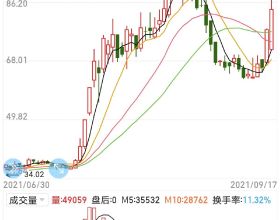蒙古帝國解體後,明代中國與亞歐大陸其他文明之所以呈現歷史分途,一方面源於不同的地緣政治環境。隨著蒙古帝國的解體,西歐擺脫了由其帶來的巨大威脅,俄羅斯面對的是勢力嚴重削弱的金帳汗國,阿拉伯文明則已實現對蒙古的伊斯蘭化,從而皆不再面對完整而強大的蒙古勢力。與之不同,明朝僅將蒙古勢力驅逐出長城以外,被稱為“韃靼”的北元與東進的瓦剌,一起對明朝構成了嚴重威脅。
不僅如此,西域地區的東察合臺汗國,雖然已是伊斯蘭文明的組成部分,但對於明朝而言,其仍是蒙古帝國的強大繼承者。至於東北亞的女真部族,雖勢力分散且弱小,但也是滅亡前一個漢族政權北宋的金朝後裔。因此,在整個北部邊疆,明朝都面臨著比歐亞大陸其他文明更為嚴峻的軍事威脅,這是明代中國與其他文明呈現歷史分流的客觀背景。
但另一方面,其他文明雖然不再受到蒙古勢力的威脅,但彼此之間的長期對峙與不斷戰爭,也構成了向外擴張的地緣阻礙。尤其是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長期衝突,一直是歐亞大陸史的重要內容。
因此,明代中國之所以選擇不同的歷史道路,還應與其自身有關。地緣政治僅構成了明代中國與亞歐大陸其他文明歷史分途的客觀背景,但決定這一歷史分途的直接原因是明朝的政權性格。明朝政權性格的形成,源於朱元璋的個人經歷及其建立明朝的過程。
元朝之滅亡,與整個蒙古帝國衰亡一樣,是在14世紀亞歐大陸範圍內自然災害與民族獨立潮流夾擊下,逐漸土崩瓦解的。14世紀中期,旱災與繼之而起的腺鼠疫瀰漫亞歐大陸大部分地區,不僅在歐洲形成滅絕大部分人口的“黑死病”,而且在中國同樣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朱元璋父母便死於瘟疫,年幼而貧困的朱氏兄弟只能借錢將父母草草掩埋。
作為元朝的滅亡者,明朝在元末紅巾軍起義中異軍突起,在並不太被看好的情況下,取得了最後勝利。紅巾軍最早在河南起事,在劉福通領導下,河南紅巾軍一度北伐,進至大都、大同與遼東,儼然對元朝形成包圍之勢,但最終未能成功。河南紅巾軍失敗後,紅巾軍開始重點向南方發展,主要有:朱元璋在江淮流域,陳友諒在長江中游,張士誠在長江下游,方國珍在東南沿海,明玉珍在四川盆地。其中方國珍、明玉珍在邊緣地帶割據一方,並不具有全域性意義。主導南方紅巾軍形勢者,便是朱、陳、張三支紅巾軍力量。
在三支力量中,陳友諒佔據長江中游,俯視朱元璋、張士誠,力量最盛,尤其是水軍最強大。張士誠佔據江南財富之地,又據有南宋舊都,他利用這一地緣形勢,籠絡士人,復興文治,儼然以兩宋正統繼承者自居。與二者相比,朱元璋崛起於淮河流域,此後雖佔領南京,但在軍力、財富上不可與陳、張相提並論。但朱元璋最終的成功,卻正與其出身淮河流域密切相關。
淮河是中國古代南北分界線,長期是南北戰爭不斷上演的核心地區,社會動盪不安。五代十國之割據攻伐,南宋與金朝、蒙元的長期對峙,使淮河流域淪為名副其實的邊疆地帶,進一步惡化了這一地區的生存環境。在朱元璋的崛起中,淮河流域提供了兩大支援。
一是淮河流域相對於長江流域的戰略優勢。長江素有“天險”之稱,也是中國歷史上偏安江南的地方政權賴以生存的天然屏障,但這有一前提條件,即南方政權保有淮河流域。淮河流域是長江流域的大門,這既因為淮河流域地勢較高,控制著長江流域的咽喉,也在於淮河流域自然條件與長江流域較為相似,一旦北方政權佔據此地,便可掌握與利用當地的水軍,長江天塹優勢便不復存在。朱元璋憑藉淮河流域,便在地理上對處於長江流域的陳友諒、張士誠政權形成戰略優勢。
二是與陳友諒政權由不同派系構成、內部存在一定矛盾不同,也與張士誠標榜文治不同,朱元璋及其主要追隨者,即所謂的“淮西集團”,都出身於淮河以南的濠州(今安徽鳳陽)一帶,不僅較為團結,而且都在長期武裝化的社會環境的薰陶下,鍛煉出較強的軍事能力,並磨鍊出邊疆地帶堅韌、粗鄙、注重實際的風格。正是由於朱氏政權整合度高、內部認同性強,朱元璋才有指揮自如的優勢。
朱氏政權崛起於淮河流域,對明朝政權性格產生了重要影響。淮河流域是近世時期落後的農業地帶,朱氏家族世代務農,朱元璋出身貧寒,這皆使朱元璋養成了謹慎保守的性格,甚至由於經歷坎坷而導致缺乏安全感。在這種區域背景、個人性格影響下,朱元璋在設計國家制度時,努力將國家權力保持在朱氏皇族手中,實行保守內斂的國家政策,以免滋生影響政權安定的因素。
明初擁有當時世界最為強大的軍事力量。明朝驅逐元朝,並在蒙古高原與北元展開多次大規模戰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一舉扭轉中唐以後漢人武力不競的歷史頹勢,其陸軍實力毋庸置疑。陸軍之外,明朝水軍實力也屬當時世界最強。與歷代中原王朝不同,明朝是唯一崛起於南方、最終統一北方的政權。在南方長期戰爭中,朱氏政權與其他紅巾軍政權一樣,都在南方湖泊遍佈的地理環境下發展出十分強大的水軍。張士誠、方國珍皆走私海鹽出身,地盤又在東南沿海,擁有強大的水軍,在情理之中。而崛起於長江中游的陳友諒,水軍實力更強。朱氏政權雖然崛起於淮河流域,但能憑藉巢湖水軍奪取南京,其水軍實力自然也不可小視。朱氏政權水軍火器配備尤其齊全。在鄱陽湖水戰中,朱元璋針對陳友諒船艦巨大、較為笨重的缺點,藉助風勢,利用火攻,從而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國初群雄事略》載:“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炮礮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曜,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二三萬人,流屍如蟻,彌望無際。”從這裡描寫的戰爭場面,足可見鄱陽湖水戰之壯觀。
鄱陽湖水戰後,朱元璋軍隊繳獲了陳友諒水軍大量船隻、裝備,從船艦名稱也可以看出其形制巨大。“獲鉅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這支龐大的水軍極大地壯大了明朝水軍實力,也成為明朝強盛於周邊海洋國家的重要籌碼。《明太祖實錄》載:“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若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繇渤海,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當之。”
但在如此強大的實力基礎之上,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卻明確宣佈“守在四夷”,從而確立了保守與內向的疆域立場。朱元璋在《皇明祖訓》裡告誡子孫: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可見,朱元璋雖然擁有強大的水軍實力,但從淮河流域農業社會的經驗出發,在國家財政上,從南宋、蒙元將農業財政、海外貿易相結合的新制度中退縮回來,並鑑於其他支系紅巾軍殘餘、日本浪人在東南沿海可能造成的威脅,實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間開展海外貿易,實行依靠農業財政,補充國內商稅的傳統稅收政策。在邊疆觀念上,相對於具有豪放開拓氣概的漢唐王朝,明朝也是一個極大的倒退,具體表現為退出西域。
從14世紀世界史的視角來看,明朝疆域政策使中國在世界近代史開啟之初,便選擇了與世界主流背道而馳的歷史方向。蒙古帝國消亡後,俄羅斯文明將蒙古牧業傳統與自身牧業傳統相結合,從而大力擴張,推廣牧業經濟,建立起牧業邊疆。伊斯蘭文明將蒙古牧業傳統、重商傳統與自身牧業傳統、重商傳統結合起來,同樣大力擴張,推廣牧業、商業經濟,建立起商牧邊疆。基督教文明利用蒙古帝國西傳的中國科技,開始了在全球範圍的遠洋貿易與海外擴張,建立起商業邊疆。而明朝由於崛起於落後的農業地帶,對蒙元開創的農業、牧業、商業相結合的混合經濟形態缺乏興趣,因此基本仍屬農業邊疆。明朝受到蒙元時代的正面洗禮最少,反而接受了其“家產製”政治觀念的負面影響,進一步將中國推向保守與內向,在邊疆開拓上動力不足,仍侷限於傳統的農業邊疆。
值得反思的是,陳友諒佔據長江中游的湖廣行省,統治核心為以漁業為生、以白蓮教為紐帶聯合起來的長江漁夫。張士誠、方國珍居於長江下游的江浙行省,皆以販賣私鹽為生,活動範圍又及於東海,統治核心是以鹽業為生的江海鹽商。相對於朱氏政權,這三個政權的統治群體與海外貿易具有更多的關聯,但卻未能取得最後的成功。這是自先秦以來,農業文明不斷消滅的商業文明,再次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主導作用。這其中蘊含了中國與亞歐大陸其他地區何種不同的地緣政治?這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這一時期亞歐大陸其他文明的歷史取向主要是外向開拓,與此相反,明朝並未充分利用其雄厚的國家實力與有利的國際條件,順應民間向外擴張的歷史訴求,最大限度地實現疆域擴張與文明推廣,而是有意不事邊疆開拓、壓制民間活力。或者說,明朝的歷史取向主要是內向收縮的。明朝的這一做法,不僅主動放棄了西域這一中國的傳統勢力範圍,而且未能追隨南宋以來民間開拓南洋的步伐,不僅為伊斯蘭教擴張提供了地理空間與歷史契機,而且在西歐基督教文明開創的世界近代史潮流之初,便體現了強烈的逆向封閉特徵,從而逐漸由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到與西方世界的距離越來越大,這對世界近代道路的形成具有深刻影響。因而,“長城以內”其實是鮮明而準確概括明朝的歷史取向與特徵的詞彙。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