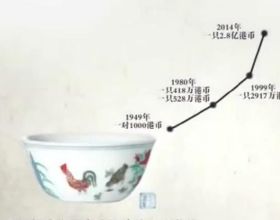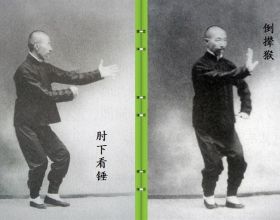文/孟澤輝 辛丑年農曆七月十五
歷史上的“走西口”,也叫“走口外”“跑口外”。最早從明末清初開始,清末民初形成高潮,綿延不斷歷時200餘年。走西口是中國歷史上規模較大的人口遷徙活動,是一部悲愴的苦難史。正如原版《走西口》唱得那樣:“走到殺虎口,碰見個舊朋友,他把我留在家裡頭,喝了一頓糠糊糊。走到石匣子溝,兩腿腫了個粗,受苦人不怕(那)腿腫粗,就怕強人(來)把命收。”真可謂是“晉北災民淚滿襟,離鄉背井訴悽音。清朝口外開邊地,一曲悲歌唱到今”。
內蒙古廣袤的草原,自古為北方少數民族的遊牧地。清末民初以後,隨著對蒙古地區實行全面放墾政策,取消了農民進入蒙古草原的限制,中原尤其是山西地區的漢民為了謀生,紛紛湧入長城以北的內蒙古察哈爾草原墾荒、經商或從事小手工業。走西口的人們由最初的“雁行”發展為定居,農業村落逐年增加。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察哈爾右翼地區漢名村莊近千,茫茫草原點綴其農家村落,顯現出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融合。
走西口與歷史上其他移民活動一樣,所選擇的道路同樣充滿了艱辛與悲涼。在酷暑嚴寒惡劣的環境中,身背鋪蓋和乾糧,披星戴月沿著漫長而崎嶇的路生死未卜地跋涉。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並不一定能順利到達預想的目的地,或淪為乞丐,或拋屍半路,“細麻繩繩捆鋪蓋,兩眼流淚走杭蓋”,真實地道出了他們離鄉走西口的悲涼心境。
由此聯想到我的祖輩,打聽到內蒙古大草原,牛馬成群,肥肥的綿羊遍地都是。吃得是牛羊肉,喝得是馬奶酒,穿得是羊皮襖,鋪得是牛毛氈,出門隨便牽一匹馬來,想去哪跨馬揮鞭,像是在天堂裡活著。民族地區的生活情景,既心動又產生出無限的憧憬。於民國初年,從山東武城流落到內蒙古豐鎮,後轉輾到陶林(今察右中旗) 一帶謀生,嚐盡了人間的疾苦.
北方地區曾經家喻戶曉的民謠: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上老鸛窩。追溯內蒙古各地漢族祖先大都為洪洞縣移民,古槐後裔遍佈全區各地,以察右後旗為例,漢族姓氏高達530多個,沿用原故地村屯名稱,或以墾荒建村人的姓氏為名的村莊比比皆是,這些獨具特色的地名,都在時刻提醒人們時常回首那段悲情歲月。
值得提起那些具有傳奇色彩的晉商,他們是口外商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我現居包頭市的發展也要歸功於晉商。包頭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過200萬。但在一百多年前,這裡還只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莊。隨著晉商的崛起,包頭也逐漸由一個小村變為商賈雲聚、百貨雜陳的繁榮城鎮。至今這裡還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
聽起來悽婉的《走西口》民歌, 字裡行間充滿了走西口人的辛酸悲壯,勾勒出一幅生死離別的圖景,讓人不禁為之動容。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走西口移民的到來,使內蒙古地區的農業、商業、手工業和城市建設等各方面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從而加速了這一地區由遊牧草原文化向半農半牧以及農耕文化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後,烏蘭察布各旗縣外出務工者高達百萬之眾,他們滿懷希望地離開故土,呼包兩市是他們最集中的地區,他們所帶來的物流、人流、資訊流已形成區內經濟大流量的互動。縱觀他們走過的足跡,雖然不像走西口那樣悲壯,但是也經歷了常人無法想象的艱辛。雖然走西口已成為歷史,但走西口的烙印仍然隨處可見。所以,移民的歷史值得追溯探討,移民的文化值得挖掘書寫,移民的故事值得留存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