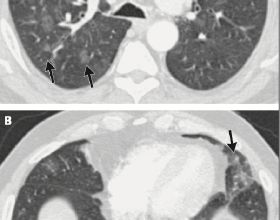“天蠍座暴脾氣舍友回來後因為我潮溼的頭髮或是當時直接在宿舍吹頭產生溼氣重,她不分青紅皂白語氣十分忡地說我怎麼不動動腦子,接著她就特別煩躁地彎下腰透過那密密麻麻的東西把鬆掉了的電源給插上了。雙子座舍友看到此景忍不住替我解釋到:她有可能是懶,換成我也懶得去彎下腰來弄。當時我很感動她為我說話,同時覺得好委屈”
“後來玻璃心的我又一次躲在床上拉上床簾發洩情緒,悶聲哭泣。我經常這樣做,這樣不會影響別人同時還能發洩情緒,但每次哭完第二天依舊笑眯眯的,像個沒事人一樣。”
“我這次特別鬱悶,我找我的雙魚座下鋪訴苦,讓她當一回我的心理諮詢師,和她說了挺多她也不斷安慰我。後來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滿腦子都是對那位暴脾氣舍友的吐槽,在腦袋裡過了一遍又一遍。那天晚上我邊哭邊想,越想越委屈,為什麼自己每次都要做受氣包呢?”
“想著想著我就失眠了,到凌晨一點多,因為臉上都是乾巴巴的淚痕,我只好下床到陽臺上洗臉,關上陽臺門,傳來一句冷不丁的話語:門關緊了嗎?我默默地嗯了一句,發現我的鼻子上還插著紙巾,那是為了不讓鼻涕一直流出來,聽起來有一點鼻音。我又默默地自我催眠,就這樣到了凌晨3點多左右,我發現我頭痛欲裂,身心疲憊,我想著白天我還有表演還要上課,我得緩緩,要不然明天又要從雙眼皮腫成單眼皮。”
“‘明天都會好的’我心裡想著,於是在不知不覺中睡了過去。到了第二天早上,果然我的雙眼皮變成了單眼皮,我打算去琴房練聲,走在路上都是同學,我不敢抬頭用我腫腫的眼睛面對她們,反正感覺自己的眼睛也睜不大,自卑感也油然而生,要知道五官中最好看的眼睛腫了,那就真的醜了。”
“我就這樣吃完早餐,去了琴房,後來我的文學院朋友來了,她問我眼睛怎麼了,我說我昨天晚上哭了,她說怎麼回事呢?我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並又開始哭起來,她安慰了我,併為我打抱不平,我們練習完了節目就一起去食堂吃飯……”
“後來我回到宿舍,我拼命想讓自己緩解情緒,但是一回來滿身的食堂味外加我的汗味讓她嫌棄地問我身上是什麼味?接著便和其他舍友說我之前也是這個味道隔著床都能聞到(她是我對床)……
“我心裡本來就特別沮喪,聽她又這麼說,心中的弦突然繃不住斷了,怒氣直衝腦門:我說,我有遺傳的疾病,我得了狐臭!她居然回了一句:那沒什麼啊,吃個藥就可以好了。我又回懟:你以為吃個藥,或做個手術就可以治好了嗎?手術我曾經也想過,但是做手術有後遺症還會留疤,所以我也不打算這樣做。‘那就每天噴藥,藥用多了也沒有了。’她說。
“我終於忍不住,便也學著她經常對我說話時的那種好像別人欠了很多債的語氣說:我每天都有塗藥,這樣還臭的話,如果你有更有效的藥推薦給我,那我就試試啊!她表示沒有,我說完之後,衝到陽臺,拿下毛巾捂住我的臉,強迫自己不要爆發,不要讓自己流淚,但是也許是已經觸碰到了我內心最深處的導火線,我終於抑制不住失聲痛哭,把這幾天的不甘和怨氣,一併地發洩出來。”
“下鋪(雙魚座舍友)跑出來安慰我,我就像一隻得了瘋牛病的牛,憤怒而絕望地說:不要再折磨我了,我不要這樣,我今晚還有演出……然後甩著毛巾,雙魚座舍友她知道我為什麼難過,也拼命緩解我的情緒。許久後開啟宿舍的門,我又異常的變安靜了,就好像隔著道門,門裡門外不是同一個世界,回到床上默不作聲地躺著。
“之後,我們就開始冷戰,第二天她把原先要給我伴奏的兩首歌推了,並給我找了其中一首歌的伴奏同學,我想她這樣大概是想和我決裂了吧。後來我的其他舍友們看不下去了,她們都私下來勸我們雙方的人不要再這樣冷戰下去了……”
看到這就沒有了,微光好奇接下去發生了什麼呢?她居然也忘得差不多了。她覺得當時自己其實也挺幼稚的,但如果換成現在的自己,還會不會做同樣的舉動呢?
很奇怪的是腦子裡好像裝了過濾器一樣,會自動把不開心的經歷給過濾了。這樣也罷,人總是得放下已經過去了事,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微光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