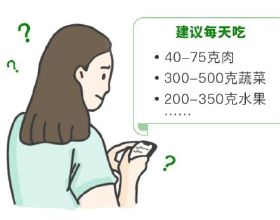作者:董立晶
《地獄公使》由韓國導演延尚昊執導,根據同名網路漫畫改編。這部最新的網路熱播劇對神、人、宗教、公理、公權提出了拷問與質疑,同時也表達了資訊社會中人該如何自居的思考與反詰。該劇有非常明顯的分水嶺,前三集為神對人的懲戒,後三集為人對神的反抗,而在構建這兩部分時,導演力圖處處為續集“留白”,無形中造成了敘事的撕裂和邏輯的難以自洽。但這些並不能遮蓋延尚昊導演在劇中所要表現的自省和保留的溫存,同時在劇中對“看客”“救救孩子”和“覺醒者”的描摹。
在前半部中,神的宣告和預示,都是針對一些有“劣跡”的人,而新真理教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大肆宣揚懲戒的正義性,以期獲得公眾的認可和追隨。在劇情一開始就出現了“地獄公使”懲戒罪人的“奇觀”,如果說這一事件僅僅是公眾的偶遇,那麼對於樸靜子死亡的直播,則無疑成為新真理教樹立威權的公祭。弔詭的是他們跪拜的並非神本身,而是錯愕驚恐的律師閔惠珍,這一鏡頭已經預示了閔惠珍必將成為新真理教的“敲鐘人”。新真理教為尋找能夠合理存在和發展的根基,大肆渲染被處刑者的罪行,直播處刑過程,以增加其威望和震懾力。但從所懲處的人所犯罪行來說,未婚生育、公款私用、賭博,這些都“罪不至死”,而作為殺害熙庭母親的兇手,卻逍遙法外,須靠人力透過“非法”途徑解決。這樣的矛盾和分裂,自新真理教誕生伊始就存在,也必將因此導致其最終的坍塌。如果說新真理教是愚弄民眾的發令人,箭簇群體無疑成為施刑的屠刀和劊子手,在狂熱的躁動下支配著無魂的軀體。警察與法律本應是平民和公共秩序最好的護衛者,但新真理教的首任議長鄭晉守對警察陳京勳的“賄賂”卻讓警察對新真理教緘默不語,並且在眾多公權部門魚龍混珠,致使新真理教的勢力急速壯大和膨脹。
作為被選為神諭宣誓物件的被執行者和普通民眾,是沒有反抗力的,只能被動地接受。如今我們置身網路社會,幾乎每天都在上演著“你未殺伯仁,伯仁卻因你而死”的悲劇。我們生活在密閉的鐵屋之中,手握一把無形短劍,不知是刺向他人,還是朝向自己,亦或在些許的罅隙中苟延。無論是劇情一開始的“路人”淡定拍攝死亡的過程,還是樸靜子的直播,還有那些戴面具的看客,人們的冷血、漠然已經到了無以附加之地,根本不是在看對同類的斬殺,而是參加狄俄倪索斯酒神的狂歡,是對他者也是對自我的一種公然的祭祀。樸靜子被直播處刑之所,就是一個舞臺,看似孤獨的舞者,觀者眾多,在場的警察、律師、媒體,戴面具的資助者,臺下的一眾看客,不在場的鏡頭背後的操縱者和熒屏前的觀眾,就像瘟疫一樣蔓延開來,而此時的樸靜子不再孤單,儼然成為一位領舞者。舞臺化的表演,“看”與“被看”產生了移置,模糊了界限,人人皆是“看客”,同時也都成為“被看”的客體與風景。沒有人質疑新真理教的合理性和神諭的公正性。“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而二者的“規”與“矩”在何方,選擇與執行的標準又是什麼?沉默螺旋的漩渦在不斷地擴大。
接下來的劇情有了反轉。新真理教為了維持自己的公信力,需不停地直播被宣告者及家人的懺悔和死亡執行過程,對於人本身的定義已經完全喪失,毫無任何隱私可言,這些都是新真理教最終跌落神壇的鋪墊。而鑄就這些罪惡的恰恰是人類自己,我們親手編織了這樣的羅網。
作為覺醒者的代表——律師閔惠珍,出於對自己曾經簽下樸靜子直播合同的救贖,亦在自己死而後生之餘受到揭露新真理教的責任的驅使,成立了蘇塗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將被處刑者或被處刑者的家人。蘇塗意指神道色彩的特殊區域,諸逃亡者至其中即可得到庇護,“以彼之道,還彼之身”。但這個蘇塗組織無力反抗神諭,只能反抗新真理教,避免被處刑者公開處刑牽連家人,也希望找到一個機會能夠揭開新真理教的真面目。新真理教利用超自然力或者稱為神諭選擇被處刑者而樹立權威和公信,隨著裴英宰、宋昭賢新生兒的被宣告處刑,成為新真理教和蘇塗組織較量的關鍵。閔惠珍接受了眾人“朝拜”,便肩負起了扯下新真理教“遮羞布”的重擔,保護被神諭者及其家人的隱私,讓世人看到新真理教的真面目。當三個“公使”殺死了新生兒的父母,新生兒發出的那聲啼哭,成為對新真理教致命的一擊,預示著新真理教的坍塌和神諭的終結。
但是新真理教為何跌落神壇?“地獄公使”諭旨的規則又在哪裡?普通大眾到底會走向何方?最後復醒的樸靜子是下一個惡魔還是天使?那些被處刑的鬼魅該在地獄中如何自處?這都是劇中留下的伏筆和懸念。“一粒沙中見世界,一朵花裡見天國”,在資訊科技高度發達的現代,元宇宙的建立,幽靈與肉體、身心異構、身心合體,在這樣的虛擬與現實中,又會幻化出怎樣的世界與人類?《地獄公使》所表達的,是韓國的特例,還是世界的共性,值得我們當下人仔細思考。
正如電影《沙丘》的最後一句臺詞“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這僅僅是開始)”。
(作者董立晶系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管理博士)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