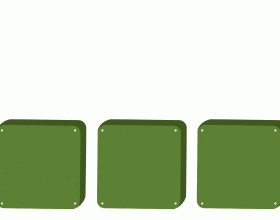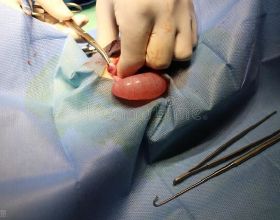問任何一個失眠者,睡眠對他意味著什麼,你立刻會明白睡眠的重要性。睡眠影響著我們清醒時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心境、精力水平、認知、記憶、免疫系統、新陳代謝、胃口、焦慮水平等等。睡眠還影響著我們和周圍的每一個人、乃至和自己的關係。
本文經授權節選自《腦子不會好好睡》(臺海出版社)。該書講述、分析了14個真實的睡眠病例,本文選取了第14章的失眠病例,內容有刪節。前往“返樸”,點選文末“閱讀原文”可購買此書。點選“在看”並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2021年9月26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出2條留言,贈書2本。
撰文 | Guy Leschziner(倫敦國王學院神經病學與睡眠醫學教授)
翻譯 | 高天羽
無論睡眠剝奪目前如何定義,千百年來它一直被用作審訊或酷刑手段。關於它最早的正式記載出現在15世紀晚期,使用者是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在之後的幾百年裡它一直受到重用,從16世紀蘇格蘭的獵巫行動到蘇聯克格勃設立的審訊營,直到今天,它無疑還存在於世界各地的黑暗角落之中。
誠然,睡眠剝奪不會給身體留下傷痕,但它不僅會造成心理傷疤和精神痛苦,還可能高度危險。雖然對於人類,還沒有人用適當的科學方法研究過長期的系統性睡眠剝奪,但在動物身上,研究已經證明這會致命。狗如果被強迫保持清醒,在4-17天后就一定會死。同樣,大鼠也會在清醒11—32天后死去。
暫且想象你遭受了這樣的折磨。你的全部渴望就是抓緊幾分鐘睡上一覺。你感覺思維混亂,視線模糊,四肢也疲累到疼痛。你的身邊並沒有一個宗教裁判員或是關塔那摩守衛,看你一有睡著的跡象就立刻把你搖醒。搖醒你的是你自己,是你的腦:你是你自己的行刑人。你失眠了。
第一次走進我的診室時,克萊兒就已經病了,雖然看起來不像。表面上,她衣著整潔,50出頭,身材苗條,相當漂亮。她的樣子就像許多成功富有的女性,大踏步走在倫敦橋附近的街上,多走幾步就能到金融城。但過去五年裡,她卻被失眠折磨得筋疲力盡。
她的睡眠是在接近更年期時開始惡化的,但在她心裡,促成失眠的直接原因很清楚:“在家照顧孩子15年之後,我決定重返職場。失眠的部分原因,是50歲的我急切地想在職場證明自己。我其實薪酬很低,但責任很重。我肩負著一項使命,就是證明自己配得上這份工作,是有價值的人。”
聽起來,為了給人留下好印象,她像是給自己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不僅如此,她還要為加薪鬥爭。“在更年期開始前,我的睡眠就不好了,但那時我只是[對自己]說:‘我睡不好覺,夜裡會醒。我只是睡眠不好而已。’但白天我還是能工作的。”
然而工作上的事似乎把她推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下我再也睡不著了。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但我真的感覺有大約一年的時間,我的深度睡眠少到了無法正常生活的地步。”我又問了她在那段時間的睡眠模式,她說:“我還是會上床躺下,但是一走上樓梯,我就開始恐慌了。我知道前面會有什麼。接著我的心跳開始加快。還沒到驚恐發作的地步,但我能感到腎上腺素在全身流動。”
對上床睡覺這一過程的焦慮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她越是害怕自己難以入睡,就越是給失眠問題火上澆油。克萊兒接著說:“我在床上一躺兩小時,然後知道這樣是睡不著的。於是我就起來,下樓給自己泡一杯花草茶,在廚房裡走幾圈,讓燈光一直保持很暗,然後再上樓試著入睡。”但睡眠總是遙不可及,這種痛苦對她的身體和情緒都造成了傷害。
“我開始覺得煩躁。有時我會叫醒丈夫,哭得幾乎歇斯底里——我很討厭自己這樣。他總是特別溫柔,盡力讓我平靜下來。他總是說出最貼心的話,真不簡單。到天快亮時,我大概能在半夢半醒間很淺地睡上一會兒,醒來時覺得昏昏沉沉。”
從這時起,她就慢慢墜向了無底的深淵。缺乏睡眠使她在工作中更難達到自己的要求,這進一步加重了她的焦慮,也使睡眠變得更難企及。“然後我就精神崩潰了。”她說。
失眠者在半夜醒來,看舉世皆睡我獨醒,這種孤寂真是無以復加。克萊兒有寫睡眠日記,她寫道:“別的家裡人都睡著了,而我只有絕望,因為我已經試了許多法子,但每天夜裡我還是會下到這裡(起居室)。這感覺太寂寞了,好像永無盡頭。”
但其實她並不孤單,絕對不是,因為失眠的普遍超乎想象。如果你也像克萊兒一樣覺得難以入睡、入睡後容易醒來或醒來後感覺睡得很差,那你就是這個巨大群體中的一員。失眠是最常見的一種睡眠障礙,患者人數遠超其他疾病。成年人中,約有1/3自述過睡眠不佳的情況;1/10長期失眠進而造成睡眠體驗持續低下,也在白天造成各種後果,如疲倦、易怒、注意力難以集中、缺乏動力等等。但失眠不僅是一種醫學病況,它還是一種症狀,可能體現了甲狀腺亢進這樣的醫學問題,也可能是服藥的後果。失眠可能是多種精神障礙的表現,如焦慮、抑鬱或雙相情感障礙。實際上,失眠患者中有一半都診斷出了精神疾病(不過這也說明另一半沒有)。即使背後沒有其他潛在問題,“失眠”本身作為一種醫學障礙也是一個“口袋”術語。它包含不同的型別,而說來奇怪,並不是每個失眠患者都缺乏睡眠。
對有些人而言,他們睡眠不好的體驗得不到證據的支援。我很少會帶失眠患者進睡眠實驗室。如果你在家就睡得不好,那麼在身上貼了電極、躺到陌生的床上、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受到記錄和分析後,你肯定更難入睡。不過,如果需要了解患者失眠的原因,或者懷疑他們還有別種睡眠障礙,我還是會讓他們在醫院住一夜。
有一種情況非常普遍:當我在睡眠監測之後見到患者,問他們睡得如何時,他們會說:“那晚睡得特別糟。”但是檢視監測結果時,我們卻會發現結果顯示睡眠質量很好:至少七個小時,中間有大量深度睡眠—雖然面前的患者還是一口咬定自己只睡了一兩個小時。這類失眠被稱為“睡眠狀態感知障礙” (SSM) 或“矛盾性失眠”,它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失眠患者和正常睡眠者的睡眠監測之間會有巨大的重疊。這樣說的人,他們體驗睡眠的方式與常人不同。或許他們的睡眠質量確實不好,但這一點無法用標準的睡眠監測技術“多導睡眠圖” (PSG) 來衡量。或者原因可能只不過是:在正常睡眠中人也常會短暫醒轉,但腦會將這些醒轉的時刻填補,當作睡眠的一部分;但上述型別失眠的患者卻會把這些時刻當作清醒,而不是睡眠監測所顯示的深度睡眠。
還有一類失眠者,他們的睡眠可能支離破碎,每晚中斷數次,但他們的睡眠總量仍在正常水平。即使是那些睡眠總長較短的人,深度睡眠量可能也是正常的,而深度睡眠正是對身體和精神的恢復最重要的睡眠階段。
但對克萊兒這樣的重度失眠者,還是有明確的證據顯示他們的睡眠時間確實很短,有時每晚只有短短几個小時。在這些睡眠時間很短的人身上,我們也清楚地看到了壓力的生理指標,即所謂的“過度喚起”。神經的悸動、飛快的心跳、全副戒備的狀態、激動或警惕的感覺,這些都是過度喚起的特徵。人承受壓力時,多種神經遞質和激素就會產生作用。應激或焦慮的狀態會激發體內的多種系統,造成皮質醇、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水平升高。在失眠患者、主要是睡眠時間較短的那些人身上研究這些系統,我們發現他們的尿液中上述激素的分解產物有所增多。此類失眠者也顯示出“過度喚起狀態”的其他特徵:夜間心跳加速,耗氧量升高(說明代謝速率升高),瞳孔變大——這又是交感神經系統活動增強的表現,而交感神經系統又負責調節“恐懼-戰鬥-逃跑”反應。重要的是,這些變化在“睡眠充足”的失眠者身上是看不到的。
常有人把失眠和睡眠不足混為一談。睡眠不足或說不讓自己睡夠的健康風險已有詳細記錄:可能有死亡、增重、高血壓和糖尿病等無數種情況。因此,失眠者自然會擔心這些問題:幾十年的睡眠質量低下想必也會對健康有同樣的破壞嘍?然而睡眠不足和失眠還是相當不同的。如果在睡眠實驗室裡研究睡眠不足的人,你會發現他們能很快入睡,但醒時在警覺性測試中表現很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睡眠時間較短的失眠者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入睡,但醒時也警覺得多。
另外,睡眠時間較短和睡眠時間正常,這兩種型別的失眠也有極為重要的區別。兩類失眠都與腦的過度活躍有關。使用成像技術監測腦波,我們會發現兩類失眠者在睡眠中腦部活動都有增加,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睡眠狀態感知障礙患者或說睡眠時間正常的失眠者會把睡眠當作清醒,或者睡過後也無精打采。不過,只有這些睡眠時間短的病人才會表現出全身高度活躍的狀態,這體現在心率一類的化學和生理指標上。雖然對兩類失眠者來說,腦部活動所受的影響都大大降低了睡眠的主觀體驗,但是許多和失眠有關的健康問題,似乎都僅限於那些睡眠時間較短、且生理上的過度喚起不只影響腦部也影響全身的人。研究者觀察了自稱失眠者的認知表現,並沒有發現他們和正常睡眠者之間有什麼顯著差別。但如果進一步在失眠者中將睡眠時間正常(哪怕質量較差、斷斷續續)的失眠者,和經客觀測量時間確實較短的失眠者區分開,就會發現有顯著認知問題的都是睡眠時間較短的失眠者。相比之下,沒有失眠問題但睡眠不足的人,不會表現出和過度喚起有關的激素和神經遞質活動及心血管方面的指標,也不會表現出相同程度的認知問題。
同樣,對失眠患者開展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的風險分析後也會發現,那些經適當測定睡眠時間確實較短的失眠者,患這些病的風險較高,而那些至少睡夠6小時的人相應風險完全不會增加。研究甚至顯示,睡眠時間短的失眠者死亡率都比常人略高,但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似乎和睡眠不足不同。我們知道睡眠和體重增加相關,那麼有沒有可能,睡眠時間極短的失眠者也會增加體重,從而更易患上糖尿病、高血壓及各種相關疾病呢?並不,睡眠時間較短的長期失眠者似乎並不比睡眠正常的人更容易增重。實際上和正常人相比,他們反而更不容易肥胖。可能過度喚起產生的化學及生理效應才是推高死亡率的直接原因。
皮質醇是一種天然類固醇,它和血壓上升及糖尿病的增加有關。一部分病人患有自身免疫神經系統疾病,而我們常會看到他們服用類固醇壓制自己的免疫系統。類固醇使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增加,相關的化學物質如腎上腺素的分泌也會增加,這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心臟和血管,造成血壓無法在夜間正常下降。
總之,睡眠時間嚴重縮短的失眠帶來的上述生理效應,應該就是在指示人在激素和心血管狀態方面的相關生理變化,且似乎也應為失眠承載的一些健康風險負責。而對於那些睡眠時長合理的失眠者,雖然有證據顯示他們的腦部活動異常,但從身體的角度看,他們還是和睡眠正常的人更為相似。
那麼,是什麼在嚴重失眠者身上激起了過度喚起狀態,使他們睡得很少呢?到底是這些失眠人士過短的睡眠引發了過度喚起,還是過度喚起狀態造成了失眠?答案還不完全清楚。但在有睡眠狀態感知障礙(即主觀認為睡得很差但睡眠總時長正常)和沒有失眠問題但睡眠不足的兩類人群身上,這些化學物質和神經系統的活動水平都很低,這顯然說明是過度喚起狀態本身引發了失眠的這些嚴重型別。
這其中毫無疑問有遺傳因素的作用。失眠常常在家族中流行。雙胞胎研究顯示,57%的失眠可以用基因解釋。最近的一項研究確認了7個與失眠有關的基因,因此這種過度喚起的狀態也完全可能有遺傳易感性。人在承受壓力、換新工作、感情不順、家人離世的時候,都常會有一段時間的失眠和過度喚起。而如果你剛好有那些基因,又剛好遇到了這些應激源,你就可能有更高的風險進入那種精神和身體都過度興奮的狀態,且這種狀態在應激源消失後仍會持續存在。在這種過度警覺或說喚起的狀態的驅使下,你的失眠就可能轉變為慢性。
這其中顯然也夾雜了心理因素。正如前文所說,大約一半慢性失眠患者背後都有精神障礙,尤其是焦慮,過度喚起正是焦慮的一個顯著表現。因此焦慮本身即可造成失眠。而那些沒有焦慮問題的人、另外一半沒有任何精神障礙的人,又如何呢?
我在門診接待的許多病人都沒有驚恐發作的情況,白天也不會憂心忡忡。但許多人都講述了相同的經歷:他們說白天裡感覺很好,但是一到夜裡要上床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擔心,尤其對入睡的過程特別擔心。他們焦慮於自己會無法睡著,會整夜翻來覆去。他們生活在對前方長夜的恐懼之中。當他們的腦袋沾上枕頭,他們不是將舒適的床鋪和進入幸福睡眠的喜悅聯絡在一起,而是將臥室看成了一個經受折磨的地方、一件刑具。他們常會反覆地說:
“我剛上床的時候還覺得疲累不堪,但只要燈一關,我的心思就飛速轉動,意識清醒無比。”正是在這一刻,他們變得過度喚起,他們的腦“興奮極了”,睡意也瞬間遙不可及。就像西西弗斯馬上就將石頭推到山頂、結果石頭卻滑脫雙手一路滾回山腳那樣,睡眠也成了這些患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眼看就要睡著,睡意卻突然被奪了去。這種狀態持續越久,相應人群和睡眠的關係就越糟。
我第一次見克萊兒時,她認為或許是自己的某幾項性格特質導致她走到了這一步。還有,當我們討論她患病之前的睡眠情況時,她告訴我她的睡眠一直多少受生活中其他事件的影響。是什麼引起了她的過度喚起狀態,她自己和我都很清楚。“我認為是工作的壓力,是我為工作給自己施加的壓力。都是我自己造成的。”她對我說,“因為重返職場時我已經上了年紀,我需要證明自己。別人可能就會有非常不同的反應。但我的天性就是想把工作做好,而且我對任何批評都很敏感。所以回家後我會為這些[批評]而苦惱,還一遍遍地在心裡重放它們。”
她也知道自己的過度喚起狀態:“我後來發展到了無法入睡的地步。正常人扭一下就能入睡的開關,對我已經沒用處了。不管是白天打盹還是晚上就寢,我都做不到。”她描述的是失眠者白天難以入睡的典型困難,以及過度喚起狀態造成的格外警覺,“我的腦子努力想維持運轉,於是不得不製造大量的腎上腺素,所以始終保持警醒。它就是不肯去休息的地方。”
經過幾年糟糕的睡眠之後,克萊兒撞上了一堵牆。
“事情發生在我提加薪的時候。和老闆的談判很辛苦,我快承受不住了。我的狀態不斷下滑。因為缺乏睡眠,加上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我陷入了深深的抑鬱,不知該怎麼擺脫。接著抑鬱加重了失眠,失眠又加重了抑鬱。我開始一把一把地掉頭髮,掉了怕有一半。但我覺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了。”
到我見克萊兒時,她已經診斷出了焦慮和抑鬱。她因為精神問題去看了醫生,在試了一圈藥之後,終於找到了一種效果很好的抗抑鬱藥。“好像是我們試的第四種藥吧,一下子產生了很好的效果。短短几周,我的感覺就好多了。我的睡眠並沒有自動變好,但心境改善了太多。就像是撥開了烏雲。我一下子意識到20年前我生孩子時就多少有些抑鬱了。這藥改變了一切。”
雖然找對了藥,但她的焦慮和抑鬱依然存在,睡眠也依然糟糕。她參加了幾種專門針對睡眠的新藥試驗,其中一些產生了短暫療效,但接著就消失了。另一些加劇了她原本輕微的不寧腿綜合徵,不幸地使她的病情更添複雜。她還嘗試了名為“接納與承諾療法” (ACT) 的心理治療,其核心是教導患者接納乃至擁抱自己的失眠,由此減輕缺覺造成的壓力感,但它對克萊兒毫無作用。
在精神崩潰之後,她的失眠又持續了一年。現在她每晚10點筋疲力盡地上床,但剛一躺到床上,她說自己就又會產生那種熟悉的警覺反應,失去那個通向睡眠的開關。睡眠之於她,就彷彿竿子吊著的胡蘿蔔之於驢子,每每彷彿就要夠到,卻又總是從眼前溜走。她會先在床上躺三四個小時等待睡意,最後又總是放棄,起床下樓。到了凌晨三四點,連續清醒20多個小時帶來的疲憊壓倒了靜脈和腦部奔湧的腎上腺素和皮質醇,她終於睡著了。但到了早晨六七點她又會醒來,根本用不著鬧鐘。
失眠和心理或精神問題間的關係很是複雜。正如前面所說,在嚴重失眠中常見的過度喚起狀態,背後可能是某種形式的焦慮。睡眠過短的失眠者常具有特定的心理特徵,如心境低落、疲憊以及對健康的焦慮。睡眠狀態感知障礙患者的狀況和嚴重失眠者有某種程度的重疊,也會心境低落且焦慮,但他們往往把時間花在鑽牛角尖上,一遍遍地思考自己的狀態,還會產生無法控制的想法。因為這些心理狀態的細微差別,加之相關激素和心血管指標的生理紊亂,有些研究者提出,這兩種失眠是根本不同的。睡眠時間正常的失眠患者即SSM人士,並沒有過度喚起的身體表現,因此也罕有長期後果,對治療似乎也有更好的反應。而生理上會過度喚起的短時睡眠者,即負責調節“恐懼—戰鬥—逃跑”反應的化學及生理系統被放大的人,則有不同的心理特徵,有更高的風險出現和失眠有關的健康問題,往往也更難治療。
總之,精神問題肯定能引起失眠。90%的臨床性抑鬱患者都有失眠。我還在醫學院做學生時,就學到了在凌晨醒來是抑鬱症的重要標誌,但是其他型別的失眠,如難以入睡、入睡後易醒等,也是常見的現象。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有嚴重失眠,而精神病漸要發作前,當事人也常會出現入睡越來越難的徵兆。但睡眠和精神障礙的關係不是單向的。失眠也是引發精神障礙的一個風險因素,並可能使精神障礙更難治療。即使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光是失眠本身就會顯著增加後續患抑鬱症的風險,特別是對短時型失眠患者而言。而對於已經患上抑鬱的人,失眠則標誌著自殺意念的增強及抑鬱復發風險的增加。抑鬱患者如果也有失眠問題,他們的病情將變得更加複雜難治。
許多問題仍無答案。這個科學領域還處在嬰兒期,無論是睡眠和精神健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還是這種關係背後的原理,我們都還沒有充分理解。失眠和精神障礙都會改變腦內的迴路和生化反應,因此,睡眠和精神健康的變化會對彼此產生連帶後果也便不足為奇。兩者都既是雞,又是蛋。但是也有可能,失眠和精神問題是由共同的遺傳因素造成的,果真如此,該領域的研究就會更添一層複雜。無論兩者關係的本質為何,它都強調了精神科醫生和睡眠科醫生需要有整體思維,不能只關注自己最熟悉的問題,在為患者治療時不能只戴著本專業的有色眼鏡。
作者簡介
蓋伊·勒施齊納(Guy Leschziner):神經科主任醫師,專長於睡眠問題,主持隸屬於倫敦蓋伊與聖托馬斯醫院的歐洲最大睡眠中心,並服務於國王學院醫院、倫敦橋醫院、克倫威爾醫院等多家倫敦醫療機構。擅長失眠、夢遊、發作性睡病等多種疑難睡眠障礙的診治,並透過報刊、電視、廣播等多種媒體(如《金融時報》、BBC 等)向公眾介紹相關知識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