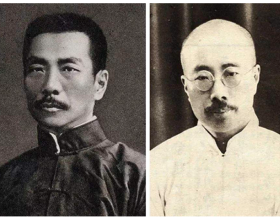“詩酒豪情,風流頓覺蓬山遠。浮生悲劇,病榻忽興春夢哀。”——臺靜農
縱觀葉公超這一生,真是應了這幅輓聯,半生瀟灑,半世悲哀。
他是我國有名的批評家、文學家和書法家,也是那個時代名聲赫赫的外交家。
他桃李滿天下,紅顏知己不在少數。前半輩子,眾人環繞,鮮花著錦,烈火烹油。平生只得一壺酒便可論道,長醉不復醒。
這麼一個孤傲、清高又純善的人,卻在晚年政壇滑坡遭罷棄,處境悲涼,門可羅雀。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孤獨地躺在病床上,睜大著眼睛向門口望去,嘴中執著重複一句話:
“我的太太女兒都要回來看我了。”
然而直到他耗盡身上最後一絲力氣,門外仍是靜悄悄的,光滑的地板上照著門扉,瞧,是如此乾淨,那是無人來的證明。
讓葉公超臨終之際唸叨的妻子袁永熹,與他結婚已有50年。他們是典型的“師生戀”代表,是大學教授與青春女學生的浪漫結合。
她與葉公超初結婚,就引起眾人熱議,風流倜儻的葉公超竟選擇了一個清冷寡言的女子,性格並不算匹配。
但在他們婚姻持續了將近10年,被外界稱作“天作之合”之際,袁永熹卻帶著一雙兒女遠赴美國,此生再未踏進國土。
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婚姻,在一起相處時間短短不足10年。或許,這兩個看似互補的人,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壞脾氣文人
葉公超幼時雖然父親離世,但在叔父葉恭綽的精心教養下,並未生出任何寄人籬下的自卑感。
相反,他從小脾氣就大、性情驕傲,不說同學,就連長輩惹他不開心了,該罵還是得罵。
但就這麼個直性子、口無遮攔的人,在讀書做學問上,從沒讓人擔憂過。
一路讀到了英國劍橋大學的碩士生,畢業後任職於法國巴黎大學研究員,他愣是放棄這份在他人眼中極好的工作,眼巴巴的回國來。
一回到國家,他就去了北大任教,前前後後又擔了暨南大學、清華大學等國內知名學府的學科教授。
外出時他春秋四季皆著西裝,頭式右分,梳理的一絲不苟,全身一塵不染。這是一個很注意個人形象的人。
但葉公超的性情著實算不上好。在上課時,他並不經常採用傳統的老師講課方式,而是讓學生按照座位順序一個接一個輪著讀課本。
讀完一段落,他再揮手以示停止,懶散問道:“有哪裡不懂的嗎?”
若是有學生不懂提問,他就會大聲斷喝一句:“查字典去。”
若學生繼續發問:“這些字在字典中查不到。”
他則挑眉,提高音量:“你那個字典沒用,換《牛津大詞典》。”
然後風平浪靜,朗讀繼續進行,直到這節課結束。
就這麼個看似不著調的人,卻被人尊稱“文藝才子”。
葉公超在職期間,在學校開辦多個跨度極大的課程,從英國文學到英國戲劇,從小說、現代詩到戲劇等等。
就這些看著風馬牛不相及的課程,他卻遊刃有餘,侃侃而談。
人們總是對優秀的人報以寬容,他的行為自然也被外人打上一層濾鏡,誇讚他不拘一格,有名士作風。
這時候的葉公超稱得上一聲風流倜儻、豪情萬丈。從未經歷過波折的他,從不屑於和他人虛與委蛇,他向來習慣直擊目標。
在授課的時候,葉公超看上了姿容出眾又文采斐然的趙蘿蕤,他並未有什麼顧慮,直接找上來對她直抒思慕。
但趙蘿蕤思索之後,選擇拒絕這個明星教授的追求。
她誇讚葉公超的學識,讚賞他的能力:“他屋裡的書遮滿牆壁直碰到天花板。他一目十行,沒哪本書的內容他不知道。”
但是,趙蘿蕤對這個教授的性情卻敬而遠之。
在她看來,這個男子即使有再多的能耐,但不能約束自己的脾氣,就像是在自己身旁擱著一個隨時會爆炸的炮筒,終有一天會傷人傷己。
被趙蘿蕤拒絕的葉公超並沒有糾纏,既然女子無意,他自不能做惹人反感之事。且世間女子何其多,這個不行那就換個。
這時,另一個女子袁永熹出現在他的面前。
袁永熹是燕京大學的校花,她眉目清冷,不施粉黛,渾身散發著高山積雪般的冷清與乾淨,性情內斂。
再反觀葉公超,卻是眉目舒朗,喜交際,處事熱情,性情外露。
有一種說法是,性情截然相反的人正適合在一起,因為他們在一起能互補,組成一個完美的圓。
葉公超匍一遇到袁永熹,就被她清冷的氣質和不做作的行事所吸引。
袁永熹和他在一起時,不會多說什麼話,特意做某種舉措吸引他的目光,就那樣自然的立著,靜靜聽著他的豪言壯語。
在一旁大說特說的葉公超看到袁永熹這般恬靜的模樣,整個人也眉目舒緩,不由笑了起來。
他想,這是自己想要的,真正和自己契合的女子,是他想相伴一生的伴侶。
他打聽袁永熹的愛好與過往,投其所好,發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勢。
這麼一個俊朗又優秀的男子追求自己,袁永熹常年無波瀾的心湖也開始泛起漣漪。
俗話說得好,烈女怕纏郎,尤是這麼一個潔身自好、優秀出眾的郎君。
袁永熹剛畢業,1931年6月30日,這一對相愛的人就舉辦了婚禮,宣誓了相伴一生的承諾。
夫妻相處
袁永熹同意葉公超的追求,並和他結婚。這一訊息傳出來,很多人都不敢信。
在他們看來,這就像是兩個世界的人,一個於熱鬧喧譁地,一個於冰冷器材室;一個眾人環繞、侃侃而談,一個周身冷清,獨自做實驗。
他們都很優秀,但他們似乎並不如何相契。
但婚姻相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過得好不好,幸不幸福,還得當事人現身說法。
葉公超擔任大學教授期間,常常有學生、弟子前往他家拜訪,請教學問。
在他新婚後不久,就有一名弟子去了葉公超家。
剛一進門,只看到一個面若清湯、布衣素釵的女子,坐在桌子旁靜靜讀書。葉公超介紹這是自己的夫人袁永熹。
在弟子和老師交談期間,袁永熹端來一盞茶之後,就坐在不遠處繼續看書,未插入他們的對話。
她和葉公超之間什麼都沒說,但卻能看到他們偶然間視線轉移,眼光撞到對方眼中,然後相視一笑。
弟子離去後和同伴感概,葉老師和師母真是天生一對,情誼深厚。
結婚不過一年,袁永熹就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小千金,葉公超取名為“葉彤”。
沒幾年,袁永熹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是個小子,取名為“葉煒”。
兩個孩子的名字都來自於詩經:“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在孩子的名字中,深深藏著葉公超對妻子的愛慕,是他對她的深情告白。
那時候所有認識他們的人都讚歎這對夫妻間的感情,稱讚袁永熹,認為她是標準的賢妻良母。
但感情從未有一帆風順的道理。正如諸多戀人的情誼經得起狂風巨浪,卻消磨於柴米油鹽。
葉公超和袁永熹之間的感情,不可避免被生活瑣事所困擾。而葉公超不加掩飾的脾氣也進一步加大了這段婚姻的裂痕。
一天晚上,吳宓到葉家做客吃飯,席間飯菜不合葉公超的口味。
葉公超像是點燃了引線的炸藥桶,爆炸了。
他把筷子摔倒在地,當著客人的面,指著袁永熹大罵。形勢就好像是捅了馬蜂窩,眼看著一發不可收拾。
但面對丈夫的指責,袁永熹並未反駁,她立在一旁靜靜地聽這些傷人的話語,不發一言。
在葉公超發洩完之後,她才據理力爭:
“作為主婦,飯菜不合口味,我有責任。但是你當著客人的面發脾氣,也是不合適的。”
此言一出,場景頓時靜默,葉公超的一腔怒氣也剎那間煙消雲散,他更是覺得羞愧,向袁永熹道歉。
本可能大肆爭吵的情況沒有出現,一切都被袁永熹三言兩語給壓了下去。
吳宓更是對袁永熹大加讚賞,他甚至在《吳宓日記》誇讚道:“深佩熹為一出眾超俗之女子。”
但這件事就真的過去了嗎?葉公超的那些話真如白駒過隙,不留心間?
不,不是的。葉公超的每一句所謂的“直言快語”,就是一句傷人的話,是釘在人心間的釘子。
他道歉,釘子被拔除了,但是釘下來的痕跡還在。
裂痕已經造成,牆體已經破敗,只需一個意外,就如推手一般,輕輕一推,牆倒了。
“意外”很快出現。
變故橫生
因戰亂,國土淪陷,葉公超把妻兒送往國外避難,夫妻間的感情僅靠書信脆弱的維繫著。
毛公鼎
又因為袁永熹性格內斂,不會說那些什麼情、愛、思念的話,葉公超便以為妻子對自己感情有變,不喜歡自己了。
這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一時間,他也不怎麼往國外去信。夫妻倆人的感情陷入了僵局。
這時候,葉公超接到叔父葉恭綽的來信,請求他幫忙守護毛公鼎,他懷疑自己的妾室潘氏會出賣我國文物訊息,透露給日本人。
毛公鼎是我國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781)時的一件重器,其鼎腹內鑄有3行銘文,是迄今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篇什最長者,共有497字(另一說是499字)。在中國青銅器的奇珍行列中,具有無可取代的珍貴价值。
毛公鼎自清道光末年出土以來,就引起各方勢力的關注,沒有任何人或國家不想把它據為己有。陰差陽錯下,毛公鼎到了葉恭綽手中。
但毛公鼎的到來,對於葉恭綽來說,禍要大於福。一國重器又豈是一介個體能保護的了?
眼看毛公鼎危在旦夕,出於對叔父的感激與一片愛國之心,葉公超毅然趕往上海。
他在日本憲兵隊搜查葉府前轉移了毛公鼎,但自己卻被逮捕。
為了洩憤,日軍對他施以鞭刑、水刑等殘酷刑法,這個錚錚男兒全都忍了下來,閉口不言,以待時機。
期間,堂妹葉崇範去探望他,葉公超透過葉崇範給友人傳信。
在日軍攻勢和緩之時,葉公超又立馬聯絡堂妹,讓葉家找人偽造假的毛公鼎。
終於,依靠上交的贗品和鉅額保釋金,葉公超在被關押折磨了49天后,終於走出監牢,得見天日。
毛公鼎事件讓葉公超受盡了折磨,而在磨難之間,葉公超不可避免的對堂妹葉崇範有了好感。
在最低谷、生死難測之際,有一個溫柔的女子伴在左右,為自己四處奔波。葉公超無疑很感動,他甚至把這種感動給誤以為是愛。
葉崇範對於多學多才的表哥早是崇拜不已,芳心暗放。郎有情,妾有意。兩人開始在一起出雙入對,曖昧難掩。
剛開始,葉公超還告誡自己,無論如何,他們是名義上的堂兄妹關係,不能做這等“禽獸”之事。
而且自己又有妻有子,也是萬萬不能做出背叛家庭的行為。
但葉公超看著堂妹尊崇與依賴的眼光,感受她的嬌俏與美好,他竟似靈魂出竅,心虛的享受著不應該享受的一切。
沒多久,他就徹底陷入這個年輕少女用溫柔織成的緊羅密實的網中,難以自拔。
這個年近40歲的男子與青春正好的女子陷入名為“愛情”的漩渦,葉公超也認為自己重回年少時光,有著少年人獨有的躁動與期待。
一對男女之間有了情況,一舉一動都是破綻,這對堂兄妹的關係也開始暗暗傳開。
遠在美國的袁永熹卻不知國內發生的諸多變故,她只從其她人口中聽到語焉不詳的訊息,葉公超出軌了他的堂妹。
袁永熹甚至不敢相信這個訊息,她從未認為過葉公超會背叛他們的感情,背叛這段婚姻。
這個看似萬般不看在眼中的袁永熹,對葉公超早已情根深種,她只是不善於表達自己,不代表她沒有自己的訴求和堅持。
她很快趕回國內,找到還沉浸於與堂妹之間愛情的葉公超,逼問他,是不是真的要放棄這段婚姻,選擇她人了。
葉公超,夢醒了。
他很慌張。他是很感激堂妹對他的付出,也受用於她的溫柔小意。但他從來沒想過和袁永熹分開。
這個有著大男子主義的男人,前所未有地卑微了下來。
他對袁永熹撒謊,之前和堂妹的那些傳言都是假的,她可是他的堂妹,兩人怎麼可能在一起。
袁永熹選擇相信丈夫的說辭。
豈料,沒多久她得知真相,葉崇範是葉恭綽的養女,她和葉公超根本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這無疑又是一個巨大的打擊,袁永熹必須要對丈夫的“背叛”做出決定了。
她想起了小時候,父親離世,只剩幾個年幼的孩子抱團取暖,袁永熹和兄弟姐妹沒有長輩看管,沒有人愛護,甚至沒有任何經濟來源。
但他們仍是相互扶持著,站起來,靠著變賣家中的古董字畫才得以生存下去,繼續讀書。
這是她悲痛的過去,但這個不幸的經歷卻也造就了這個女子寧折不彎的錚錚鐵骨。
她不會撒嬌,不會說那些好聽的思念的話,但她極盡所能的包容著葉公超的幼稚和憤怒,一點點把這個小家庭經營好。
她對外表現冷漠,對內仍有拘謹。
看著絕對理性,也只是因為她知道哭鬧沒用,道理在你這就是你對,人心不在你身上,強行挽留也沒有用。
或許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一團火和一塊冰怎能共處?
袁永熹最終仍是沒有哭,她只是沉默著,收拾傢什,牽著兒女踏上離家的路程。
至於被她扔在身後的丈夫,聽著他的懺悔,她心中已不再有波瀾,傷痛積累到一定程度,早已麻木。
孤苦終老
愛人離去讓葉公超好一番頹廢,而毛公鼎事件也改變他以往的想法,他不想再停留在原先的地方,孤枕難眠,也不再畏懼政壇風波。
在董顯光的邀請下,他去了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駐馬來亞專員,隨機也離開了這個傷心的地方。
憑藉優秀的英語水平,葉公超展露出自己少有人匹敵的外交能力,他不備稿,僅憑紮實的語言水平和學識能力即興發言,驚豔全場。
他被人稱為“外交奇才”,他步步高昇,從駐他國專員到外交部常務次長,又到外交部部長。
他在外風光無限,狂蜂浪蝶無數,卻被他溫柔一笑皆拒絕。回到家中,開啟燈,只有孤零零的房間,連空氣都沉默了起來。
袁永熹則在美國加州大學做物理學研究員,她整日沉浸在實驗室中,觀望著儀器表上的數字。
偶爾空閒下來,還是會忍不住想那個人,想他的笑他的怒,他的抱負他的無奈。
他們仍沒有離婚,一個在美國,一個臺北,心照不宣地維繫著這個名存實亡的夫妻關係。
有時候葉公超參加宴會需要女伴,袁永熹會特意趕過去。
她挽著他的臂彎,陪著他走進宴會廳,在旁邊聽著他與其他政客的交談,靜靜的沉默的笑著,一如往昔。
等到宴會結束,走出大門,她會毫不客氣地甩下他的胳膊,轉身踏上回美國加州的路,不和他說一句話。
這種狀態持續多年。
一直到1961年,因蒙古加入聯合國的事情,葉公超夾在美國與老蔣之間左右為難,成為老蔣出氣的工具,被急召回臺,卸下身上職務。
以往賓客如雲的場景不再有。這個妻兒不在身邊、身無權勢的男子,開始畫畫。
畫蘭花、畫竹。因為墨竹最能抒發他的抑鬱,他更多畫的也是竹。
偶爾和幾位老友聊天,談及家人。他還嘴硬道稱,妻兒不能理解他的追求與事業。
面對他人揶揄的笑聲,葉公超仍執著道:“本來就是。”
但有時會帶上一句嘆息:“有家難回。”
就這樣孤零零的生活著,回憶著。到了晚年,葉公超的身體愈發不好了。
他住進醫院,纏綿病榻之際寫了《病中瑣憶》,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回想這一生,竟覺自己是悲劇的主角,一輩子脾氣大,吃的也就是這個虧,卻改不過來,總忍不住要發脾氣。”
是啊,回望這生,他因這個性情錯失太多,愛情、親情也拋他而去。
他已是明白自己年輕氣盛時犯下的那些錯誤,但時光不再重來,袁永熹也不會給自己彌補的機會。
她一向自得其樂,一個人也能過得好的,更不要說兒女也都在她身邊,伴她左右了。自己這個丈夫和父親,倒是真的無人問津。
葉公超的病越來越嚴重,偶爾有老友過來探望他,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一番寒暄後也將離去。
他一直在想自己的家人,病重的訊息也讓人傳過去了,但為何妻子和兒女還不來看望自己。
葉公超躺在病床上,眼睛痴痴地望著門外,他渴望一個場景,妻兒推開門走進來對他說,原諒他了。那他就滿足了。
但他什麼都沒等到。
一直等到葉公超重病離世,袁永熹和他的一對兒女也沒有回到臺北,只有袁永熹託人送來的一副輓聯:
“烽火結鴛盟,治學成家心虛安危輕敘別。丹青遺史蹟,幽蘭修竹淚痕深淺盡縱橫。”
此生不見,親近之人皆離心離身,就是她對葉公超最大的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