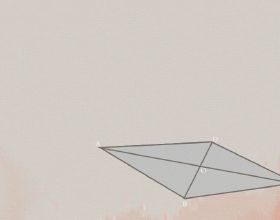在福州市千年古街三坊七巷,古厝、古街、古樹、榕樹交相輝映。新華社記者 魏培全攝
在我國悠久的文學傳統中,“文”與“史”的交織幾乎貫穿古典文學史始終。對於古代先賢們而言,“文學”與“歷史”並非截然二分。“柔日讀經,剛日讀史。”“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經”“史”“文”三位一體,構成古代士人的基本知識框架和心靈結構。今天我們在閱讀古代典籍時,亦不難體會到文史哲不分家的古典傳統所留下的鮮明印記。讀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我們說這既是“史實”也是“詩歌”;讀到《史記》中那些令人蕩氣迴腸的故事,我們說這既是“史家之絕唱”也是“無韻之離騷”;讀到《莊子》中的鯤鵬、游魚、神龜、大椿,我們說這既是“寓言”也是“哲理”……試問上述哪個是“文學”哪個是“歷史”?是否必須區分出哪個是“文學”,哪個是“歷史”?
今日“文學”與“歷史”的分割,很大程度上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運動的產物。從現代學科建設的意義上看,“文”與“史”的分家有積極的一面,但同時也需要意識到用西方的“分科”觀念審視中國本土的“文學”與“歷史”書寫,難以避免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身”,從而強行將活生生的機體割裂開來。由此,“文學”與“歷史”這樣一個對中國古人來說原本不是問題的事情,在今天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性特徵的問題。那麼,在新時代的文學活動中,能否跳出過度強調分化的西方現代文學觀,重新啟用優秀的文史合一傳統,進而創作出真正體現中國特色、彰顯中國氣派的當代作品?作家簡福海的歷史散文集《歷史的斑紋》(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從散文創作的側面為這種可能性提供了一個頗具現實意義的案例。
這本散文集以曾經居住在福州市三坊七巷一帶的近現代歷史人物為物件,為讀者描繪了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仁人志士的群像,包括林則徐、沈葆楨、陳寶琛、林覺民、陳衍、嚴復、林紓、冰心、林徽因、廬隱等。這些不同領域、不同遭際、不同性格的歷史人物之所以能出現在同一本書裡,除了他們的人生都曾與三坊七巷結下不解之緣,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都承載著百年中國在走向現代、救亡圖存的艱辛探索中所必然留下的歷史傷痕。“斑紋”是這段歷史抹不去的印記。而作者正是透過捕捉歷史在三坊七巷留下的層層斑紋,為今人講述一段段不應被忘卻的往事,透過藝術書寫,生動呈現近現代歷史人物的心靈歷程。
在嚴謹的歷史學家看來,歷史不是“故事”而是“事實”的累積。就文學而言,亞里士多德曾經斷言,文學比歷史更具有真實性,文學的這種真實性源於“一樁不可能發生而可能成為可信的事,比一樁可能發生而不能成為可信的事更可取”。但深思一層,對於歷史散文作者,歷史家和哲人的看法似乎都不全面。因為好的歷史散文既具備歷史事實的真實性,也具備文學藝術的真實性,二者不可偏廢。
《歷史的斑紋》以紮實的史料為依據貼近歷史。“名人故居或展館裡的書籍影像史料,以史實的質地袒呈,幀幀飽滿。”寫林則徐的晚年放逐,其《衙齋雜錄》《軟塵私札》中的記錄、與魏源等人的詩詞唱酬時常見諸行文。寫陳衍的詩家情懷,其《石遺室詩話》自然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在《烹飪教科書》這類看似與陳衍詩學貢獻毫無關聯的犄角旮旯,作者也能從中翻檢出詩人心緒中兒女情長、煙火之氣的淵源。寫林覺民的英勇就義,相較於家喻戶曉的《與妻書》,其《六國憲法論》《駁康有為物質救國論》等著述作者並未輕易放過,後者更能令人明白革命志士甘於拋妻別子行為背後的精神支柱之所在。可見,對書中所涉人物的著作、日記、奏章、書信等,作者均下過一番資料爬梳的功夫。本書滿足了歷史散文對真實性的嚴苛要求,凸顯了寫作者的誠心誠意。
作者善於以豐富的想象為橋樑觸控心靈。歷史散文不離史實,但絕不堆砌史實。如果說,史料記載的事實已然凝結成為某種知識,那麼散文書寫對這些知識的“理解”則離不開“想象”的津樑。康德曾言,想象力與知性之間的自由嬉戲才是審美愉悅的心理根源。哲人的話裡隱藏著開啟歷史散文寫作的一把鑰匙。這把鑰匙簡單說就是透過散文作者豐富的想象力,把知識性的史料還原到其曾經活生生存在過的時代語境中,在作者與所寫物件的共情共鳴之中,在跨越時空的心靈呼應之中,讓冰冷的史料再度獲得美的體溫。可以說,《歷史的斑紋》找到了這把鑰匙。龍潭精舍“畏廬”裡的林紓翻譯著《福爾摩斯》,馬限山頂的沈葆楨佇立凝望著閩江濁浪,流放途中的林則徐回憶起烏白雙塔、左營司巷、市橋燈火,冰心在南后街的“紫藤書屋”裡享受著文學滋養……作為寓居京華的福州人,作者對故鄉風物氣息的深刻記憶為他對歷史背影的想象式還原插上翅膀。其筆下,時間的鴻溝在心與心的觸控中撫平,逝去的往昔在想象的共鳴中重現。歷史由此融化進當下的現實,英靈的魂魄亦再度活色生香。
《歷史的斑紋》遣詞造句精心雕琢,運筆行文富於節奏,敘事描寫宛如眼前。作者眼中,林徽因是生命的一爐香,冰心是春天的一叢藤。孤寂的廬隱如鼓嶺的一團霧,睿智的嚴復似天地的一聲雷。“潮潤的江風,順著宮巷潛入沈府。院裡,爬過馬鞍牆的榕枝滑落幾聲鳥鳴,婉轉如古詩;陶缸中的芰荷,在午後的陽光裡,安然打盹……”鏡頭般的句子,烘托出沈葆楨在家閒居時的安逸、舒緩。“既是伴侶的耳語,亦是歷史的文身。一百年後的今天,面對熱血勇士向萬水千山說出的最燎烈的情話,我們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諦。”凝練精到的比喻,將《與妻書》中的溫情、決絕、惆悵、悲傷、英勇、無畏種種況味一網打盡,捨生取義亦柔腸百轉的林覺民躍然紙上。正是這些生花妙筆托起了書中史實的嚴謹與想象的自由。
(作者:楊光,系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