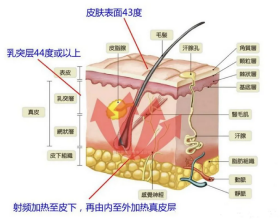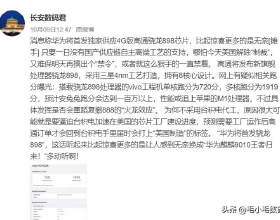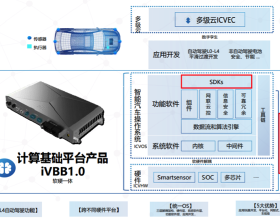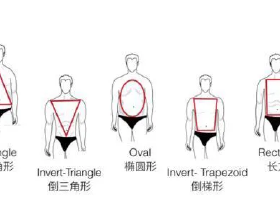編者按:今年是王荊公安石(西元1021-1086)誕辰一千周年。作為一代大儒名相,王荊公的成就實非一隅一項所能限定。以文章而論,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早有定評,且其詩詞亦足名家;以經術而言,其所撰《三經新義》(《周官義》《書義》《詩義》)熔鑄古今,貫通百家,義理豐美,故其人允稱大儒,其書亦列於學官;至以事功而言,其為一代名相,堪稱傑出的政治家,更為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昔清季清陸心源有云:“三代以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為儒,……自漢至宋,千有餘年,以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數人,荊國王文公一焉。”允為的論。惟近千年來,世事蒼茫,造化弄人,本屬蓋棺而定之人事,難脫譭譽參半之後名。又歷代論者,立場各異,甚或吠形吠聲,以本身當世之事牽涉其中,難得知人論世之實,常令人墮霧裡雲中。今值儒學重光,又逢荊公誕辰一千周年,宜有紀念。本刊同仁為表彰前賢,究明義理,特邀有關專家撰文組稿,成此“紀念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專輯,以饗讀者,更期方家玉音相和,不吝垂教。
為王安石辯誣
摘要:王安石變法伊始,即遭遇保守派士大夫強烈反對,這並不是因為變法已經出現嚴重後果, 而是基於理念、政見、立場之爭。這種立場先行的批判方式,削弱了保守派檢控的關於變法之弊的可信度。事實上,諸多針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指控,包括所謂的“青苗法”一味抑配、王安石“察謗議時政”“棄地五百里”之說,都是經不起查證的。今天我們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決不可只聽保守派一面之詞,而應當細心辨析史料,多方求證,以成公允之論。
關鍵詞:王安石 變法 青苗法 抑配 邏卒 宋遼劃界 辯誣

作者:吳鉤,1975 年生,廣東汕尾人,宋史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為宋代制度史與社會史。
北宋熙寧二年(1069),神宗皇帝拜翰林學士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君臣相得,厲行新法,史稱“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變法之一,也是最富爭議的一場大變法,時至今日,仍聚訟不斷。李華瑞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史》收錄有自南宋至當代的關於王安石變法的種種爭議,可參見。
王安石變法伊始,即遭遇保守派士大夫強烈反對——熙寧二年七月,第一項新政“均輸法”剛剛公佈,知諫院陳襄便上疏表示反對:“何必收輕重斂散歸之公上,與民爭錐刀之利,而失王政之體乎?”另一名諫官範純仁也再三奏請廢罷“均輸法”,因為“王者治民,惟在務農桑、禁遊惰,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自然公私有餘矣”。
其時,“均輸法”剛在東南推行,假設它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這個嚴重後果顯然還未產生,那麼保守派士大夫為什麼要堅決反對“均輸法”呢?“青苗法”“免役法”等其他新法的遭遇同樣如此:甫一推行,即引來強烈的抗議。可見保守派士大夫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是因為變法已經出現嚴重後果,而是基於理念、政見、立場之爭。
這種立場先行的批判方式,削弱了保守派檢控的關於變法之弊的可信度。事實上,諸多針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指控都是經不起查證的。比如保守派異口同聲、言之鑿鑿地聲稱“青苗法”存在嚴重的“抑配”問題,事實是不是如此呢?試看一個例子:熙寧三年(1070),河北緣邊安撫都監王光祖面奏神宗:“昨巡歷至廣信、安肅軍,聞散青苗錢官吏多不聽民自相團保,乃令上戶均保下等貧民,亦有直以一村約度人數自配給者,可更廣察訪施行。”神宗因此詔河北緣邊安撫司體量。安撫司調查後回奏:“二軍並取民情願在外結成保甲赴縣,未嘗抑勒,亦無以逐村計口支散者。”神宗又令王光祖“具析以聞”,即與河北緣邊安撫司進行書面質證。最終王光祖因奏對不實而受處分,神宗又下詔“特放罪”。
當時保守派對“青苗法”抑配問題的指控,多是這類不實傳言。檢讀熙寧二年至三年宋朝臣僚討論“青苗法”的奏疏,可以發現,保守派一面指稱官方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不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一面又譴責“青苗法”以利誘民,“小民匱乏,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然而,“一例抑配”與“不召而至”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農民積極請貸青苗錢,“不召而至”,官府為什麼還要搞強行攤派,“一例抑配”?
從“青苗法”的利率水平來看,也不大可能出現大面積的攤派行為。因為青苗錢年息二分,利率比民間貸款低得多(農民青睞青苗錢,原因即在此)。以上戶的經濟條件,也許不需要借貸,但他們如果借到青苗錢,也完全可以以更高一點的利息轉貸出去。
事實正是如此。按舊黨中人呂陶對“青苗法”弊病的揭發,青苗錢的支俵確已出現“詭名冒請”的問題。司馬光也指責官放青苗錢時,“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為什麼要“詭名冒請”“冒名詐請”?徽宗朝時有臣僚作出解釋:“訪聞形勢之家法不當給,而邇來諸路詭名冒請者亦眾,蓋欲復行稱貸,取過厚之息,以困貧弱。”形勢戶先詭名冒請青苗錢,然後轉貸給貧弱之戶,從中賺取利息差。“冒請”與“抑配”是兩種完全相反的行為,如果有人“冒請”,又何必“抑配”?
當然,並不是說宋政府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不存在攤派行為。區域性的攤派現象應該是有的,因為提舉官為追求政績,務要多支散青苗錢;而為便於日後收回本息,官方又傾向於將錢貸給有償還能力的上戶,上戶往往又不需要貸款,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出現抑配上戶的問題。但是,我們不必高估抑配的嚴重性,宋朝臺諫官指控青苗錢的俵散“不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無疑是誇大其詞的。
在立場明確傾向保守派的史家筆下,王安石還被塑造成容不得半點異議、熱衷於鉗制人言的大權相。南宋人呂中《大事記講義》載:“熙寧五年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罪之。此商鞅議令之罰,而安石亦為之。” 陳均《九朝編年備要》載:“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皇城卒七十人、開封府散從官數十人,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元人修《宋史》,沿襲這一說法:“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也收錄了類似的記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罪之。”不過李燾畢竟是史學大家,有著史家的審慎,特別註明“此據司馬光日記,系(熙寧)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見此,更詳考之。”顯然,所謂的王安石“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信源是司馬光,且缺乏旁證,所以李燾才註明“更詳考之”。
那麼司馬光的記載可信嗎?坦率地說,極不可信。因為熙寧五年(1072),司馬光已經遠離京城,隱居於洛陽,京城之事顯然是他道聽途說的。而熙寧年間,為抹黑王安石變法,反對變法計程車大夫捏造了許多謠言,朝野上下,流言滿天飛。
透過檢索史料,可以大致考證出所謂的“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究竟是怎麼回事。熙寧五年正月,由於有臣僚報告宰相王安石:“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並營房為不便,至雲今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或手持文書,似欲邀車駕陳訴者。”早朝時候,王安石便將此事提出來討論:
文彥博(時任樞密使)曰:“近日朝廷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並營事,亦合如此。此輩乃敢紛紛公肆詆譭,誠無忌憚。至言欲造反,恐須深察,又恐搖動士眾為患。”……上(神宗)欲得詆譭軍士主名,樞密院謂責殿前、馬、步三帥,安石請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開封府。
討論的結果,神宗決定查出煽動造反的主謀姓名。樞密院提議由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三帥負責調查,王安石則提請委皇城司。神宗說:“不如付之開封府。”最終神宗決定由皇城司派邏卒暗中刺探兵營動向,開封府則負責審訊。
時過未久,中樞又對“邏卒探事”提出了異議:
馮京(時任參知政事)言:“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頗不安。”上曰:“人數止如舊,探事亦不多,藍元震(內侍,時任皇城使)又小心,緣都不敢乞取,故諸司不安。”僉曰:“外間以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決杖,故多捃摭細碎。”上曰:“初無此處分。此輩本令專探軍中事,若軍中事但嚴告捕之法,亦可以防變。”安石曰:“專令探軍中事即無妨,若恃此輩伺察外事,恐不免作過。孫權、曹操用法至嚴,動輒誅殺,然用趙逵、呂壹之徒,皆能作奸亂政。陛下寬仁,不忍誅罰,焉能保此輩不作奸?三代聖王且不論,如漢高祖、唐太宗已不肯為孫權、曹操所為,但明示好惡賞罰,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誕謾,天下事安有蔽匿不聞者?細碎事縱不聞,何損於治體?欲聞細碎事,卻致此輩作奸,即所損治體不細。”上以為然。
可見王安石是明確反對特務政治的,他不可能為堵住別人的嘴而指使邏卒伺察官民。
從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贊成鉗制人言,那是熙寧六年(1073),樞密副使吳充給神宗提交了一個議案:
朝廷開廣言路,微至於庶人皂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誼也。而比來士大夫輒以書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排詆營救,增飾事情,嫌愛在心,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慾。雖朝廷必加稽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詆者既難於反坐,營救者又陰以為德,含沙射人,束縕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託公誼以售私恩,此風浸成,實黯聖政。乞有司申嚴法禁,庶懲薄俗。
吳充的意思是,為避免有人“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慾”,朝廷應該立法嚴禁士庶投書高官。神宗採納了吳充之議,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立條制”。但王安石告訴神宗,沒有必要設立限制言路的法禁:“堯、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誕謾,自不須多立法禁。”這便是王安石對人言的態度。
綜上所述,可以總結:熙寧五年初,皇城司確實派出邏卒“探事”,但指揮皇城司的人肯定是神宗皇帝,而不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邏卒的數目也不可能是“七千餘人”,因為熙寧五年皇城司的整個編制也才三千多人,“七千餘人”當為“七十餘人”之訛;而且,這些邏卒的“探事”範圍也作了限制:“專探軍中事”,以防有將士密謀不軌,並不是“伺察外事”“捃摭細碎”。
可是,別有用心者卻謠稱是王安石為鉗制人口,“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道”,“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云云。這類流言從京城傳到洛陽,司馬光聽信了記入日記:“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罪之。”而且在奏疏中將鍋直接扣到王安石頭上。熙寧七年(1074)四月,因神宗下詔求言,司馬光終於忍不住,上疏攻擊王安石及其新法,疏中說:“(王安石)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由於保守派熱衷於造謠傳謠,司馬光道聽途說又信以為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訛傳訛,王安石便背上了鉗制人言的大黑鍋。令人遺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聽信司馬光一面之詞,不作考證,認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邏卒伺察於市井間,發現哪個人訕謗新法,立即抓起來治罪。卻不想想:宋朝的皇城司直隸於內廷與樞密院,非中書所能指揮,況且時任樞密使的文彥博一貫反對王安石,怎麼可能協助王安石監聽市井謗議?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負,又怎麼會浪費心力去理會市井間的議論?
在反對王安石變法、追隨保守派的宋朝文人筆下,王安石還揹負割地給予契丹的黑鍋。且來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的記述: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時王荊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雲。韓公承荊公風旨,視劉公(劉忱)、呂公(呂大忠)有愧也,議者為朝廷惜之。嗚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荊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使帝忽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數哉!
邵伯溫所記的“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一事,發生在熙寧七年二三月。在蕭禧抵達東京之前,神宗曾問王安石:“契丹若堅要兩屬地,奈何?”王安石說:“若如此,即不可許。”神宗又問:“不已,奈何?”若契丹不罷休,又如何是好?王安石說:“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與之辯而已。”
這是《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顯然,王安石並不同意對遼國割地求和。隨後,神宗派太常少卿劉忱、秘書丞呂大忠等人前往河東路,與遼方談判代表蕭素、梁穎會於境上,商量劃界。但因為雙方各不相讓,談判陷入僵局中。而在宋遼談判期間,王安石亦罷相歸江寧故里。
次年春夏,王安石復相。神宗又與他商討同契丹劃界之事。王安石說:“我不可示彼以憚事之形,示以憚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神宗說:“彼必不肯已則如何?”王安石說:“譬如強盜在門,若不顧惜家貲,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
從君臣的對話不難看出:王安石反對割地予契丹。他對宋遼劃界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兩點:一,不可向遼國示弱,要據理力爭,料契丹不敢舉兵;二,就算契丹舉兵,也不用怕它。
宋神宗儘管表示“如此則不須畏”,但內心還是有些憂懼,所以又派中使帶著手詔去拜訪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四位老臣,請他們出出主意。
富弼、文彥博與曾公亮都反對割地,韓琦卻建議厚撫契丹,割讓爭議地塊:
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為諜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佔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約,兩絕嫌疑。
對韓琦的看法,王安石極不以為然,直說:“琦再經大變(指擁立英宗、神宗繼位),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啟寵納侮’。”
不過宋神宗對劃界的態度似乎更接近韓琦。熙寧八年(1075)四月,神宗皇帝給代表朝廷與遼國談判劃界的韓縝下詔,對部分地段的劃界作了讓步。要說割地給予契丹,那也是出自神宗本人的“聖裁”。對於割地,神宗大約有幾分慚愧,跟王安石解釋說:“度未能爭,雖更非理,亦未免應副。”王安石說:“誠以力未能爭,尤難每事應副,國不競亦陵故也。若長彼謀臣猛將之氣,則中國將有不可忍之事矣。”對朝廷這次示弱的可能後果很是憂慮。
宋朝與遼國的劃界,一直到熙寧末年才算結束,劃界的結果是宋朝大約放棄了數十里的領地。但到了輕薄文人的筆下,宋朝的讓步被誇大成“棄地五百里”“棄地七百里”,王安石更是被誣為主張割地求和的“賣國賊”。
事實卻是:熙寧七年劉忱在河東與遼方談判劃界時,王安石已經罷相居江寧;熙寧八年至十年,韓縝與遼方的劃界談判,則直接由神宗指揮,期間王安石雖已復相,卻長時間以疾居家,未理朝政,不久(熙寧九年十月)便又罷相;而在朝之日,王安石每次與神宗論及劃界之事,都是提醒、勉勵神宗不可向遼國示弱。他怎麼可能主張割地予契丹?
在宋遼劃界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保守派文人的顛倒黑白:韓琦分明提議向遼國“退近者侵佔之地”,在邵伯溫筆下,卻搖身變成反對棄地的諍士、智者;王安石明明白白跟神宗說過不可割地,卻被邵氏誣為將祖宗故地“輕以畀鄰國”。
邵伯溫記述的王安石“棄地五百里”謠言,源頭出在蘇轍身上。元符年間,蘇轍在回憶錄中說:
予從張安道(張方平)判南都,聞契丹遣泛使求河東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謂:“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揮邊吏分畫。”使者大喜,出告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之辯,卒莫能得。予聞之。
蘇轍在編造王安石於熙寧劃界之時力主棄地的謠言時,用了兩個詞:“聞”“予聞之”。這一細節表明,蘇轍的記述乃是來自道聽途說。當時,應該確有傳言聲稱王安石講過“咫尺地不足惜,後取之不難”之類的話。
那麼王安石講過嗎?講過。那是熙寧五年九月,在一次御前會議中,王安石說:“朝廷若有遠謀,即契丹佔卻雄州,亦未須爭,要我終有以勝之而已。”但是,王安石講這話的背景是:朝廷正用兵於河湟,而知雄州張利一卻在宋遼邊境生事,引契丹巡馬過河。樞密使文彥博揚言與遼國“交兵何妨”。王安石不欲與契丹爭細故,影響收復河湟之大業,因而才用過頭話反駁文彥博。實際上,當時宋遼之間並沒有發生領土糾紛。等到熙寧七年二月,傳遼使蕭禧前來索地,王安石便明確跟神宗說:“若如此,即不可許。”
蘇轍卻將王安石熙寧五年講的話掐頭去尾,改頭換面,刪掉背景,然後裝入熙寧七年“契丹遣泛使求河東界上地”的事件中,之後邵伯溫之徒又添油加醋,終於讓王安石背上了棄地數百里的黑鍋。
為建構廢除新法、恢復舊法的合法性,保守派士大夫還虛構了神宗皇帝幡然悔悟、與王安石分道揚鑣的敘事。呂本中《雜說》這麼記載:
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安石對所厚嘆曰:“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安石嘗進呈陳襄除龍圖閣直學士,呂嘉問集賢院學士、河北路都轉運使。上曰:“陳襄甚好,嘉問更候少時。”居半月,再以前議,上回頭久之,卻顧安石曰:“聞相公欲去多時。”安石倉皇對曰:“欲去久矣,陛下堅留,所以不敢遂去。”既下殿,即還家乞去。其婿吳安持往見之,安石問:“今日有何新事?”安持曰:“適聞有旨,未得閉汴口。”安石曰:“是欲我去也。”數日遂罷。王安石既去,嘉問因對,上問:“曾得安石書否?”嘉問因言:“近亦得安石書,聞陛下不許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計。”上曰:“是則為呂惠卿所賣,有何面目復見朕耶?”
這個故事說得有鼻子有眼睛,可惜卻是保守派支持者編造出來的。事實上,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多次請辭,神宗都不同意。二月初七,因王安石固辭機務,神宗還詔管勾東府使臣“不得令王安石家屬行李出府”。
六月初,神宗御批停罷發行“折二錢”(一枚銅錢當兩文行用的大錢),王安石不同意,屢爭,甚至發了脾氣:“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朝後即稱疾不出。神宗派人傳諭勸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鑑,何遽如此?”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的原因其實沒那麼複雜,不必扯到君相勾心鬥角的“陰謀論”。最主要的原故如其罷相制書所言:“俄屬伯魚之逝,遽興王導之悲。”這兩則典故說的是喪子之痛。熙寧九年六月,愛子王雱突然去世,讓王安石受到沉重打擊,再無心思過問政事。
王雱是王安石一直引以為傲的王家長子,自幼聰慧,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十三歲時,他聽秦州士卒談熙河的蕃部,立即發表意見:“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拓邊的戰略,與此如出一轍。二十二歲中進士,官授旌德縣尉,不赴。三十歲前,已完成《老子訓傳》《莊子注》《佛經義解》《南華真經新傳》《孟子解》《詩經新義》《尚書新義》等學術著作,可謂對釋、道、儒三家學說都有深入的研究。他還寫了數十篇縱論時事的策論,軍器監之設,即是他所首倡。他又工於詩詞,傳世的詞作儘管不多,卻寫得清婉宜人,不輸北宋第一流的詞人。
王安石對王雱的期待也很高。相傳王安石曾與女婿蔡卞聊天,說起親族中的年輕才俊:“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說著,扳著手指計算:“獨兒子也。”即指王雱。在王安石心目中,王雱是可以當宰相的人才。《宋史》稱王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他確實有資格這麼驕傲。如此人物卻英年早逝,可謂天妒英才。
王安石對王雱之死還心懷深深的自責。這得從王安石與參知政事呂惠卿失和一事說起。呂惠卿本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熙寧八年,呂惠卿卻與王安石鬧翻,並離開朝廷。隨後,御史中丞鄧綰彈劾呂惠卿諸兄弟曾經勾結地方貪官,在華亭縣強借富民錢購田放租,以權謀私。神宗於是派人成立一個推勘院,根究此事。
熙寧九年,在推勘院推鞫本案時,絕頂聰明的王雱竟然做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原來王雱對呂惠卿恨之入骨,為坐實呂惠卿的罪名,切責親信練亨甫、呂嘉問二人趕緊想法子。練亨甫、呂嘉問想出了一個餿主意:“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即把鄧綰對呂惠卿的彈劾狀當成中書的正式檔案下發推勘院,指導辦案。呂嘉問時任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練亨甫是中書戶房習學公事,要在中書下發推勘院的公文內挾帶點私貨,那還不容易?
但中書有一個堂吏,是呂惠卿的親信,發現了呂嘉問的小動作,急忙給呂惠卿報信。呂惠卿的心涼透了,以為是王安石欲置他於死地,於是憤然上奏,前後凡數十紙,在自辯的同時,也奮力詆譭王安石。
神宗將呂惠卿的奏狀出示給王安石看。王安石愕然,說,中書不可能這麼做。回家問兒子王雱,王雱說了實情,王安石大怒,將兒子痛責了一頓。只是這時候,王雱已經病重,受了父親的責罵,更是“忿恚增劇”,病情加重。過了十幾天,六月廿五日,王雱便病逝了,年才三十三歲。
兒子的荒唐做法,讓父親王安石深感慚愧;而王雱帶著羞憤離世,又讓王安石悔恨、自責。兒子病逝後,王安石心如死灰,執意辭位,神宗還是遲遲沒有同意,直至十月底,才批准了辭呈。
王安石這次罷相後,回到江寧,終老於鐘山之下。保守派士大夫稱神宗“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以說明王安石已經被神宗遺棄。但實際上,元豐三年與六年,為大禮之年,朝廷舉行南郊祭天大典,天子親郊,神宗都召王安石回京,在郊祀時陪位。只是王安石自己心灰意懶,決不肯復出,兩次託病謝絕了神宗之召。
縱觀北宋元祐以降保守派士大夫(及其追隨者)對王安石與熙寧變法的敘事,不實之處甚多。出於反對變法之立場,他們不僅誇大了新法的弊端,甚至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抹黑王安石。尤其是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誠如有識之士所指出:“《邵氏聞見錄》凡涉熙寧變法處,幾近謗書。”今天我們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不論觀點為何,首先決不可只聽保守派一面之詞,而應當細心辨析史料,多方求證,以成公允之論。
來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註釋從略,引用時請核查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