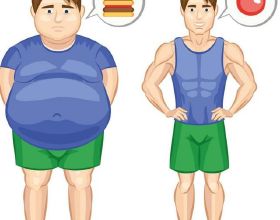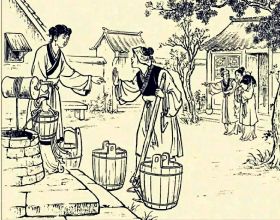王大鵬
通常來說,我們說某個人不說“人話”帶有某種侮辱的意思,但是在科普這個問題上,“說人話”可能是科普人員需要掌握的一種技能。當然這裡的“說人話”意指說普通公眾能理解的話,或者說就是要用大家耳熟能詳的詞語來解釋一些複雜的科學道理。畢竟科研人員經過“十年苦修”而習得的對科學本質的理解不太可能期望普通人能夠“一夕頓悟”。那麼這就需要我們採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從受眾的視角去思考和看待問題;不過也有人並不認同這一點,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隻滿足了某些特定的受眾,也就是具有很多“前置知識”的受眾,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也許某些消費科學內容的人本身就是對科學感興趣的人呢。而如果我們想獲得更多的受眾,或者說讓更多的人理解科學,那麼“說人話”依然是必須的。
在談到科學家與媒體關係的很多文獻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記者會抱怨說科研人員不“說人話”,不會講故事。實際上,他們這裡談到的是受訪人員無法將專業術語進行轉化,這會使得訪談人員和受眾“如墜雲霧”,繼而不得要領,我們也喪失掉了一次開展科普的機會。
當然,我們這並不是說術語不好,而是說術語應該用在適當的場合,比如學術交流過程中。這就好比足球運動員與球鞋的關係,不是說他們不能穿球鞋,而是說最好不要在室內穿球鞋,球鞋最適合的場所是球場上的草坪。術語在學術交流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節省了人們溝通交流的時間,另外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共同體的集體認知。“隔行如隔山”,如果你不是某個領域的專業人士,那麼你可能真就不明白某些術語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是,當我們從學術交流撰寫大眾傳播的時候,就需要警惕對專業術語的使用。實際上,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知識的詛咒”。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一個專有名詞-Robust,中文翻譯成“魯棒性”,根據《牛津詞典》中的解釋,在科學中使用“Robust”時所採用的含義是一個系統或組織有抵禦或克服不利條件的能力。但是在翻譯成中文時,我們一時難以搞清楚它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專業領域的研究人員可能一下子也完全不知道它說的是什麼。
那麼話說回來,如果我們在向公眾進行科普的過程中用到了“魯棒性”這個詞,但是又沒有解釋它的意思,我們又怎麼能期望受眾能夠理解這其中的含義呢?
這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其他的還有“視界”、“坍縮”、“量子糾纏”、“熵”等等。當然,在科普的過程中需要把握一個核心原則,那就是科學性,否則就會走向“有普沒科”的極端。但是我們依然需要考慮的是,科學家或者科普人員所強調的科學性與公眾視野下的科學性是不是一個意思,二者的內涵和外延有多少重合度,又存在多大的差異。
同時進行術語轉化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科研人員要對這個術語有著透徹的理解,也就是說欲讓比人明白,需要自己先明白。正如盧瑟福說的那樣,“如果你不能跟實驗室擦地板的女工解釋清楚你是做什麼的,那這就說明你實際上並不知道自己是做什麼的。”
斯蒂芬˙傑˙古爾德在《乾草堆中的恐龍》中說,“我將科普文寫作分為兩個類別:第一種為伽利略模式,主要是關於自然謎題的知識性文章;第二種則為聖方濟各模式,主要是關於描寫自然之美的抒情散文。”同時,他又在《奇妙的生命》中認為,“我在每一次撰寫所謂‘普及讀物’時,都極力維護一條個人原則。(“普及”一詞的字面義令人嚮往,但現已被貶損,帶有簡化或添油加醋的意味,好像這樣的讀物應該如同輕音樂,讀起來無須費神。)我相信——就像伽利略完成他那兩部鉅著,是以義大利語對話的形式,而不是用拉丁文寫就的說教綱要;就像托馬斯˙亨利˙赫胥黎寫出他那高超的文章,不用一條術語;就像達爾文出版他所有的書籍,都是面向大眾讀者——我們仍然可以有這樣一類科學讀物,既適合專業人士閱讀,也能讓感興趣的非專業人士讀懂。儘管科學的概念數量豐富,意義多樣,但不必有所妥協,不必經過扭曲的簡化,也能以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讀者可以理解的語言表達出來。當然,較之學術出版物,面向一般讀者的讀物在遣詞造句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但只限於將令行外人士感到迷惑的術語和措辭去掉,而概念的深度絕對不可有所不同。”
從上述這兩段古爾德關於科普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也在倡導“去術語化”或者對術語進行轉化,其目的無外乎讓公眾更好地理解科學。
所以,好的科普要儘量“去術語化”,要儘量“說人話”。
(作者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
來源: 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