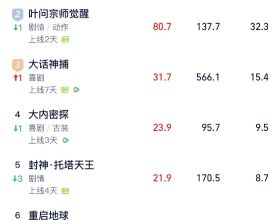近期,隨著孫寶寶的到來,家裡的事情太多太忙,屈指一算我也是有些日子沒回老家了,趁著月嫂還沒下單,兒子沒上班,我也回家看看老的和小的。
我說這城鄉差別不僅僅體現在衣食住行上,就連天氣的差別也是比較大的,在慈利似乎還沒感覺到很冷,而老家的冬,雪花已經在輕揚,等我從車上下來,那白白細細的雪花像是在迎接遠方歸來的遊子,一哈向我襲來,就在我頭上、臉上、身上、甚至腳背上親個不停,那一朵朵一點點硬是親化了它自己才甘心,有調皮點的竟然從我脖子的縫隙鑽進懷裡,是想貼近那顆滾燙的心吧,它們便是放肆地盡了興,凍的我卻直打哆嗦,上齒敲下齒。
“家”的下面是“豕”,“豕”就是“豬”,意思有豬才是家。大學士曾國藩八字家訓也講到了豬。於是農村家家戶戶都得養豬,才像個家的樣子,而每年冬至節便開始陸陸續續宰節豬,又叫殺年豬,寒冬將至,年亦將近,算是對一年的辛勞表示獎勵和犒勞。殺年豬是有講究的,逢亥、逢六的日子,逢破日、閉日都不宜殺年豬,意思來年養豬不順頭。逢馬、逢牛、逢虎則是殺年豬的吉祥日子,寓意來年養豬牛高馬大。冬至這天79歲的老母也請屠夫來家宰節豬,按常規,我知道她肯定是先天晚上就不給豬餵食了,空了一夜的肚子,第二天屠夫才好翻腸子,豬倒生以後,母親還會拿來一撮紙一柱香燒在豬圈門口。你想都想不到,老人家早晚伺候餵養了一整年的大白豬,竟然殺了三百多斤肉,平均每天估到一斤肉,還有幾十斤豬油,來年一家三口是不缺肉吃,不缺油吃了。屠夫會把肉砍成十來斤一小塊塊的,有說法叫七方八肘,意思一塊正身肉一般七斤左右,一塊圓膀肉(帶腿的屁股墩子)則八斤上下。父親再用鹽在大水缸裡醃製幾天,等血水全部出來,肉裡面全部進鹽以後,便一塊一塊繫上棕葉繩掛在炕架上。炕肉時還有禁忌的哦,炕肉的人只管加油往炕架上掛肉,卻不得出聲,不然被老鼠聽到了,怕它會爬上炕架偷肉吃。炕架下面火坑裡的火燒起來也是有講究的,一個是日夜不斷火,不要冷一把熱一把;二個是要燒明火炕,不需要太多的煙子燻;三個是掛肉的位置要不高不低,過高怕肉炕臭了,過低怕皮焦肉沒好。這樣子差不多炕到臘月中下旬的時候,肉便外黃內透,皮不黑肉不稀,切起來平整,炒起來鬆散,吃起來香酥不油膩。
老家殺年豬還有一個習俗,就是把親鄰四舍接來吃殺豬飯,喝豬血湯,以示喜慶、熱鬧、親和。母親宰節豬也跟往年一樣接了族親鄰里,可是她老人家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一年不如一年,加上前不久生了一場大病,身體剛剛恢復好點,請客做飯的事該是困擾著她,該是想我回家的,又看我正忙著,心疼女兒的她絕對不會叫我回家幫忙的。這不,怎麼說母女連心呢?當她看到沒打電話就回家了的我,借心花怒放、喜形於色等等這些詞都不及於表達和描繪她老人家的心境。我還只在門外喊一聲:“媽媽”。正在烤火的她回過頭來笑開了花,驚訝地問道:“玉岸哦,你今天怎麼有空回來了的”?我說:“專門抽空回來看你”。“冷哦,快烤火,強純(我爸爸)加點炭”。她自己則拿個裝零食的盆去房間取來幾樣小吃,叫我先吃點,等會才有飯吃,她說接了我么么嬸嬸,還有我堂兄堂弟,堂姐堂姐夫他們吃飯。我忙說:“哦,那好啊,正好我可以幫你炒菜”。她的每一個神態與動作都讓我感受到她內心的欣慰與喜悅,母親選了一個最大最紅的碰柑遞給我,然後斯斯文文地笑著告訴我,冬至殺豬那天喊了幾個人吃飯的,沒喊齊,你爸爸糊里糊塗炒的菜,今天干的強你回來了,她說這些人平常都對我們很好,很照顧我們,病了也來看我,殺豬了有菜要給他們做點飯吃……她還在唸叨著,我吃完碰柑便去櫃子裡找來她的舊棉衣,換上趕緊進廚房。菜都準備好了,除了肥肉、素肉、豬血、雞蛋就是自己菜園種的各樣小菜和醃菜,還特意買了白豆腐,豆腐對於鄉里人那是極品佳餚,請客必備的食材之一。
媽媽坐到灶門口一面燒火一面跟我說著話,說你現在不比以前了,叫我一定要耐煩一些,人到世上就是門些事……也只嗯、嗯的應著她,並告訴她孫寶寶長的好呢,你也命好都四代同堂了,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父親則忙著各家請客,給我打哈下手擺碗筷、酒杯、爐灶、燉缽。不到兩個小時,向來毛手毛腳的我洗、切、煮、炒、燉、擺。一桌“豐盛”的老家風味的家常菜躍然呈現。跟往常一樣,我首先給弟弟盛飯夾好菜送到他手上,客人們吃完飯喝完酒,坐到火邊張家長李家短熱熱鬧鬧說著散白話,天黑之際便都各自回家了,母親還特地給每家客人都送一些她自己樹上摘下來的柚子。
不難感覺二老這一天的欣喜與幸福,許是年紀大些了的緣故,其實,我何嘗不想多給他們一些這樣的時光,這樣的時光又是何其的寶貴,寶貴到生怕有了這次,就沒了下次,呸、呸、呸,又自我心裡責備起來。唉,也難怪我會這麼想,天黑了,一家人圍著火坑烤火,高興了一天的父親突然嘆了口氣,然後語重心長又懇切地對我老公說:“潤初,你看哪裡有價格合適的棺材給羅弟兒買一副,要三底四牆五蓋,要全杉木的,好些,到土裡不容易爛”。還交待他自己百年長壽後就到墳山坡上找個地方,那裡是羅家的祖陰之地,只要不是見兇,不是少年王都可以葬,突然聽到這話,我心裡一涼,連著打了幾個寒顫,看著他的臉說不著急吧,不說這話,他還只四十多歲呢!父親的表情卻異常嚴肅古板,皺著眉抖了抖手指頭的菸灰接著說:“你是找不到,這段時間家裡出了些事,趁我和你娘還在,給他安頓好了,我們哪天眼睛一閉也才得放心,豬圈那麼寬,明年我們扳蠻喂的一頭豬,有地方放,買來了我找么么一刷漆,幹了再用蚊帳布蓋起來,年長日久又不會壞的。”我無語,只默默地看著他,硬是看透了那顆酸楚的心,流血的心,父母心。停了會他扔下菸頭,擦了擦鼻子底下,我聽到他的鼻子發出粗魯的吸氣聲,接著又說:“這回差點就把我們的低保搞掉噠,那次開會60個黨員代表,有59票同意我們家,兩個月後又開會宣佈我們低保取消了,羅弟兒就到網上發了一封求助信,第二天來了七八個幹部到家裡調查,說情況有誤,第三天通知我低保補上去了。”我說還有這事?怎沒聽你說起?我看到他交叉的雙手輕微地顫抖著。旁邊的母親用火鉗撿了撿燒餘的柴火頭,輕輕的說:“你一打電話叫我們莫多做,生活搞好點,現在社會好,我們不做不行啊,爸爸那天就打算告訴你的,一想,告訴你也沒用,只會煩惱你,也就沒說了,一個人就睡到床上說胡話,這怎麼辦呢?我找哪個踢呢?丫頭還有月月讀書,又要帶孫兒,一個人撈錢怎麼搞的贏?還要管我們,直到村幹部通知他低保補上去了,你爸爸才睡著瞌睡。”看著父親和母親,我依舊不想說話,僵硬的喉嚨也說不出話來,心裡那個痠痛哦,一陣一陣地絞著……一旁的老公就一直寬慰著他們……直到說起月月的成績有了進步,她好懂事的,每學期老師都鼓勵她評了三好學生或者優秀班幹部,二老沉重的臉上便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兩尺的距離我看的很清楚,父親是那般的耿直敦厚,母親是那般的溫善柔弱,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那般的慈祥,那般的純樸、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