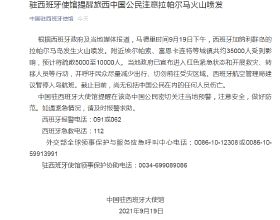虔誠信佛的“石三伢子”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學習毛主席》的報告,報告中說:
毛主席常說,他是從農村中生長出來的孩子,開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後的。他最不同意晉察冀一個課本描寫他在十歲的時候就反對迷信,說他從小就不信神。他說恰恰相反,他在小時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厲害。當他媽媽生病的時候,他去求神拜佛。
周恩來的這段話說明,毛主席在小時候是信佛的。
佛教由印度傳入東土,與生於斯長於斯的儒道兩家完全不同。但是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佛教傳入中國後,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佛教思想與儒家道家等本土文化不斷地撞擊、融合和發展,早已成為有著重大影響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一。
佛家與儒家的互補、互用趨勢,中國禪宗的出現就是最好的例證;而北宋“理學”的出現,則標誌著儒、釋、道三家融合的完成。所以,不懂佛學,就很難讀懂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學史。佛學已成為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國學中最具獨特色彩的一個門類。這也是近現代所有國學大師們所公認的。
幼年毛澤東的信佛,是由於深受虔誠信佛的母親的薰陶感染。1936年,毛主席對美國記者斯諾說:
我父親毛順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親信佛卻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
毛主席的母親文七妹對佛教產生信仰的時間,至少可以追溯到1893年毛主席誕生之際。在毛主席出生前,文氏曾先後懷過兩胎,但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
毛主席誕生之後,文氏除了高興之外,還千方百計地要使他“長命百歲”。為此,文七妹先後採取了四項措施:其一,是讓毛澤東拜七舅媽為“乾孃”。其二,是替兒子向南嶽觀音菩薩“許願”,答應毛澤東長大成人之後去“還願”。其三,是讓毛澤東拜“石觀音”為“乾孃”。其四,是自己吃“觀音齋”。
毛主席的七舅媽子女頗多,而且個頭長得健壯結實。母親要毛主席拜七舅媽為乾孃,是希望託七舅媽的福,庇廕他健康成長。在上述四項措施中,除這一項屬於民間風俗之外,其他三項都與佛教有關,而且都是與觀音信仰有關。
毛主席的母親雖然向南嶽的觀音菩薩“許願”,求其保佑自己的兒子平安,可是她還是覺得南嶽的觀音菩薩離她太遠了點。因此,她又在孃家附近找了一座“石觀音”,要毛澤東拜它為“乾孃”。文七妹領著年幼的毛澤東拜石觀音做“乾孃”時,還向石觀音表示,從此這個小孩就寄名石頭,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就叫他“石三”。於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在親友中喊開了。
毛澤東童年時從兩歲至八歲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過的。他的外祖母也虔誠信佛。每逢觀音菩薩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他都少不了由母親或舅父、舅母領著,去向石觀音禮拜。所以“石三”的乳名和石觀音的形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因革命鬥爭環境的險惡,毛主席還曾用“石山”的化名發表文章或通訊。這個“石山”顯然就是從“石三”衍化而來的。例如1923年7月1日,毛主席在《前鋒》雜誌上發表《省憲下之湖南》一文時,署名便是“石山”。同年9月28日,毛主席在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附語中特別交待:
此信託人帶漢寄上,因檢查極厲害,來信請寫交毛石山,莫寫毛澤東。
1951年5月,毛主席在接見他的表兄文運昌等人時,曾談到拜石頭為乾孃的事。他說:“我小時候有個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時候,我母親信迷信,請人算八字,說我八字大,不拜個乾孃難保平安。母親帶我去唐家圫外婆家,發現路上有一塊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頭為乾孃。因此,母親又給我取名‘石三伢子’。”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了他闊別32年的故鄉韶山。6月26日傍晚,毛主席在韶山招待所設了幾桌便宴,款待他少年時代的師長和親友,以及當年曾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赤衛隊員、老共產黨員和烈士家屬。
當賓主各就其位之後,工作人員輕聲告訴毛主席:“主席,客人都來齊了,可以開始了。”
毛主席站了起來,舉杯環視四周,微微笑道:“今天,各位父老鄉親都到齊了,就只差我乾孃冒[沒]來呢。”
頓了頓,他用商量的口氣說:“是不是還等呢?”
鄉親們聽毛主席這麼一說,都感到很詫異。他們知道主席有個乾孃是七舅媽趙氏,已去世30多年了,這是主席自己也知道的。怎麼現在又冒出個乾孃呢?
毛主席見鄉親們迷惑不解的樣子,也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只是爽朗地笑道:“大家喝吧,我們不等啦。”
席間,有幾個年輕人仍想打聽個究竟,便指使一個小姑娘去問毛主席:“主席爺爺,您的乾孃是哪一個呀?”
毛主席放下杯筷,笑容可掬地抱起小姑娘,大手向西一指說:“我是那個山圫裡石頭的孩子,你又是哪個的孩子呀?”
原來毛主席講的就是“石觀音”。他拜石觀音為乾孃,是幼年時代在外婆家生活時的事,即使是當時在座的五六十歲的韶山老人亦不知情。所以當毛主席重提此事時,大家都感到詫異。
在虔誠信佛的母親的影響下,少年毛主席對佛教的信仰也十分真誠。他不僅和母親一樣,對父親不信佛感到傷心,而且曾和母親討論,如何改變父親不信佛的態度。1936年,毛主席向斯諾回憶說:
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他只是罵我們,在他進攻之下,我們只好退讓,另想辦法。但他總是不願意和神佛打交道。
……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賬,路上遇到一隻老虎。老虎猝然遇見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親卻感到更加吃驚,對於他這次脫險的奇蹟,他後來想得很多。他開始覺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從此,他開始比較敬佛,有時也燒些香。然而……他只有處境不順當的時候,才求神拜佛。
資料表明,1909年,即毛澤東16歲時,他曾去南嶽“朝山進香”。這次“進香”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毛主席的母親生病時許了願,治好之後去“還願”。1957年,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也是如此說的。但根據毛主席童年與佛教的關係,在毛主席幼年時代,文七妹曾向南嶽的觀音菩薩“許願”,祈求保佑兒子健康成長等來看,這次“進香”可能有著雙重任務:既替母親“還願”,也替自己“還願”。
研經訪僧究佛理
少年毛澤東對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誠的。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知識的增多,善於獨立思考的他對佛教信仰的懷疑也隨之增長了。延安時毛主席在和斯諾的談話中說過:
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了影響,我自己也越來越懷疑了。我母親開始為我擔憂,責備我不熱心拜佛,可是我父親卻不置可否。……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有影響,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學來了一個“激進派”教師。說他是“激進派”,是因為他反對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勸人把廟宇改成學堂。大家對他議論紛紛。我欽佩他,贊成他的主張。
毛主席所說的“激進派”教師指李漱清。李漱清畢業於湘潭師範學堂和地方自治法政專門學校,曾在湘潭縣西二區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執教多年。由於受維新思想影響較早,所以他常在鄉間給人們講述各地見聞,勸人們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對封建禮教。他主張廢除廟宇,用廟產興辦學堂,以提高農民子弟的文化科學知識。李漱清的這些主張被一些思想落後的人們視為激進,因此得了個“激進派”的“頭銜”。
1917年8月23日,風華正茂的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認為釋迦牟尼,是老百姓自己將其神化起來的。
毛澤東還從個性解放的立場出發,認為“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此時毛主席將教會一類的宗教組織與國家之類的法定權力機構等同起來,把它們都視為束縛人的個性發展的一種組織形式。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這時對宗教,包括佛教的理論已經失去了興趣。恰恰相反,由於毛主席從青年時代起,即養成了對哲學的濃厚興趣,在一師讀書時期,他不僅比較系統地研究過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而且對佛教哲學亦有所研究。直到1920年6月,即毛澤東的世界觀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前夕,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還表示要研究佛學。他說:
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一難得書,二不得空時,懈怠因循,只好說“今日不學又有明日”罷了。希望先生遇有關於言語文字學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多餘的印刷物,並請賜寄。收聚了書,總要劃一個時間,從事於此。
在長沙讀書期間,毛主席不僅研讀過佛經,而且到一些寺院中去遊歷考察,與高僧交談,親身體驗佛教文化。
據毛主席一師時的好友蕭子升在書中回憶:
1917年暑假期間,毛澤東和蕭子升從長沙出發,到好幾個縣的農村裡“遊學”。行至寧鄉縣溈山密印寺時,他們特意拜訪了老方丈,翻閱了寺中藏的各種佛經,向方丈請教一些佛法問題。方丈定要留他們在寺裡盤桓幾日,並告訴他們,那些掛單和尚,雲遊四方,談經論道,對弘揚佛法很有好處。
毛澤東和蕭子升在這座寺廟裡住了兩天,由和尚引導著在各處參觀,瞭解了寺院的組織和僧人的生活。他們還向方丈詢問了全國佛教的概況,以及佛經出版的情況。還了解到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經籍出版的中心。像溈山寺這樣的講經中心,全國至少有100處,如果算上規模較小的,大約有千處左右。
告別的時候,毛澤東和蕭子升表示,還想訪問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寫幾封介紹信。方丈說:那是不必的,你們不需要任何介紹信,因為無論走到哪個廟裡,你們都會受到像在這裡同樣的歡迎。
從溈山下來,他們就向安化縣走去。路上在茶館歇腳,準備寫日記時,兩人又議論起佛教與人生哲學問題,以及歷代帝王同宗教的關係。認為唐代最具典型:皇帝尊孔子為“王”,從此全國各州府縣一律修建孔廟;皇帝姓李,又尊老子為道教始祖,開始建立道觀;外來佛教也受到歡迎,於是寺院遍及全國。儒、釋、道都為官方所尊,和諧共處。到印度取經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二人認為孔子、老子都是哲學家,而非教主,這還是由於中國人的現實主義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發展到狂熱地步。
毛澤東對蕭子升說:自古以來,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對宗教也不過於執著,不像西方那樣發生長期的宗教戰爭。此外,儒家思想遠比佛、道二教影響為大,幾千年歷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試取士,以此規範社會人際關係。兩人都認為這都值得大加研究。
青年毛澤東對於佛學研究的心得,在保留下來的《〈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可略見冰山之一角。
《倫理學原理》是德國哲學家、倫理學家泡爾生(1846~1908年)的著作。1909年,蔡元培將日譯本譯成中文。楊昌濟在一師授修身課時,曾用此譯本作為教材。毛主席在精讀此書時,不僅劃了很多圈點、直線和波浪線,而且密密麻麻地寫了1.5萬字左右的批註。
《〈倫理學原理〉批註》中的文字表明,此時的毛澤東,佛學思想在很多方面對他產生了影響。
青年毛澤東雖不信佛,但研究佛教哲學,從中汲取精華,為己所用,幫助自身成長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要善於發現智慧,增強自身本領!
毛主席推崇禪宗六祖慧能及其《壇經》
在中國佛教的幾個宗派中,毛主席比較熟悉的是禪宗。據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建國以後,毛主席曾多次索看《六祖壇經》,有時外出視察也帶著這部經典。
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毛主席就談到過禪宗六祖慧能:
唐朝佛教《六祖壇經》記載,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惠(慧)能敢於否定一切。有人問他:死後是否一定昇天?他說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麼辦?他是唐太宗時的人,他的學說盛行於武則天時期,唐朝末年亂世,人民思想無所寄託,大為流行。
擔任過毛主席的秘書和英文老師的林克,在其所著的《在毛主席身邊的歲月片斷》中說:
毛主席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讚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新精神。我對慧能及禪宗的一點微薄知識,多是得自毛主席的講授。
毛主席對我談到慧能的身世。……為我背誦了這兩首法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毛主席跟我說,後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間本無任何事務,故無塵埃可沾;佛性本來是清淨的,怎麼會染上塵埃?這與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萬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勝神秀一籌。
毛主席還談了慧能學說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甚至可以“喝祖罵佛”。
“禪”是梵語音譯,意即坐禪或靜慮,本是一種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禪,靜靜地坐在那裡“止觀”。自從鳩摩羅什譯出《禪法要解》後,禪學便成了一種專業。而禪宗在中國的興盛,卻是與慧能的變革分不開的,他的變革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種種客觀要求和束縛,完全走向主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把成佛的條件定得很寬鬆;二是用大眾化的語言來傳播佛教。
禪宗六祖慧能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年),小時家境貧寒,皈依佛門後,一直是雜役僧,幹些舂米的活兒。年老的禪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眾僧作法偈,意在從中體會各僧的根基悟性。門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間在壁上作了一首,眾僧都叫好,就是毛主席對林克背誦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滿意,說他只到門前,還未入得門來,讓他重作。
神秀苦想數日,作不出新偈。於是,不識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請人代寫了一首,就是毛主席給林克講解的第二首。弘忍聽後很賞識,就定慧能為傳人,把衣缽授給了他,並讓他速回廣東新興縣老家。慧能遂為禪宗六祖。
《六祖壇經》,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據慧能的談話集錄的一部典籍,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其中記述了禪宗六祖一生得法傳寶的事蹟和他啟導門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淨心”、“自悟”四字。
淨心,即心絕妄念,不染塵勞;自悟,即一切皆空,無有煩惱。能淨能悟,便可頓時成佛。於是,有人用“見性成佛”來概括《六祖壇經》的主旨。“性”就是眾生本來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見”大體就是“自悟”,並且往往是“頓悟”,所以說,“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因為,“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毛主席認為,慧能的思想動搖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禪宗徒眾,敢於說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稱為佛了。這樣,原來天竺各宗派所虛構的高不可攀的佛,變成了舉目可見的平常人。《金剛經》裡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慧能回南方傳播的禪宗南宗,就是要盡力掃“相”,佛即“諸相”之一;掃相必然要掃佛。所以攻擊南禪的宗派,說他們“喝祖罵佛”。
應該說,六祖慧能敢於否定經典偶像和成規,勇於創新,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的特點,與毛主席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並使之中國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無相通之處。對此,毛主席在晚年曾有過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會見一位國外共產黨領導人時,毛主席特別強調: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著,他便以佛教為例說:鳩摩羅什說,“學我者病”,他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中國有個學者叫嚴復,他引了鳩摩羅什的話,在他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上面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