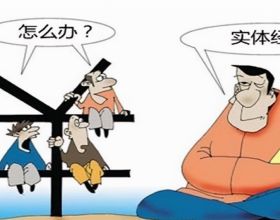長城在中國人眼中,有著極其特殊的寓意。他是國防與軍事的象徵,也是國家興盛與敗落的見證。三十年前,父母帶著我遊覽了北京的八達嶺長城。隨著歲月的流逝,原本記憶中連貫而立體的長城形象變得碎裂而模糊。大約十年前,我便萌生了重遊長城的念頭。這些年來,雖數次到北京,但都是一兩天的行程,遺憾地與長城擦身而過。去年夏秋轉圜之際,我因工作在京小住了兩個月。我與同事們在九月的一個週末,結伴登上了八達嶺長城,終於了卻這樁多年的心願。
去長城的那天,天朗氣清。我和同事們用過早餐,登上了頭天預約好的中巴,直奔京城的西北方向而去。中巴在熱鬧的街區穿行約二十分鐘,進入了八達嶺高速公路。路兩側,樓宇漸漸稀疏,樹木開始密集起來,提示我們正在遠離都市的喧囂,復歸大自然的懷抱。
五十分鐘的路程很快過去。中巴車內的人睏意漸起。就在此時,視野所及的前方道路兩旁毫無徵兆地升起了巨大的山體,卻不見任何矮丘、緩坡作為地勢上的過度。山地與平原,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地貌就這樣硬生生地拼合在一塊了。突然隆起的地形就像一首樂曲,前半部章節舒緩低沉,未作鋪墊便插入一段高亢密集的音符,迅速地將樂曲所表達的情緒推向了高潮。
平時積累的地理常識告訴我,這就是聞名的燕山山脈。此山因其所在地域屬於戰國時代的燕國管轄而得名,燕山山脈夾於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之間,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天然分界線。駛入燕山的“懷抱”,意味著離長城更近了一步。剛才還保持安靜的車廂活躍起來,大夥兒紛紛掏出手機,將背板的攝像頭指向車窗外,攝錄下山區的景緻。我也將身子斜倚著,貪婪地欣賞著靈秀的山色。這兒的山體不像粵贛交界的五嶺那樣來得厚實,但勝在山勢險峻。延綿起伏的山脊線, 就像一條盤亙在蒼茫大地上的巨龍。山脊左右側的山體受雨水的沖刷,有的部位裸露出大片粉黃色的岩石。與充滿裂隙孔洞的石灰岩相比,這種岩石更加的緻密堅硬。山腳至崖壁之間,肆意生長著榆、槐、松、柏、杉、楓等北方常見的樹種和一些不知名的藤蘿、雜草。初秋時節,涼風習習,但燕山裡的林木依然披掛著濃烈的綠色,其中交雜著一些被北風吹黃染紅的枝葉。遠遠望去,依山分佈的植被就像潑在巨幅畫布上的油彩,或濃或淡,或疏或密。將其任何的一塊框入鏡頭,都是一副絕美的風景畫。
山中的景色使人消散了倦怠,也忘卻了時間的存在。越往群山深處行進,山勢愈發陡峭。分列於道路兩邊的山巒像一對合抱的臂膊,將路基兩側的空間不斷收攏。不經意間,中巴車鑽進了一條狹長的山溝。對向的道路已“抬升”到山坡之上,只剩下單側道路仍在溝底蜿蜒。一條單軌鐵路不知從哪座山嶺被遮擋的背面繞了出來,與汽車行進的公路齊頭並進。燕山山脈裡,像這樣險要的溝谷還有不少。在古代,這些山溝與谷地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作戰的捷徑,也是漢民族重兵防禦的區域。
汽車在溝裡走了五六分鐘,夾逼的山體突然向後“回撤”。道路左方出現了一座堅固雄偉的關城,城樓古樸而肅穆,城牆寬厚而高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居庸關。可惜的是,中巴不等我們細看城樓的建築,便飛馳而過。這次長城之行,沒有安排遊覽居庸關,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遺憾。真不知道下次與居庸關相會要等到什麼時候。
離開關隘,意味著溝底的路段結束。地勢再度升高,中巴車順著依山而築的公路走了一段上坡路,再連續穿過三四條悠長的鑽山隧道。當陽光再次射入車廂,大夥兒又一次激動起來。過隧洞前,公路處於對峙的兩山之間。此時,前方視野所及之處,已是一片平疇,重重青山“退到”了遠方,山脊線上巍巍的長城清晰可辨。中巴車繼續開行了十來分鐘,從匝道下了高速路,再行駛了一段普通公路,便抵達了八達嶺長城風景區的停車場。我們一行人將在這裡換乘景區的擺渡車前往八達嶺長城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