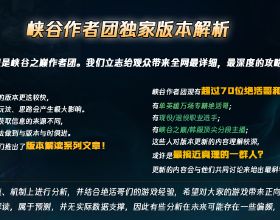又是一年菜籽花開時,王大妮站在自家的房子後,眼前是一排排楊樹,楊樹早已發出了新綠。新綠過後是一條小路,緊挨著小路是一塊菜籽地,菜籽花上飛著蜜蜂、蝴蝶什麼呀!
在菜籽花相鄰的麥田裡,一對小夫妻手拉著手,躬著腰,左躲躲、右閃閃,不時用頭抵抵,還不斷笑笑。“格格……格格……”聲穿過菜籽花飛向站在房后王大妮耳朵裡。
王大妮受不了了,也跟著笑,跟著蹦。後來突然她沒了笑,停了跳,而是“嗚嗚……嗚嗚嗚……”哭起來,肩膀也跟著哭聲一上一下聳起來。緊接著胸前的小皮球也跟著一圈圈轉起來,皮球轉夠了,王大妮也累了,於是帶著小皮球回家了。
回了家,她屋子也不回就坐在房簷下,兩手託著腮幫子,託著眼裡流著的淚回憶著往事。年輕時她可比現在俊,十里八村去問問沒有不知道她的。十七年前她嫁到這裡那天,村道上堆滿了人,都只為能看她一眼,瞅瞅抬她的轎子,聽聽那咿咿呀呀聲。
她嫁的人當然也沒得說,肯定一等一。他王石頭,王大妮的丈夫在方圓百十里是駕駛農機能手,修理高手,什麼高階農具到他手裡都能玩得團團轉。他人長得也不錯,一雙放光的大眼,說起話來眉毛忽閃忽閃。肩膀寬厚結實,王大妮每次靠上去就如躺在樑子上,好像還能聞到麥草和菜籽花的香味。
不久,王大妮就在麥草和菜籽花香味中懷孕了。又是幾個月過去了,她順利生下了一個男孩。每年春天他們也會如公牛領母牛,母牛帶牛犢,在房子後的麥田裡,菜籽花旁撅著屁股,低著頭,抵抵架,一家人撒撒歡。此時他們的心裡只有無憂無慮和快樂。
可好景不長,兩年後王石頭就死於車禍,王大妮哭呀哭,哭走了太陽,又哭來了月亮,送走了月亮,又迎來了日出,只是還是沒有喚醒他的王大山。說什麼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純粹是鬼話、鬼話。
她還記得那天,自從他上班走之後,她的心就砰砰直跳,跳過了胸膛,跳到了嗓門,“咚咚咚……砰砰砰……”平時貪睡的孩子也一反常態哭哭啼啼,搞得她心情很不好。房子後的楊樹上也不知從哪飛來了老鴰,“剮剮……剮剮剮……”叫得她渾身都起雞皮疙瘩。不好了,有禍事要降臨了。
她拿起一土坷垃狠狠向老鴰砸去,老鴰只是拍拍翅膀從這枝飛到那枝,又從這枝跳到那枝,它奶奶的,和姑奶奶玩起了捉迷藏。她惱呀!一次不成,再來一次,這次老鴰卻如孫大聖般在空中翻個筋斗,又穩穩站在枝頭,“剮剮……剮剮剮……”那聲音反更刺耳了。她又急又恨感覺渾身上下都是燙的,就像穿著的衣服全燒了起來,可老鴰卻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依然在枝頭“剮剮……剮剮剮……”。
正在她心煩意亂之時,屋裡地電話鈴突然響了,那端發出了一個陌生人的嗓音:“請問您是王石頭的家屬嗎?”
“是、我是。”
“請您立刻趕往白雲路與蓮花路交叉口,這裡剛剛發生了一場車禍,看是否……”說完就掛了電話。
那邊電話打得很急,語氣也很迫切,她立刻感到了一種不祥之兆。不過她顧不上想那麼多了,立刻帶著孩子就奔向了現場。
當她匆匆忙忙趕到出事地點時,她一眼看到事發地點圍了許多人。當她撥開人群一眼就看到了就倒在血泊裡的丈夫,她一下子撲過去,抱住他,就大哭道:“石頭、石頭你這是咋了?你快醒醒吧!我是大妮、大妮啊!”
過了好一會,王石頭的眼才裂開了一條縫,輕聲說:“大妮,我對不起你,我失言了,不能陪你到老了。”
“你不要胡說了,你會沒事的。”說著王大妮不斷擦著淚,並使勁捶著王石頭。
“大妮、你輕點,把我都弄疼了。”
“嗯、嗯。”她頭點得如搗蒜汁。
“我自己的情況我最清楚,我知道我快不行了,快抱緊我,我好冷。”說著他的眼光又向四周尋找,“我的兒呢?兒呢?”
“乖,快過來,到這來。”一旁站著的兒子怯生生地看著,看著這個突然變了樣的爸爸,一句話也不說。“還不快叫爸爸,快叫呀!你這孩子今天是怎麼了?”
“別難為孩子了,我現在這樣子大人看見都害怕,更何況一個孩子呢。”
“我死了你可要好好活著,找個好人家嫁了。另外我最放不下的就是這孩子。”
“你放心吧!我一定帶好孩子。”他聽完這句話這次是真放心了,最後看了兒子一眼,又瞅瞅她,頭一歪,眼睛慢慢閉上了。
天塌了,地陷了,自此王大妮把心封了。從此她只是全身心照顧孩子,陪孩子弱苗變小苗,小苗變大苗。一晃十五年就過去了,如今孩子都長到了一米七幾,可十五前發生的事總是浮現心頭,那血淋淋的場景時常出現在夢境裡,而又總是驚醒她,讓她夜夜難眠。
她是出生在一個新時代的女性,可心裡始終裝著的是舊傳統的思想,她忘不了他,忘不了過去的一切。他給了她快樂,也給她身心套上了一把無形的枷鎖。她要用十幾年去撫平,也許一生。
當初他走的那些年,中間也沒少人搓和讓她再找一個,她都婉言謝絕了。她不想草率行事,關鍵是她還沒有走出愛的陰影,她要對得起別人,更要對自己負責。
這段路王大妮一走就走了十五年,孩子走高了,她走老了。不瞭解的人還以為她眼光高,裝貞潔。可她心裡的苦只有她自己知道,既不怨也不恨,要怪就怪命不好。
這十五年一個人拉扯一個孩子的確不易,不過幸好有鄰居張木經常幫忙,莊稼該打藥了幫忙打了,到了收的時候,又出力替她拉回家。孩子小時候也沒少生病,每次又都是張木開車送到醫院,想想虧欠張木太多。
張木是個實誠人,話不多,每次只是默默幹活,幹完活連口茶都不喝。他也是一個可憐之人,早年就死了妻子,這些年也沒能續一個,連個洗衣做飯的人都沒有。人心都是肉長的,王大妮看在眼裡,有空時自然會過去幫忙打理打理,算是報答。
一來二往,日久生情,兩顆寂寞的人漸漸地走近了,只是這張木不善表達,滿肚子的話說不出口,而王大妮思想上又有陰影,這些年猶猶豫豫,中間又缺個繫鈴人,這鴛鴦的鈴鐺只能是幹“叮鈴鈴……叮鈴鈴……”就是叮鈴不出結果。
盼來了花開田野,等過了百花凋零,張大妮依然寡著,張木還是幹棍一條。張大妮每天早上對著鏡子梳頭,數著日漸多起的銀絲實在是著急了。她不想把這份愛帶到墳墓,更不想遺憾終生,於是她耍起小心計,像春天發情的貓咪試探性的叫幾聲,“喵嗚……喵嗚嗚……”她要叫醒張木,喚來她落暮下的愛情。有時張木幹完活,王大妮故意發發牢騷來刺激刺激張木,可張木就是木頭棍子一根,橫著是一根棍子,豎著還是一根棍子,棍子、棍子,這個死棍子。
終於在一天傍晚,張木又拉完麥,連手都沒洗就往大門邁。這次王大妮瞅準了機會,咬咬牙,握握拳一個箭步衝上去就抱住了他的腰,“你難道真的是木頭做的,怎麼不明白俺的意思。”
王大妮抱著張木,她的心貼著他的後背,兩個人的呼吸聲疊加在了一起,此時兩個人的心就如老太太手裡拉著的風箱,“呼呼……呼呼呼……”一聲緊一聲慢,又如高潮擂著的大鼓,“咚咚……咚咚咚……”慢了,快了,快了,慢了,排山倒海,“轟”火燃了,燒旺了,爆發了。
張木喘著粗氣說:“怎麼不明白,俺明白就是說不出口。”
“說不出也得說,俺教你,我愛你。”
“不行,說不出來。”
“你這悶驢,我還不信了。”說著王大妮就鬆開了手,又抬起腿朝他大腿上就是一腳。
“你說不說,說不說。”說著又抬起了腿。
“俺領教了,俺說、俺說,你愛俺。”
“說錯了。是你愛我。”
“好。是我愛你。你愛我,我愛你不都是一回事嗎?”
“不一樣。”說著兩個人扭抱在了一起,那樣子就如春天枝頭盛開的菜籽花,分不出哪枝是哪枝,哪朵是哪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