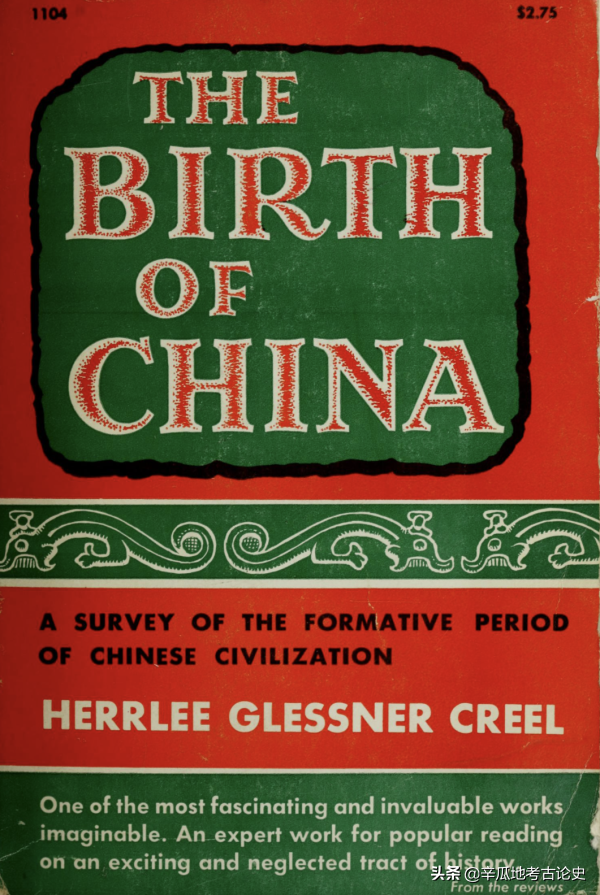“早期中國”指的是從人類歷史在東亞地區開始之時(大約兩百萬年前——這個年代大致代表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開始,關於中國境內最早的人類化石遺存,目前還存在爭議),到公元220 年東漢結束這樣一個漫長的時期。而公元220 年也經常被不準確地看作中國進入佛教時代的標誌。作為一個為中華文明打下如此重要基礎的初期階段, 早期中國經常被視為了解中國的一個視窗,它在政府、社會實踐、藝術、信仰和哲學思想方面為學習各階段中國歷史的學生提供了一系列必要的基礎課程。但是,就一般意義而言,文化是決定我們現代人類生活和行為方式的潛在指揮系統,人們生活於其中,而歷史是教授文化最好的一種方式。那麼很自然地,對早期中國的瞭解可以為現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及與之相關的價值觀念提供一個最基本的解釋。這就是我們研究歷史,或具體說研究早期中國歷史的重要意義。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早期中國研究是受益於現代學術進步最明顯的領域之一,特別是考古學科的發展每天都更新著我們對古代中國的理解。但是,它也是一個政治和學問有時會相互影響,並由不同民族或國際的學術傳統所共同塑造的領域。
在開始我們這段古代歷史的旅程之前,我首先介紹早期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時代界定,這對理解《早期中國》中將要討論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是很有必要的。出於同樣的目的,本文還將對早期中國研究作為現代學術領域的發展過程做一個簡短的討論,這將會使讀者意識到不僅要看到過去,同樣重要的是還要了解看待和解釋過去的不同方式。
地緣中國:自然環境
地理學家常常把中國的地勢分為四大階梯: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它橫跨現今青海省境內以及西藏自治區的全境,佔據中國領土總面積的四分之一(見早期中國重要考古遺址圖)。第二階梯從青藏高原的邊緣向北、向東延伸,由許多山脈和高原組成,比如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平均海拔在一千到兩千米。第三階梯由華北平原、位於東北部的東北平原、南部的長江三角洲以及交錯分佈的丘陵組成,平均海拔在五百到一千米。第四階梯是大陸架,它從中國東部和南部海岸延伸進入海洋。
雖然我們討論的只是那些被認為屬於早期中國部分的地區,然而回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仍處在其幼年期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更多的文化發展發生在由第二階梯上的山脈和高原所環繞的那些山谷和帶狀平原地區,或是沿主要山脈分佈的過渡地帶,而不是位於東部沖積平原的中心地區(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的早期定居文化開始於今伊拉克北部,然後向東南發展,在公元前5500―前4800年薩馬拉文化時期就已經佔據了臨近波斯灣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下游地區)。簡單地講,這種發展的原因是生態學方面的。在公元前2000 年,中國東部平原的大部分地區仍舊被沼澤和湖泊覆蓋(歷史有記錄的黃河改道就有二十六次),部分海岸線位於現今海岸線向內陸縮排至少一百五十公里的位置。先秦文獻中記錄的華北平原上有四十多個沼澤或湖泊,大部分沼澤或湖泊在公元三世紀以後已經乾涸。實際上,幾千年以來,華北平原一直處於黃河流經第二階梯帶來的大量泥沙所形成的沉積過程中。自然環境,特別是地形和氣候變化無疑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早期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人類生存活動也改變了地表結構,使環境發生重要的變化,就像近代工業社會的擴張給地球帶來的顯著變化那樣。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古生物氣象學家在認識中國多種生態區的長期氣候變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見圖一,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從河床和湖底鑽取數百個土壤標本,透過對其所含孢粉和其所屬的各種型別的古植物進行分析,可以構建出一個地區長期的溫度波動變化)。根據不同地點的相關資料,研究者可以界定約11,000年以來在溫度波動方面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大約在距今11,700年(11,700 BP)的更新世末期(BP[距今年代]用於地質學中,表示長時間跨度;而BC[公元前]被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所使用,表示近幾千年內的時間;更新世在地球史上是個地質年代,開始於距今2,588,000年,結束於距今11,700年,隨之而來的是全新世[最新階段]),當地球在邁出最後一個冰川期的時候,華北地區的溫度攀升,平均溫度高於現在三到四攝氏度,降水量(每年一百五十毫米)比今天多百分之四十。這意味著在華北平原大部分地區直到青藏高原邊緣地帶有著豐富的降水量以及眾多的湖泊和沼澤。就中國總體而言,在農業生活開始之前,氣候溫暖溼潤,並且被厚厚的植被所覆蓋。這種高溫(圖一中的長的低彎曲線)從距今八千年持續到距今五千年,並在其較晚時期有大幅度波動,直到距今三千年的時期,溫度驟降,低於現今氣溫(參見Shi Yafeng and Kong Zhaozheng, et al. , “Mid-Holocene Climates and Environments in China,”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7 [1993]: 222)。這次降溫期在歷史年表中恰好是在商代(公元前1554―前1046 年)結束,西周(公元前1045―前771 年)開始這一時期。但是在商代的大部分時期,華北地區的氣溫仍舊比現今氣溫高出約二攝氏度。在距今三千年初溫度驟降之後,曾經有一個時期,溫度又再次攀升。但是在最近的一千五百年間,華北地區的溫度比今天寒冷得多,當然這已經不在早期中國範圍內了。
相對來說,上面所討論的氣候變化對南方地區的影響較小。但是比起北方地區,南方地區多山,並且被山脈劃分為沿長江的三大獨立地區,分別是:四川盆地、長江中游的湖泊和沼澤地區以及下游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最近的一次降溫發生在約公元第一個千年的中期,導致了南方地區的一些重要湖泊萎縮,甚至乾涸。例如,先秦時期,從今天的武漢向西一百二十公里以內的長江中游平原的大片地區都在著名的雲夢澤水面以下,在歷史記載中也被稱作“大澤”。但是在公元三世紀之後,大多數沼澤漸漸乾涸,並且形成了現今環繞中心城市的耕地。
中國東部沿海的航海業在早期中國當然是可能存在的。這一點可以從跨越北方和南方沿海地區的早期文化的廣泛接觸中看出。同時,考古學上東南大陸和臺灣島之間的文化聯絡也證明了這一點。並且,居住在臺灣島上的各種南島語系族群又與太平洋島民有著進一步的聯絡(“南島語系”是一個語系,廣泛分佈於太平洋及東南亞島嶼和半島,甚至向西遠達馬達加斯加島;有關早期中國語言區域劃分,參見 E. G. Pulleyblank[蒲立本],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 in 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11-466)。在西南地區,穿過現今雲南的熱帶雨林,同南亞次大陸的文化聯絡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建立了,並且這一聯絡在秦漢帝國時期又得到進一步擴充套件。在西北地區,許多綠洲一路向西越過中國邊境。儘管透過這些綠洲或者廣泛跨越北方大草原的物質產品和思想的交換可能始於青銅時代早期,甚至更早,但是中國與亞洲大陸內部的地緣隔絕直到公元前一世紀才被完全打破。甚至在公元前二世紀,早期中國的探險者發現通往中亞的道路之後,沿這條新興的“絲綢之路”的旅行也是非常困難的。
早期中國和大的歷史趨勢
何為“早期中國”?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把早期中國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的、獨立的階段嗎?上文提到早期中國止於公元220年東漢滅亡(對於“早期中國”明確的時間劃分見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寫的《早期中國》雜誌創刊詞,他把這份雜誌的目標解釋為:“《早期中國》雜誌是一個研究通訊,它致力於中國史前及商、周、漢時期研究領域的新理念的傳播和驗證”)。有三個原因可以說明為何我們把這一段長的歷史時期作為研究和教學的一個完整領域。首先,儘管早期階段的中國文明也會不可避免受到其他地區的影響而有所改變,然而它的演化基本上是基於東亞本土的傳統思想、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一系列發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這個次大陸的內在成長過程。然而,漢帝國在公元前一世紀擴張至中亞地區,這種擴張使中國開始同世界其他地區的重要文明有了持續的接觸。最為重要的是中東和印度,隨之而來的佛教的傳入把中國文明帶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維度——一個新紀元的戲劇性開端(在西方學術界稱為“佛教時代”)。在世界歷史上,與這種轉折並行的是西方由古典時代到基督教時代的過渡。第二,這個時期的研究有一個考古學提供的共同的資料基礎。儘管在早期中國晚期,大量的資訊可以透過傳世文獻資料獲得,然而出土文獻(尤其是地下出土的法律文書)仍然是我們研究中最重要的根據。第三,由於這些資料很多形成於約公元前221 年中國的書寫系統統一之前,因此,早期中國的研究極大地受惠於古文字學的支援——古文字學研究的物件是形式多樣的古代漢字書寫和銘文。
儘管東漢滅亡以前發生的所有事件都在早期中國的時間範圍以內,然而,按照慣例,我們以公元前7000 年左右中國早期農耕社會的出現作為開始(在此之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體質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是文化進步的結果,這種發展可以在以全球為研究範圍的現代科學領域得到有效的分析,因此,它的研究不受我們所說的所謂文化和地理板塊的“早期中國”的限制), 特別是在黃河和長江流經的陸地上。在接下來的兩千年裡,中國東部地區較大範圍的原始農業社會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綜合體。公元前4000 年後期,許多地區開始出現由不同等級聚落組織的早期複雜社會體系,通常由一個大的夯土城牆所環繞的政治中心來領導(在人類學的定義中,“複雜社會體系”一詞指的是,在一個社會中至少有兩個或者更多的階層和一個以酋長權力為中心的中央決策過程)。緊隨其後,首先在中國北方和南方的有限區域內,經過高度的社會發展,出現了早期國家或國家水平的社會。從考古和歷史的研究中我們充分了解到,在華北地區,這些早期國家被一個像商(公元前1554―前1046 年)和西周(公元前1045―前771 年)這樣的王朝統治。它們因此被稱為早期“王國”(royal states)。公元前771 年,西周國家崩潰,缺失一個真正的中央權力,這隨即開啟了一條王國間激烈的戰爭之路。直到公元前221 年秦統一中國,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帝國,這一持續了五百年的混戰局面才得以終結。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 年)統治之下,這個帝國官僚系統得到鞏固和加強,最終,這一早期中國時期隨著東漢帝國(公元25―220 年)的滅亡而結束。
因此,在早期中國,我們觀察到不同級別和規模的社會組織的興衰;並且本書的重點就是追溯和解釋早期農業村落髮展為國家直至帝國的社會發展過程。如果我們把中國歷史看作一個整體,那麼早期中國是整個歷史長河中跨度最長的時期,並且也是社會變化和政治發展最激烈的時期。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區域範圍內的原始文化特質被逐步改變,並且融合成為有特色的中國文明。
重新發現中國古代
儘管“早期中國”概念的形成相對來說是近來的事情,然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對這一時期的研究已經有一個非常長的歷史了。一般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三個重要發現為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開啟新的天地,並且直接促成了中國現代史學的崛起:首先是1899年河南北部安陽地區商代甲骨文的發現;其次,1900年在位於甘肅省西部沙漠邊緣的敦煌佛教石窟內,發現了多達五萬卷的中古時期的文書;再次,是1909年儲存在北京故宮的明清兩朝檔案檔案的丟棄和隨後的重新獲得。無論是對現代中國歷史還是整個世界的歷史,這些重要的文化事件都具有多重意義。
儘管上述後兩個重要發現在時間段上不屬於早期中國的範圍,然而英國探險家奧雷爾· 斯坦因(Aurel Stein)在去敦煌的路上,在一個沙漠的邊塞遺址(近來被重新發掘)中挖掘出了大約七百片寫有文字的竹簡,由此引發了該地區及該地區以外一系列西漢帝國時期行政文書的發現。由於斯坦因沒有能力做這樣的研究,這些敦煌出土的竹簡隨後被一位在北京的法國學者,也就是西方漢學研究之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研究並出版。此時沙畹剛出版了古代中國最重要的歷史文獻的譯本,即公元前一世紀由司馬遷撰著的《史記》。沙畹關於敦煌漢簡的研究著作被帶到中國後,便被中國著名的學者們影印並加以註釋,作為新版本出版。
敦煌漢簡連同沙畹所熟知的歷史文獻一起提供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背景:其中,早一代的法國漢學家受到了以語文學和歷史語言學為重點的訓練;考慮到敦煌文獻包含近十種語言的資料,他們的這種興趣當然並不限於漢語言。不過,法國學者的興趣逐漸由語言學擴充套件到歷史和宗教研究的各個領域,並且在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那裡,早期漢學的研究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對實物的研究,特別是對青銅器和銅器上銘文的研究(關於西方漢學的早期歷史,參見David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p. 1-40; H. Franke,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in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pp. 11-23)。
在中國本土,甲骨文的發現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和古董商有關,但是這些發現逐漸帶來了學者們對甲骨的收藏及研究和出版,而這些學者也對宋代(960―1279)以來金石學傳統中著錄的商代和西周青銅器銘文有所研究。王國維(1877―1927)在這些學者中貢獻尤著,他因忠於清朝而在清朝滅亡後流亡日本多年,後回國任清華國學院教授。王國維完成了一系列有關中國早期王國——商和西周的宗教和文化制度研究的文章。王國維的研究奠定了現代早期中國歷史研究中主要以發掘出土的古文字學材料為基礎進行研究的基調。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宮廷中的占卜記錄,對甲骨文的識讀直接促成了1928 年河南北部商朝都城安陽的發掘。這使得安陽殷墟成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直到1937 年7 月日本全面入侵華北地區以前,位於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共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發掘,對商王的宮殿與墓地都進行了發掘,發現大批材料,當然也包括更大數目的甲骨。抗戰結束之後對安陽的發掘工作隨即恢復,並一直持續到今天。安陽考古對我們理解商代和早期中國文明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安陽發掘者——頭戴剛從1004號商王墓中出土的青銅頭盔。照片攝於1935年第十一次發掘。圖的正中扮演商王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資深考古學家石璋如,他手持一件青銅長刀。石璋如的左邊(後面)是夏鼐,他於1962—1982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後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所長。最左邊站立的是尹煥章。石璋如右邊是李光宇;最右邊懷 中抱著一隻貓的男子是王湘。
現代中國史學有許多不同的來源,從不是一個單一的學術傳統。當王國維致力於以考古挖掘資料和傳世歷史文獻的互證為基礎重建中國古史系統的研究時,另外一種基本上屬於文獻研究的新趨勢主張完全摒棄有關中國歷史的傳統觀點。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對中國政治現實日漸加深的挫敗感在1919 年五四運動時達到最高峰。這種政治文化趨勢在歷史研究中的反映被稱作“疑古”運動,由顧頡剛(1893―1980)領導。他是北京大學一位年輕的畢業生,早在1921 年就形成了自己有關中國歷史的理論。對於顧頡剛來說,傳世文獻中的中國古史是一代代後人創作的虛假史實的層層堆砌,因為很明顯,那些屬於後代的文獻資料,特別是漢代的文獻,經常比那些與古史同時代的早期文獻講得更多。儘管我們可以用這些材料來研究戰國至漢代這一時期的人文思想,但是把這些文獻當作更為早期的歷史的材料來看是站不住腳的(顧頡剛在1927年出版的《古史辨》創刊號中就宣傳了這個理論,《古史辨》七冊書於1941年之前出版完畢,它是“疑古”運動的核心著作,關於顧頡剛的英文研究,請看 L.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用顧頡剛的精神導師胡適的話說,中國歷史必須被縮短至少兩千年,應該從東周時期(公元前770―前256 年)開始。
顧頡剛和他的同事們在打破傳統中國古史觀權威上的革命性作用是不應該被低估的——透過這樣做,他們使傳統的中國史學邁出了史學現代化的第一步。然而,作為一門嚴肅的學問,“疑古”運動被其自身邏輯中的眾多缺陷所削弱。顧頡剛和他的追隨者們不僅在做研究時幾乎無視由王國維等學者所取得的很有希望的堅實進展,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論證後世捏造某一傳統時,其觀點所具有的說服力完全基於早期“不存在”相關記錄,這本來就是不能被證明的。在很多情況下,某些文獻雖然被顧頡剛和他的追隨者們判定為後世的偽作,但當考古發現提供了它們在早期存在的證據時,他們註定是失敗的一方(顧頡剛和其追隨者的論證邏輯也受到另一個邏輯的破壞,即時代越早,能夠流傳到現代的資料也越少,因此,當說某一記載在先秦時期不存在時,其實很難判斷它究竟是不曾存在,還是曾存在過,但沒有流傳下來,鑑於過去三十年間在戰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新的文獻材料,我們不禁要問,在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之前究竟有多少文獻在歷史上銷聲匿跡?)。但是更一般地來講,“疑古”派把歷史研究簡化成了對文獻年代的考察,這將歷史學帶入了一個極其狹窄的視野中。“疑古”派研究只是一門研究文獻的學問,作為這樣一種學問,它並未對早期中國研究領域整體上越來越多依賴同時期古文字和考古學材料的這一變化做出及時反應。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和臺灣,“疑古”運動基本上被邊緣化,而主流歷史學則是採用一種更積極的態度來對待傳世文獻。
在日本,“疑古”的觀點在白鳥庫吉(1865―1942)等學者的著作中已經有了預示。白鳥庫吉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文背景下,花費畢生的精力試圖否定從黃帝到所謂夏朝的建立者禹的歷史存在。然而,特別是在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領域,一種並行的新發展趨勢產生了。當這樣的學問在中國仍處於形成期的時候,日本也培養出了它的第一代學者,如最早研究中國青銅器的貝塚茂樹(1904―1987)和專門研究甲骨文的島邦男(1908―1977)。基於日本在中國文獻學研究方面長期的傳統,加之二十世紀早期中國著名學者訪日的促進,日本遂成為中國之外現代漢學的誕生地之一。特別應該提到的是郭沫若(1892―1978),他是近代最有創見的青銅器銘文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在早期中國研究領域的代表;郭沫若在1928 年國共合作破裂之後流亡日本期間完成了他大部分的研究工作。
的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傳統都深受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影響。由於戰後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非官方性,儘管日本學者在社會分析中也運用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但最終還是擺脫了當時在中國盛行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歷史分期理論。這使得日本學者能夠創立新的研究模式,並能在早期中國領域探索新的論題。也正是因為這樣,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時候,當中國的學術研究受到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干擾,日本在漢學研究領域能夠始終維持著較高的水平,譬如說增淵龍夫(1916―1983)、西嶋定生(1919―1998)等戰後學者的中國古代社會和經濟史研究。總之,可以這麼說,日本的學問有著能夠平衡具體的實證研究和較為寬廣的理論視野的優勢。這種優勢使日本學者特別在早期中國社會經濟史領域貢獻出一批優秀的研究成果。
北美早期中國研究的新進展
顧立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生於芝加哥,獲中國哲學博士學位,曾跟從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貝特霍爾德· 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學習中文。為了對早期中國歷史有更深入的理解,顧立雅於1931 年來到中國。那時,在北美只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對早期中國歷史抱有真正的興趣。在中國期間,顧立雅同中央研究院的前沿學者們保持著緊密的聯絡,並多次前往安陽參觀正在進行的發掘工作。他1936 年返美后執教於芝加哥大學,不久即出版《中國之誕生》(見H.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37])。此書為長期以來只閱讀法國學者著作以瞭解早期中國文明的西方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的入門書。此時的芝加哥也成為中國學者訪學的重點,他們的學術興趣對芝加哥大學教師的研究起著輔助性的作用(這些訪問者中最著名的有商代甲骨文研究的著名學者董作賓[1895―1963],以及從事青銅器和金文研究的青年學者陳夢家[1911—1966])。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隨著更多關注漢末之前歷史的學者在北美的主要高校任教,一個基本的早期中國課程體系在北美建立起來了。然而,早期中國研究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獨立學術組織的健全的學術領域,並於1975 年開始出版《早期中國》(Early China)雜誌,是到了這些早期學者的學生們這一輩才實現的。在此引用該雜誌廣受尊重的創辦者,也是美國第一位真正的商代甲骨文研究專家吉德煒的一句話:“如果我們要帶著一種同情心去深入理解現代中國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忽視它的古代歷史。早期中國研究在我們現代的課程設定中有其合理的位置;我們必須保證它的價值被大家所認識。”(Early China 2 [1976]: i)
然而,同歐洲和日本相比,除了源自歐洲漢學的藝術史和文獻學之外,美國的早期中國研究在過去的學術根基相對薄弱。正是因為這樣,北美的早期中國學者受到了在中國興起的“疑古”運動的強烈影響。顧頡剛的自傳在中國出版之後很快就被譯成英文,而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所做的關於顧氏生平和學術成就的專著在《早期中國》雜誌創辦前幾年就已經出版,這使得顧頡剛成為在美國最著名的現代中國歷史學家(見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北美的早期中國研究不僅在幾乎與中國相隔絕的情況下度過了它的成長期——1950 年以後中國同西方國家的聯絡就中斷了,也走上了一條同中國的辯論之路,尤其是過去二十年間就一些重要的問題與中國學者多有爭論,比如夏朝存在的真實性問題,或者可以廣義地理解為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和中國變成一個統一民族的程序問題。
爭論的真正原因是對於中國古代傳世文獻的價值在認識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一方面,“疑古”運動繼續影響著北美早期中國研究領域中的很多學者,並塑造了他們的基本學術態度;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學術傳統已經日漸遠離這一個派系。儘管在許多情況下,批判精神使北美學者免於陷入傳統史學的泥潭——這是他們的幸運,然而只有很少的學者意識到“疑古”運動自身邏輯上的缺陷和因此而喪失的很多研究機會。可以公平地說,那些徹底否定傳世文獻對理解早期中國歷史之價值的持極端懷疑論的學者雖然存在,但人數還是很少的,大多數北美的早期中國學者在研究中依舊繼續使用傳世的文獻資料。在更理想的情況下,傳世文獻資料會同考古挖掘材料或者古文字材料相結合,從而形成一種更加平衡且較少片面性的古史解讀方法。
然而,這裡始終存在這麼一個問題,那就是:上述中國、日本和西方(歐洲和美國)的漢學研究傳統是否屬於三個相互區分的不同的學術領域?或者,它們是否應該被看作一個整體的人文事業?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也許隨著新千年的到來,當全球化的趨勢影響到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時候,這個問題及其可能的答案便顯得不那麼重要了。文獻和銘文資源的數字化及其新資料以電子形式發表使得中國以外的學者同中國本土學者一樣能夠對新發現做出快速的反應。中國財富的日漸增長還可以給更多中西方學者提供學習交流的機會,因此,年輕一代的學者將會更加通曉不同的學術傳統,更善於接受不同的觀點。早期中國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國際合作的產物,在未來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