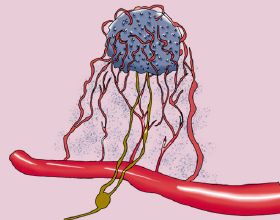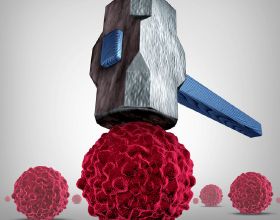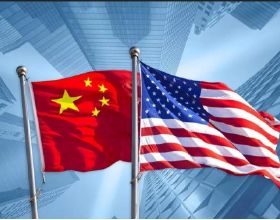正陽門外最堪誇,王道平平不少斜。
點綴兩邊好風景,綠楊垂柳馬纓花。
——蘭陵憂患生《京華百二竹枝詞》,1909年
(一)
民國三年六月,北京建城以來的第一個市政管理機構京都市政公所正式成立。不過,公所初創時的頭等大事只有一件:如何拆掉四九城的城牆。
北京城的格局是“內九外七皇城四”,或者叫做“大圈圈裡面有個小圈圈,小圈圈裡面有個黃圓圈”,皇城雄踞內城正中,高牆環繞,且皇家禁地,平民不得接近,東城的人要去西城,就得從大清門外的棋盤街或是地安門北的皇城根繞行,一袋煙工夫的路程,愣是能走半天,為此還衍生出一個怪現象:東西城的人雖然相距咫尺,但口音並不同。
清末以來,北京人口急劇增長,城內擁擠不堪,臭水橫流,遍地垃圾,不過城中百姓不以為怪,甚至隱隱還有一絲自豪,畢竟祖祖輩輩都是這麼過來的。只有少數開眼看世界的明白人認識到封閉的城牆阻礙城市發展,洋人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租界,從來不蓋圍牆、不設藩籬,結果物暢其流、人稱其便,繁華熱鬧勝於舊城百倍,所以頗有一股聲音呼籲效仿西方,改城為市。
八國聯軍禍亂京師的時候,強行扒掉永定門西側的一段城牆,鋪設鐵軌,將京津鐵路的終點從城外的馬家堡延伸到天壇(後來又修建了前門火車站),這是北京拆城之始,對於洋人破壞公物的行為,北京南郊鄉民居然讚不絕口,因為發現進城不那麼擠了,而且不用受那城門盤查的鳥氣。
民國成立的第一年,上海人便迫不及待地推平上海縣城垣,北京城的管理者也躍躍欲試,頗想擼起袖子開創一番新氣象,不過,堂堂帝都怎能和上海這個僻處東南的三線小縣城相提並論,城牆要拆,但不能大拆。
話說皇城內有一條東西向的大街,因位於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之間,故得名長安街,此處原本是閒人免進的大內禁地,在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主持下,市政公所扒掉中華門(明朝叫大明門,清朝叫大清門)內的幾段宮牆,鋸掉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高高的門檻,將長安街改造為東西幹道。
市政公所還打通了紫禁城神武門外的東西大道。
北京交通的老大難問題是正陽門,也就是前門。
前門在內九門中規模最大,號稱國門。前門外是繁華的大柵欄商業街,城門腳下聚集著無數引車賣漿的流動攤販,甕城內有觀音廟、關帝廟各一座,京漢鐵路與京奉鐵路交匯於此,城樓外蓋起了兩座火車站,如此龐大的人流量只靠城門門洞通行,端的是摩肩擦踵、人肉相疊,足以和今日北京的地鐵早高峰一戰。
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提交了正陽門改造計劃:拆掉甕城與東西月牆,在兩側城牆再開兩個門修築馬路。
方案一公佈,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前門一帶的商販大為不滿,他們首先鼓動京師總商會上書北洋政府抗議,然後在報紙上大打輿論戰,添油加醋地傳播一種論調,說是正陽門一動就會有禍事,第一次遇到了八國聯軍,第二次遇到了京軍譁變,這次才開始提議拆牆,就發生了張家口兵變。
這些捕風捉影的說法讓京師人心惶惶。大總統袁世凱尚未坐穩寶座,不願節外生枝,下令停工。
大柵欄的商戶自以為得志,哪知半年後,袁世凱忽然雷厲風行地重啟工程,在他的親自關懷下,工程異乎尋常地順利,不僅商戶們乖乖搬遷,連美國使館在前門附近擁有的一片操場也主動讓出用於修路。
原來,袁世凱起了當皇帝的小心思,而正陽門是清朝的國門,符合他“除舊佈新”的心理需求。
正陽門改造完成後,甕城不復存在,新開門洞兩座,新闢馬路兩條,道路之外又增設了些綠地、噴泉之類景觀——這讓正在遊歷中國的瑞典學者喜仁龍嗤之以鼻,看到原汁原味的傳統中國古建築被平淡無奇的西洋城市風街景取代,喜仁龍心情複雜,酸溜溜地寫道:
“那些有幸能看到當初帶有甕城、甕城門和甕城場地的前門原貌的人,看到如此多的古建築被大規模拆毀,無不感到痛惜,但他們也承認,原有狀況無論是從衛生或是交通的觀點來看,都是不能容忍的。”
朱啟鈐乘勝追擊,雄心勃勃地制定“京都環城鐵路”計劃,鐵軌建在城牆與護城河之間,所以要在甕城上開洞,誰知工程方圖省事,直接將朝陽門和東直門的甕城夷為平地。
朱啟鈐原本還計劃將內城西南琉璃廠一帶的城牆開通,這一帶人煙輻輳、商鋪如林,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奈何高牆阻隔,淘個古玩字畫啥的還得繞道宣武門或前門,很不方便。
可惜,這一計劃尚未施行便胎死腹中,袁世凱稱帝夢碎去世,朱啟鈐作為“帝制禍首”之一黯然下臺,此後,北洋政府動盪不堪,朱啟鈐的計劃遂被束之高閣。
十年間,北京城的主人如走馬燈般變換,1926年,馮玉祥率國民軍佔領北京,任命心腹大將鹿鍾麟為京畿警備司令,這鹿鍾麟雖然是個赳赳武夫,卻頗想在市政上有所作為,偶然翻閱舊檔案,讀到開城門計劃,他大聲叫好,立即下令拆城牆。
馮玉祥為新開挖的門洞取了個寓意美好的名字:“和平門”。
一晃又是多年,北京變成了北平,抗戰時期,北平落入敵手,兩個日本人佐藤俊久與山崎桂不知何故對千年古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廢寢忘食地搗鼓出一份厚厚的《北平都市計劃大綱》(這居然是北京歷史上的首個城市規劃),按照他們的設想,北京城就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改建太費勁,最好的辦法就是另起爐灶,具體而言就是在西郊五棵松開發居住區,在東郊開發工業區。
為了連線東西兩個“新市區”,有必要將長安街延伸到城外,於是在東西城牆各開兩個豁口,命名為“啟明門”與“長安門”,不得不說,這名字頗有中國韻味,不過起名者是日本人就是原罪,於是抗戰勝利後,北平政府順應民意,取和平建國與民族復興的含義,分別改名為“建國門”與“復興門”。
(二)
1952年5月,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門前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北京圖書館門前巍然聳立著一座大牌樓,俗稱“三座門”,每個門洞只能容一輛車子進出。當日,一部汽車拐彎駛向“三座門”時,對面一輛車赫然飛馳而來,慌亂之下,汽車重重地撞在門垛上,司機重傷,送醫後不治身亡。
這件看似平常的事件迅速引爆了一個話題:需不需要拆掉北京的舊城牆和牌樓?
北京市政府認為很有必要,並迅速出臺了方案:拆掉朝陽門和阜成門城樓與甕城,東四、西四、歷代帝王廟等處的牌樓一併拆除,這樣,整條長安大街將暢通無阻,成為真正的康莊大道。
這可急壞了一個人,就是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
其實,民國三十餘年已經斷斷續續地拆了很多城牆,加上疏於維修,坍塌傾圮者比比皆是,不過城樓大多儲存,雖然破破爛爛的,若是略加整修,也不難恢復昔日燕京的風采。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個文化人,梁思成覺得雙方應該有共同語言,他苦口婆心地勸道:城門、牌樓是北京的獨特景觀,北京城的風格是歷史形成的。保護好古文化建築,城市才能保持美麗。再說,交通問題可以用建環島等方式解決,不一定要破舊立新嘛。
吳晗不耐煩了,他可是連十三陵都想拆的人,沒等梁思成說完,便用嘲諷的語氣說道:思成啊,你太保守了。將來北京城發展起來了,到處都是高樓大廈,你這些牌坊、宮門也就成了雞籠、鳥舍,哪有什麼觀賞價值?
尖酸刻薄的語氣讓梁思成情緒崩潰,當場老淚縱橫。
數日後,鄭振鐸邀集若干文化界名人聚會,吳晗和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均在座。席間,不知哪個沒眼力見的提到拆城樓的話題,鄭振鐸唏噓道:推土機一動,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就要壽終正寢咯。
林徽因忽然顫顫巍巍地站起來,指著吳晗的鼻子,厲聲道:你們將來一定會後悔的!就算將來恢復了,也是假古董,不是真古董了!
林徽因已經罹患肺病,心情又極激動,所以嗓音全無平時的圓潤,顯得十分虛弱,吳晗不願與病人衝突,只得尷尬地陪著笑,一言不發(後來林徽因病情加重,於1955年仙逝)。
總理親自出面做梁思成的工作,梁思成很固執,痛心疾首地說:歷代帝王廟前的牌樓一拆,以後再也看不到夕陽斜照、西山餘暉的美景了。
總理微笑著回了一句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勞動人民更喜歡欣賞煙囪而不是落日,轟轟烈烈的城市建設終究不以梁思成的個人意志為轉移,隨著牌樓的一個個消失,他痛哭了幾次,引得心胸豪邁的領袖戲言說城門打洞,居然有人哭鼻子(小布爾喬亞就是矯情)。
1957年,梁思成再次發表意見說:東直門城樓不能再拆了,這是現存唯一的明朝楠木建築,價值連城。民國時,有個日本工匠看到這個建築,寧願自掏腰包做維護……
這些陳詞濫調自然沒人愛聽,東直門城樓毫無意外地被拆,梁思成怔怔地在東直門下坐了一個禮拜,默然無語……
如今的北京城,只剩正陽門城樓、德勝門箭樓、東南角樓等寥寥幾處遺址,它們落寞的身影蜷縮在現代都市的鋼筋水泥中,訴說著昔日的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