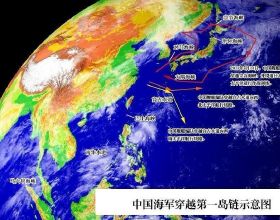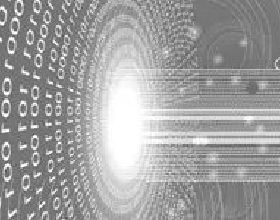“難以置信的美!舞蹈像天鵝一樣優雅,像中國龍一樣敏捷。《洛神水賦》,河南衛視的一個水下舞蹈節目。”(原文為英語,化自《洛神賦》中名句“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因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點贊,令河南衛視一段不到兩分鐘的水下舞蹈影片《洛神水賦》(原名《祈》)火爆網路。因影片多采“飛天”造型,它又被網友稱為“水中飛天”。
洛神宓妃是本土傳說中溺死的女鬼。《昭明文選》注稱:“宓如,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洛神。”
黃初四年(223年)七月,32歲的曹植被再貶為雍丘王,自稱“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據《三國志》:“(曹植)入見清河長公主……帝(曹丕)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曹植)自殺也,對帝泣。”可見,曹植寫《洛神賦》,有投水自殺之意。只是文筆巧妙,反讓宓妃從女鬼成了女神。
那麼,本土女神又是如何與西來的“飛天”結合的呢?除編舞者的人為創造之外,二者確有一點歷史淵源。
“飛天”本是一種鳥
“飛天”是日本學者長廣敏雄在1949年提出的概念,較形象,在民間廣傳,但學術界一直有爭議。
“飛天”源自印度佛教,但梵文中從無專稱。
長廣敏雄認為是乾闥婆和緊那羅,乾闥婆又稱香音神,善彈奏,不食酒肉,喝百花香露,佛說法時,便出現在天空中。緊那羅名樂天,即天樂神,不能飛翔,後與妻子乾闥婆合為一體,成為“飛天”。(一說緊那羅也分男女,男生馬頭,女貌美)
此說最大缺陷是自造新說,佛經中只有“天人”之稱,長廣敏雄後來也常用“天人”代指“飛天”。
學者段文傑則認為,“飛天”就是“天人”,乾闥婆、緊那羅都在天龍八部(天眾、龍眾、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呼羅迦)中,在佛國世界裡有特殊職能,而“不是泛指六慾諸天和一切能飛的鬼神”。
隨著研究深入,學者們發現,“飛天”中還有夜叉,但不論乾闥婆、緊那羅還是夜叉,可能共有一個源頭——迦陵頻伽。
迦陵頻伽又稱妙音鳥,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鳥,身體似仙鶴,兩腿修長,雙翅,面如菩薩。《妙法蓮華經》中記為:“山川巖谷中,迦陵頻伽聲,命命等諸鳥,悉聞其音聲。”
迦陵頻伽很容易被古代中國人認可,在上古傳說中,常有人鳥結合的“羽人”的身影,他們常在西王母左右。漢代“羽人”造像發達,已頗有“飛天”的韻味。
由此看來,鳥崇拜是打通中西、“飛天”舶入的關鍵。
古人為什麼崇拜“羽人”
“羽人”傳說至少在商代已出現,最早的文字記錄出自屈原的《遠遊》:“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意思是要去飛仙居住的丹丘,留在這不死的仙鄉。古人較少看到鳥類死亡,以為長了羽毛就永生,漢代王逸曾說:“人得道,身出毛羽,可長生不死。”
《山海經》中有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先民常以鳥羽制冠和服飾。李澤厚先生提出,“美”字本意即戴長羽,而非“羊大為美”。在薩滿傳統中,巫師戴大羽冠,道家或出於薩滿,所以稱成仙為“羽化登升”。
從漢代起,“羽人”形象大量出現在刻石上,嬉戲類佔比甚高,分六搏、百戲、戲獸三種。六博是賭博性質的棋類遊戲;百戲又稱“角抵”,近似今天的雜技,有二人持械對練,也有登杆、走大繩、倒立、馬術等;戲獸多是鳳凰、麒麟等瑞獸,也有九尾狐、四尾翼虎等異獸。
漢代商業發達,人們對信仰符號的要求不再苛刻,更重視有趣。“羽人”也從傳統的追問生死、超越紅塵,轉向吃喝玩樂、招貓逗狗。漢代之前,“羽人”都有鳥嘴,到了漢代,鳥嘴成了鷹鉤鼻,翅膀也萎縮了。這可能有實際操作的原因:鳥嘴、翅膀屬開放造型,廢料且易折。到後來,為了省事,連羽毛都不刻了。
沒翅膀,人神全靠幻覺溝通,曹植見宓妃即如此,為了表現幻覺,到顧愷之畫《洛神賦圖》時,只好畫上雲彩、水,表示進入仙境,開中國畫雲水法的先河。
楊衒之最早提到“飛天”
傳說64年(一說是59年),漢明帝(東漢第二位皇帝)夜夢身高六丈、頭頂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來,博士傅毅稱此即是佛,漢明帝遂派蔡愔、秦景等十餘人出使西域,在大月氏遇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將他們請到中國傳教,佛教正式進入中原。(民間傳播可能更早)
隨著佛教傳播,“飛天”也逐漸進入中原。
最早提到“飛天”一詞的,是南北朝楊衒之,他在《洛陽伽藍記》中寫道:“飛天伎樂,望之雲表。”
據《廣弘明集》記:“(楊衒之)見寺宇壯麗捐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認為《洛陽伽藍記》反佛。但也有文獻稱楊衒之是居士,《居士分燈錄》中說:“餘觀楊衒之,不過一俗漢。而才參達摩,便爾悲喜交並,何見性成佛入斯之易也。”
《洛陽伽藍記》常被後人用作史料,所以各方都想將楊衒之收入己方。楊對佛教的認識不太深入,對“飛天”的觀察也比較模糊。
“飛天”不是完全抄襲自佛教,也帶有道教痕跡。
比如敦煌壁畫中,“飛天”與飛仙並存。“飛天”頭後有圓光,無雲彩,成群密集在一起;飛仙頭後無圓光,空間遼闊,且有云。
一些觀眾看了《洛神水賦》後,認為張冠李戴,將“飛天”和洛神宓妃混為一談。這就忽略了,中原“飛天”與印度“飛天”區別明顯:後者重寫實,造型豐滿、性感,男女成對出現,充滿豔情意味。
中原“飛天”則迥異,它與雲水法一脈相通。
“飛天”開始減肥
“飛天”的主體是舶來的,但也不只是受古印度文化影響。
以“飛天”頭後的圓光為例,它來自古希臘。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大軍的後裔在今阿富汗等地駐紮,形成貴族階層,並在數百年間掌控著當地政治、文化等。古希臘文明與古印度文明交匯,形成犍陀羅文明。一方面,古希臘哲學與早期佛教相結合,從小乘走向大乘,更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將古希臘造型藝術帶到東方。
犍陀羅地處中原與中亞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早期傳入中原的佛經都來自犍陀羅,用犍陀羅文寫成,而非梵文。犍陀羅文明將印度“飛天”的肥膩造型改造得更健美,且主題更多元,而不是隻有愛情。
沿著絲綢之路,犍陀羅改造後的“飛天”傳入龜茲。龜茲是當時西域三十六國中最強者,後附東漢,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併入大唐。龜茲篤信佛教,“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
龜茲是“飛天”造型突變的關鍵點,從龜茲石窟可見,“飛天”的造型已與敦煌壁畫近似,惟高鼻深目,穿印度服裝,披帛。此外,不再是一男一女,而是男女合體。
龜茲“飛天”傳入中原後,中原匠人進一步加以改造:將圓臉改成尖臉,面帶笑容,鼻子更挺拔,嘴也變小了。上身仍多裸露,保留了健美的姿態,但由肥碩轉向纖細,下肢則變長,飛翔姿態也開始多樣化。
為何至今讓人感動
對比隋唐“飛天”造型和漢代畫像磚,會發現二者驚人相似。
據學者謝生保《敦煌飛天形體姿態的來源》分析,敦煌“飛天”中大量採用漢代百戲的造型,比如單臂倒立、倒立頂杆、馬上倒立、爬竿、柳肩倒立(一人按另一人肩倒立)等。
一些“飛天”動作與游泳有關,比如仰泳式、自由泳式、潛水式、渡水式。可見,《洛神水賦》將“飛天”放在水中,並不違反傳統。
除了這些之外,“飛天”中還有武術式、翻騰式、雁落式、蹲距式等。
如此豐富的姿勢,體現出東西方不同的審美習慣。中國傳統繪畫自古不強調時間、空間、地點、形狀等,造型可穿越時空,關鍵看如何與自然融為一體。我國最早的繪畫理論家、南北朝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曾提出六法,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氣韻生動”,從而將顧愷之的“傳神說”精密化,後人稱讚說“六法精論,萬古不移”。
英國學者李約瑟曾說:“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時,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的宇宙哲學。”
換言之,古代中國人視繪畫為有生命的、高度複雜的行為,不論採用哪種技術,只有呈現出物件的複雜性,才算成功。這種複雜物不是堆砌的,而是鮮活、可對話的。中國式“飛天”造型複雜,充滿韻律感,以傳達超越、自由的感受。這種感受來自觀賞者內心的最大公約數,即意象。
所謂意象,就是寓意之象,透過客觀之物,觸動人們心靈。所以,雖相隔千年,現代手段複製出的“飛天”仍能讓網友們感動。
吸收了三大文明養分
唐朝是“飛天”藝術發展的最高峰,隨著唐朝由盛而衰,晚唐“飛天”造型飽含憂鬱與淒涼,體現出當時人們內心中的焦慮。到五代、宋時,“飛天”藝術走向衰落。
一方面,從唐代末期起,隨著西夏等崛起,中原與中亞文明的溝通被遮斷,以致後人幾乎忘掉了絲綢之路。加上宋代外患不斷,塑造了孤芳自賞、顧影自憐的時代文化。知識階層沉浸在對傳統文化的留戀中,漸失大氣。唐人推崇豔麗的牡丹,宋人則讚美低調、簡樸卻含香氣的梅花。其結果是,宋人喪失了對“飛天”藝術進一步創新的激情,使它漸漸淪為一種裝飾圖案。
另一方面,隨著理學興起,成為宋代主流價值觀,佛教文化的衝擊力減弱。在禮教思想審視下,“飛天”的創造空間越來越小,到了元代,已成“神仙可有情緣在,手掉芙蓉欲贈誰”,已無藝術生命力。
“飛天”的興衰可證兩點:
首先,只有主動學習外來文化,主動繼承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才能創造出讓後人感到自豪的、自己的傳統。
其次,只有拿來是不夠的,還要創造、創新。敦煌“飛天”既不是印度“飛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國“羽人”的傳承,它吸收了古印度、古希臘、古中國三大文明的養分,所以特別自信和輝煌。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全球化時代,堪稱至理。(責編:沈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