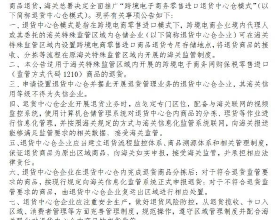來源:拾遺
不得“好死”——這可能是現在最被我們忽略的幸福難題。
中國各大城市在陸續釋出幸福指數。
但這些釋出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質量”也是幸福指數的核心指標。
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後,釋出了《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報告: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科技發展到今天,醫生面對最大的問題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這可能是現在最被我們忽略的幸福難題。
0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搶救後,終於保住生命。但鼻子裡從此插上了胃管。
進食透過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裡。
胃管至少兩個月就得換一次,“長長的管子從鼻子裡直通到胃,每次換管子時他都被嗆得滿臉通紅。
長期插管,嘴合不攏,巴金下巴脫了臼。只好把氣管切開,用呼吸機維持呼吸。
巴金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可是他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因為家屬和領導都不同意。
每一個愛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著,哪怕是靠呼吸機,但只要機器上顯示還有心跳就好……
就這樣,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說: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02
“不要再開刀了,開一個,死一個。”
原上海瑞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常務理事朱正綱,2015年起,開始四處去“攔刀”。
他在不同學術場合央求醫生們說,“不要輕易給晚期胃癌患者開刀。”
現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醫院,首選就是開刀,然後再進行化療放療。
“就是先把大山(腫瘤主體)搬掉,再用化療放療把周圍小土塊清理掉。”這種治療觀念已深植於全國大小醫院,“其實開刀不但沒用,還會起反作用。
晚期腫瘤擴散廣,轉移灶往往開不乾淨,結果在手術打擊之下,腫瘤自帶的免疫系統受到刺激,導致它們啟動更強烈的反撲,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術後幾乎都活不過一年。”
而現在歐美髮達國家很多都採用“轉化治療”,對晚期腫瘤患者一般不採取切除手術,而是儘量把病灶控制好,讓其縮小或慢擴散。
因為動手術不但會讓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餘下日子都將在病床上度過,幾乎沒有任何生活質量可言。
所以,朱正綱現在更願稱自己是“腫瘤醫生”,外科醫生關注的是這次開刀漂不漂亮,腫瘤醫生則關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這有本質的區別。”
03
美國是癌症治療水平最高的國家,當美國醫生自己面對癌症侵襲時,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和選擇的呢?
201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穆尤睿,發表了一篇轟動美國的文章——《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幾年前,我的導師查理,經手術探查證實患了胰腺癌。
負責給他做手術的醫生是美國頂級專家,但查理卻絲毫不為之所動。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沒邁進醫院一步。
他用最少的藥物和治療來控制病情,然後將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後的時光上,餘下的日子過得非常快樂。
穆尤睿發現,其實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國醫生遭遇絕症後都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他們選擇的不是最昂貴的藥和最先進的手術,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
他們在人生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東開一刀,西開一刀,身上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後,被掛在維持生命的機器上……
這是連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
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醫生同事跟我說過:如果有一天我也變成這樣,請你殺了我。
一個人失去意識後被送進急診室,通常情況下家屬會變得無所適從。
當醫生詢問“是否採取搶救措施”時,家屬們往往會立馬說:“是。”於是患者的噩夢開始了。
為了避免這種噩夢的發生,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這樣“被活著”,除了痛苦,毫無意義。
04
羅點點發起成立“臨終不插管”俱樂部時,完全沒想到它會變成自己後半生的事業。
羅點點是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有一次,她和一群醫生朋友聚會時,談起人生最後的路。
大家一致認為:“要死得漂亮點兒,不那麼難堪;不希望在ICU,赤條條的,插滿管子,像臺吞幣機器一樣,每天吞下幾千元,最後‘工業化’地死去。”
十幾個老人便發起成立了“臨終不插管”俱樂部。
隨後不久,羅點點在網上看到一份名為“五個願望”的英文檔案。
“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援生命醫療系統。”
“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
“我想讓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麼。”
“我希望讓誰幫助我。”
這是一份叫作“生前預囑”的美國法律檔案,它允許人們在健康清醒時刻透過簡單問答,自主決定自己臨終時的所有事務,諸如要不要心臟復甦、要不要插氣管等等。
羅點點開始意識到:“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
於是她攜手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創辦了中國首個提倡“尊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
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讓患者自然有尊嚴地離開人世,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陳小魯一直後悔沒有幫父親有尊嚴地離開。
陳老帥病重到最後,已基本沒有知覺。氣管切開沒法說話,全身插滿了管子,就是靠呼吸機、打強心針來維持生命。父親心跳停止時,電擊讓他從床上彈起來,非常痛苦……
陳小魯問:“能不能不搶救了?”
醫生說:“你說了算嗎?你們敢嗎?”
當時,陳小魯沉默了,他不敢做這個決定。“這成了我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情。”
開國上將張愛萍的夫人李又蘭,瞭解羅點點和陳小魯倡導的“尊嚴死”後,欣然填寫了生前預囑,申明放棄臨終搶救:
今後如當我病情危及生命時,千萬不要用生命支援療法搶救,如插各種管子及心肺功能啟動等,必要時可給予安眠、止痛,讓我安詳、自然、無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蘭病重入院,家屬和醫生謹遵其生前預囑,沒有進行過度地創傷性搶救,李又蘭昏迷半日後飄然仙逝,身體完好而又神色安寧,家人傷痛之餘也頗感欣慰。
“李又蘭阿姨是被生前預囑幫到的第一人。”羅點點很感動。
05
經濟學人釋出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何謂死亡質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後生活質量。
英國為什麼會這麼高呢?當面對不可逆轉、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的是緩和治療。
何謂緩和治療?
就是當一個人身患絕症,任何治療都無法阻止這一過程時,便採取緩和療法來減緩病痛症狀,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讓生命的最後一程走得完滿有尊嚴。
緩和醫療有三條核心原則:
1. 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2. 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3. 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英國建立了不少緩和醫療機構或病房,當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經無法治癒時,緩和醫療的人性化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
這時,醫生除了“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症狀的辦法”外,還會向患者家屬提出多項建議和要求:
1. 要多抽時間陪病人度過最後時刻。
2. 要讓病人說出希望在什麼地方離世。
3. 聽病人談人生,記錄他們的音容笑貌。
4. 協助病人彌補人生的種種遺憾。
5. 幫他們回顧人生,肯定他們過去的成就。
肝癌晚期老太太維多利亞問:“我可以去旅遊嗎?”
醫生亨利回答:“當然可以啊!”於是維多利亞便去了嚮往已久的地方。
06
中國的死亡質量為什麼這麼低呢?
1. 一是治療不足:生病了缺錢就醫,只有苦苦等死。
2. 二是過度治療: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在接受創傷性治療。
尤其是後者,最讓人遭罪。
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劉端祺,從醫40年至少經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錢不要緊,你一定要把人救回來。”“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會遭遇這樣的請求。
他點著頭,但心裡卻在感嘆:“這樣的搶救其實有什麼意義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後時刻,劉端祺經常聽到各種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現在才琢磨過來,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癒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
還有病人說:“就像電視劇,每一集演完,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知道,儘管主角很想活,但還是死了。”
病人不但受盡了罪,還花了很多冤枉錢。資料顯示,中國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了最後的無效治療上。
有時,劉端祺會直接對癌症晚期病人說:“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
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病床換上新床單,人離世了。
整個醫院,劉端祺最不願去的就是ICU,儘管那裡陳設著最先進的裝置。
“在那裡,我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花那麼多錢、受那麼多罪,難道就是為了插滿管子死在ICU病房嗎?
07
穆尤睿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的文章會在美國造成如此大的影響。
這篇文章讓許多美國人開始反思:“我該選擇怎樣的死亡方式?”
美國人約翰遜看完這篇文章後,立即給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電話:“現在才知道,對於臨終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適當的過度治療。不要再搶救了,讓老人家安靜離開吧!”
太太最終同意了這個建議。
第二天,老人安詳地離開了人間。
這件事,也讓約翰遜自己深受啟發:“我先把自己對待死亡的態度寫下來。將來若是神智清楚,就算這是座右銘;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這個算作遺囑。”
於是,約翰遜寫下了三條“生前預囑”:
如果遇上絕症,生活品質遠遠高於延長生命。我更願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親人,多回憶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沒做的事儘量做一些。
遇到天災人禍,而醫生回天乏術時,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搶救。
沒有生病時,珍惜健康,珍惜親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隨後,約翰遜撥通電話,向穆尤睿徵求意見。穆尤睿回答:“這是最好的死亡處方。”
當我們無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時,是像約翰遜一樣追求死亡質量,還是用機器來維持毫無質量的植物狀態?
英國人大多選擇了前者,中國人大多選擇了後者。
08
這是上海“麗莎大夫”講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說普通,是因為這樣的事每天都在各大醫院發生——一個80歲老人,因為腦出血入院。
家屬說:“不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活著!”
4個鐘頭的全力搶救後,他活了下來。
不過氣管被切開,喉部被打了個洞,那裡有一根粗長的管子連向呼吸機。
偶爾,他清醒過來,痛苦地睜開眼。
這時候,他的家屬就會格外激動,拉著我的手說:“謝謝你們拯救了他。”
家人輪流晝夜陪護他,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上的數字,每看到一點變化,就會立即跑來找我。
後來,他腫了起來,頭部像是吹大的氣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氣道出血不止,
這使他需要更加頻繁地清理氣道。
每次抽吸時,護士用一根長管伸進他的鼻腔。
只見血塊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來。
這個過程很痛苦,只見他皺著眉,拼命地想躲開伸進去的管子。
每當這時,他孫女總低著頭,不敢去看。可每天反覆地清理,卻還能抽吸出很多。
我問家屬:“拖下去還是放棄?”而他們,仍表示要堅持到底。
孫女說:“他死了,我就沒有爺爺了。”
治療越來越無奈,他清醒的時間更短了。而僅剩的清醒時間,也被抽吸、扎針無情地佔據。
他的死期將至,我心裡如白紙黑字般明晰。便對他孫女說:“你在床頭放點薰衣草吧。”
她連聲說:“好。我們不懂,聽你的。”
第二天查房,只覺芳香撲鼻。他的枕邊,躺著一大束薰衣草。他靜靜地躺著,神情柔和了許多。十天後,他死了。
他死的時候,膚色變成了半透明,針眼、插管遍佈全身。面部水腫,已經不見原來模樣。
如果他能表達,他願意要這十天嗎?這十天裡,他沒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權力,生命的意義何在?讓一個人這樣多活十天,就證明我們很愛很愛他嗎?我們的愛,就這樣膚淺嗎?
09
2005年,80出頭的學者齊邦媛,離開老屋住進了“養生村”,在那裡完成了記述家族歷史的《巨流河》。
《巨流河》出版後好評如潮,獲得多個獎項。
但時光無法阻止老去的齊邦媛,她感覺“疲憊已淹至胸口”。
一天,作家簡媜去看望齊邦媛。
兩個人的對話,漸漸談到死亡。
“我希望我死去時,是個讀書人的樣子。”
最後一刻仍然書卷在手,
最後一刻仍有“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優雅,
最後一刻眉宇間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潔淨,
以“讀書人的樣子”死去,這是齊邦媛對自己的期許。
你呢?
如果你是絕症患者,當死亡不可避免地來臨時,你期待以什麼樣的方式告別人世?
如果你是絕症患者家屬,你期待家人以什麼樣的方式告別人世?
不久前,浙江大學醫學院博士陳作兵,得知父親身患惡性腫瘤晚期後,沒有選擇讓父親在醫院進行放療化療,而是決定讓父親安享最後的人生——和親友告別,回到出生、長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種地的鄉親聊天。
他度過了最後一個幸福的春節,吃了最後一次團圓飯,7菜1湯。
他給孩子們包的紅包從50元變成了200元,還拍了一張又一張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最後,父親帶著安詳的微笑走了。
父親走了,陳作兵手機卻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責和謾罵我不孝。”面對謾罵、質疑,陳作兵說:“如果時光重來,我還會這麼做。”
尼采說:“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我們,至今還沒學會如何“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