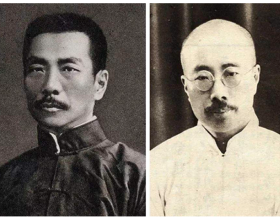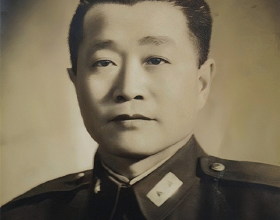加繆先生,是沒有晚年的那類作家,如菲茨傑拉德,抑或卡波蒂。但他又遭遇了“意外”,像巴特出了車禍,福柯患了病。對偉大藝術家而言,死於盛年,是不幸,也是運氣——加繆逃脫了“晚期風格”。從那標緻外形,到作品面貌,都未見一絲衰弱氣。他的迷人(姿勢、衣著和動作),與作品如同套裝,上面標記著“名士氣”三個字。不與權貴為伍,越名教而任自然,雖貧而貴。我甚至突發奇想,為他找到一個綽號——“法國嵇康”。
新近出版的《郭宏安譯加繆文集》(由《反與正 婚禮集 夏天集》《局外人 西緒福斯神話》《墮落 流放與王國》《加繆筆記 1935-1959》《陽光與陰影的交織 郭宏安讀加繆》五本書構成),讓我重新整體地思考這位法國作家。
正反合一:“加繆式辯證法”
加繆的創作有無“總體性”,其寫作奧秘又是什麼?這問題關乎寫作思維模式、心理機制,將是作品的奠基。它藏匿散佈在小說、散文、戲劇和筆記中。我想那是一套“加繆式辯證法”,把對立的兩極要素,轉化同一。《反與正》是作家的首部散文集(寫於22歲),書名或許預示了貫穿始終的創作思維。在貧窮和光明交織的世界,處理兩種對立的危險:怨恨和滿足。它們甚至化為作家的持久意象——陽光下的苦難。“苦難使我不能認為陽光下和歷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陽光告訴我歷史並不就是一切。”
20歲出頭的加繆,將異質性和同一性,用得如此圓熟,令人歎服。他日後的更多作品,幾乎都延續了兩分法的對立統一,悖謬式的兩難無解。這也是深度之源。他總能洞悉反面與反題。“對我來說,最大的奢侈從來就是與某種匱乏相聯絡的。”這得益於家庭:“他們幾乎什麼都缺,卻幾乎什麼也不羨慕。這個家庭甚至不識字,它以沉默、謹慎、自然而樸素的驕傲給了我最高的教誨。”在巴黎的浮華里,他總感到疏遠中的憐憫。這到底是敏感還是矯情?這是難得的理解力,總有透視帷幕、看到後臺的目光。
以正反同一、矛盾同源的思路,或許更能理解加繆的底部邏輯。《西緒福斯神話》永遠把絕望和希望同構,像二進位制一樣交替,歸零和重寫,如同鐘擺,是人生永遠的橫盤。加繆筆記提供了參照註解:“人的歷史是神話的歷史,人用歷史覆蓋了這個事實。兩個世紀以來,傳統神話的消失扭曲了歷史,因為死亡變得沒有希望。然而,如果不能接受這種沒有希望的死亡,就沒有人類的真相。”
“有些地方,精神死了,是為了誕生一種恰成它之否定的真實。”《局外人》中的冷漠兒子,那只是表徵。道德判斷在文學中將是表象,正如不能以流淚作為悲痛的指標。“在我身上,我所說的慈悲還是叫冷漠為好。”有理由相信,小說移置了加繆本人經驗,“父親啊!我曾經瘋狂地尋找我不曾有過的父親,而現在我發現了我一直有的東西,我的母親和她的沉默。”
拼圖、註解與對照記
《加繆筆記》對於讀者意味著什麼?這類似你問一個收藏家,官窯殘片有何價值。碎落的標本,能夠對勘鑑定完整器。筆記與作品,亦是這種對照。它“照見”意圖動機,自剖檢視,是創作運思的秘密。其迷人處,如同內衣,雖非外穿,卻深藏丘壑。它必然聯動日常與藝術,是關於思想生活的速寫。筆記,最雜燴的文體,也最私密。加繆的六個筆記本,融匯創作提綱、素材片斷、日記遊記、隨感評論。它足以顯示覆數化的加繆“面孔”(哲學的,倫理的及文藝批評的)。即興捕獲,靈光一閃,甚至心血來潮。加繆和他的精神導師尼采一樣,熟諳筆記體魅力——短促、有力、含混,充滿隱喻。
它也延續了尼采的關切,甚至在情緒上,亦是如此。反抗絕望、強力意志、偉大的健康,對怨恨妒忌(弱者無力)不屑一顧。加繆奉行強者情感,一切情緒都是正向性的。“那是與愚人孜孜以求的利益的一種輕微的距離,總是使我避免了怨恨之心……我的作為人的激情從來就不是‘反對’。我的激情總是向著比我好或者比我偉大的人。”筆記表明,他厭倦在文章中攻擊論戰,正因其只欣賞值得崇敬之人。
《筆記》應視為無數主題與“觀念整合”,作品像是對筆記的創造與賦形。如同油畫傑作誕生前的素描小稿,很多抽象觀點,成為散文和小說的延伸原點。兩者是雙聲,是協奏。所謂復調對話,首先應包孕自我獨白。“我最喜歡的十個詞,答案:世界,痛苦,土地,母親,人,荒原,榮譽,貧窮,夏天,大海。”如果可以繼續新增,我可以補上:沉默,冷漠,孤獨,寂靜。身處巴黎權貴圈,卻充滿異己感,作家心靈如同自我流放。
小說集《流放與王國》,都能在《筆記》裡找到原始設計——孤獨者們的遠離塵囂。《約拿》是藝術家困境的寓言,就像伍爾夫自己的房間。畫家在閣樓上逃避人情所累和創作衰竭。《不貞的妻子》中女人只有逃離丈夫,精神出離,在寂靜夜晚才能找到價值。《來客》裡主人公不願轉交囚徒,這事關榮譽。他於荒原放逐囚徒,提供“自由選擇”的處境。“天空和寂靜,我牢牢地抓住了它們的詩意:清醒,冷漠,乃是絕望或美的真正的象徵。”
作家之前提:成為藝術家
無論散文還是筆記,加繆都常以藝術家自謂。它強調藝術家乃是作家的前提與本質。在瑞典演說中,他再次談及藝術家與時代,以及藝術職責。這完全可視為雙關,潛藏著對薩特介入文學的辯駁,對存在主義標籤的不滿。“我們正經歷著一個不甘寂寞的時代,無論如何,它不允許我們對這個時代漠不關心……在這一片喧囂之中,作家再也不能希望置身局外繼續其心愛的沉思和想象了。”“在這裡我認為捲入比介入更恰當。實際上,對藝術家來說,問題不在於一種自願的介入,確切地說,是一種義務兵役。”
後果是,藝術逐漸失去了悠然與神聖自由。不應要求文學提供現成的解決方案,“好聽的道德教訓”。作家區分了倫理性道德和藝術性道德,前者是社會性規約,後者是藝術性自律——“我從來也不能放棄光明、生之幸福和我於其中成長的自由的生活。”他認為作家首先要懂生活的藝術,其後才是文學;首先要懂現世的歡愉,其次才是永恆;首先要懂身體的美學,之後再談靈魂。“因為我關心活著的人的命運,而不是靜觀永世長存的天空。”
其散文也確實印證出一個生活藝術家、感官主義者的精神肖像,他更像是伊壁鳩魯的門徒。“我知道我對死亡的恐懼源於我的生之嫉妒……我善妒,因為我太愛生命,不能不自私。永恆與我何干。”《婚禮集》重思了青春、衰老與死亡,它們都歸於生命的激情,不計未來的耗費。“青春沒有幻想。它沒有時間、也沒有虔敬的心情構築幻想”。《阿爾及爾的夏天》潛藏著作家的藝術倫理,阿爾及爾乃是精神溯源地。那裡除了過量豐富的自然,一無所有。它不提供教訓,只呈現感官快樂。阿爾及爾拒絕了“神話、文學、倫理學和宗教,有的只是石頭、肉體、星星和手可以觸控到的真實的東西”。這也暗示,藝術思維本質上是野性思維。藝術家要相信實在、詩意和自然,不應成為一堆社會學科的附庸和配菜。
加繆雖家境不佳,卻不以為意。這或許由於他很早就習得陽光下的苦難,貧窮中的享樂。這源於阿爾及爾的基因——健康的快樂(不是蒼白缺血的文雅),希臘式的傲慢天真,“不是建造生命,是燃燒生命。”“我認為在整個阿爾及利亞道德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詞。並非這些人沒有原則。人們有他的道德,一種非常獨特的道德。”它叫做街頭倫理,“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公正的倫理。”
筆記和作品,構成意義的連續體。作家對批評與論戰的無限厭倦,也內在性地說明沉默、冷漠與孤獨,為何對加繆如此重要。這並非意味著作家滑向了唯美主義。他曾評價,王爾德想將藝術置於一切之上。“但是藝術的崇高不是在一切之上飛翔。相反,它要與一切相結合。”事實上,加繆在除錯個體與集體、個人與時代的距離,描摹一種審美共同體——在孤獨寂靜中找尋共情力與匯聚感。“藝術並不是一種獨自的享樂。它是透過給予最大多數人以共同的苦樂的特殊的形象來使之受到感動的一種方式。”藝術家必須走出離群索居,只有承認歸於眾人的現實,才能保有藝術的個性營養。
“正是在他與別人之間的不斷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脫離的集體的途中,藝術家成熟起來了。”這種論述看上去是黑格爾式的,充滿了揚棄、折返和上升歷程。加繆也確實拿哲學境界來要求藝術職責——為真理和自由服務。正如羅蒂所言的“團結與反諷”,加繆認為藝術要團結儘可能多的人,抵抗“謊言和奴役”,這是兩個重要承諾。
批評線上
加繆與薩特的分歧之處
薩特在回答加繆的信中說:“您可能貧窮過,但您已不窮了,您是個資產者,和讓松一樣,和我一樣。”這句話說得過於輕鬆了。加繆和薩特不一樣,就以貧富論,薩特終其一生不知錢為何物,因為他極少有缺錢的時候,而加繆直到獲得了諾貝爾獎才最終擺脫了貧困。與錢有關的還有他們極不相同的童年,薩特是在作為語言學者的祖父的關懷下長大的,包圍著他的是書籍,餵養著他的是詞語,誘惑著他的是寫作;而加繆是在兇暴的外婆的棍子下長大的,他面對的是一個不知道如何疼愛他的寡言的母親,甚至連一張寫字的桌子都沒有,有的只是不用花錢買的陽光和大海。薩特可以進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可以去德國研究現象學,可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問政治;而加繆只能半工半讀地念阿爾及爾大學,早早地投身於反對社會不公的鬥爭。在抵抗運動中,薩特只是個初出茅廬的新手,但已經有了政治上的興趣;而加繆卻是《戰鬥報》的領導人,多少有資格對薩特的抗德功勞報以一笑。薩特一輩子都在巴黎的左派知識分子中間活動,他自然可以“斷定資產者都是壞蛋”,但是這並不說明他對無產者有什麼瞭解;而加繆卻始終和巴黎知識界格格不入,畢生跟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及巴黎的印刷工人保持著友誼。
薩特的哲學來源於思辨,而加繆的哲學來源於生活,因此,薩特可以論證“存在先於本質”“原始謀劃”“自由選擇”和“人命定是自由的”等等,結果是否定人性的存在,排除選擇的價值判斷,完全的責任變成了完全的無責任;而加繆則只是描述荒誕和探討如何走出荒誕,描述反抗和探討如何避免反抗的失度,結果是要人們“義無反顧地生活”,堅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
薩特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去也沒有現在的人,他被投向這個世界,他只受到未來的吸引,因此他只能選擇成為歷史的工具;而加繆的人是西緒福斯式的人,是普羅米修斯式的人,他“感覺到他的生活、他的反抗、他的自由,而且要盡其可能”。薩特只是冷眼地觀察,對人和他的世界都是悲觀的,加繆是熱烈地擁抱,對人從不悲觀,悲觀的只是人的世界。所以一個說“人首先是他主觀上感受到的那個謀劃”,而“他人是地獄”;另一個則說“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我的王國在這世界上”。薩特想要創造歷史,而加繆想要創造生活,拒絕使人成為歷史的工具。
——郭宏安:《阿爾貝·加繆》,原載《陽光與陰影的交織——郭宏安讀加繆》,譯林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