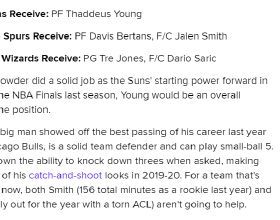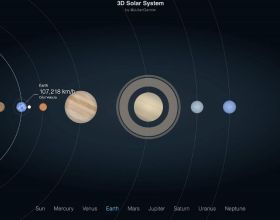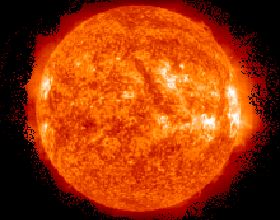咸豐朝妥協派是在國內階級矛盾和中外民族矛盾同時激化的情況下,部分統治集團成員形成的一個以挽救清朝統治為目的、以改變閉關觀念和放棄部分中國權益為條件、聯合西方列強共同鎮壓農民起義的政治派別。
這個派別在閉關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時代裡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定社會因素和複雜歷史背景的。所謂社會因素主要指鴉片戰爭後日益發展的買辦勢力以及與之互相滲透的一些東南地方官。買辦與地方官結合,形成了最初的對外妥協勢力。
鴉片戰爭之前,買辦是清政府監督控制下的中外貿易中介商。其人數、貿易品種、數量等都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鴉片戰爭後,不平等的條約為買辦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中方貿易的一些限制被強行取消。買辦人數隨著五口外商紛紛湧入而與日劇增。1850年閩浙總督劉韻珂曾說:“五口夷目夷商所用華人,難以數計。”買辦的經濟實力也在依附列強的商業活動中迅速膨脹。從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買辦透過中外貿易所獲利潤達白銀350餘萬兩。買辦發家後又往往自辦商業,其收入也十分可觀,他們成為當時社會上最大的暴發戶。買辦們的經濟利益決定了他們與傳統閉關觀念截然不同的對外思想,即:敞開國門,擴大中外貿易,以便賺取更多的利潤。
馬克思指出:“資本並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種以物品為媒介而成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買辦們經濟上的發跡必然會反映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去,與社會各階層發生新關係。買辦勢力一經形成,就產生了向清政權滲透的趨向。產生這種趨向的原因有四點:
第一,中國當時城鄉中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各地區間十分封閉,買辦們必須得到一定社會地位才便於打通層層官府,保住既得利益,拓展貿易領域。
第二,買辦大部分出身卑賤,不是科場失敗者便是小本生意人,這在當時重農抑商傳統觀念濃厚的中國社會遭人輕視。為了出人頭地,買辦們都以攫得一官半職為榮。早期買辦吳健彰、楊坊、徐潤、唐廷樞等人都曾不惜重金購得官職。
第三,買辦們可以從所獲官職中直接獲取經濟利益。例如曾任上海道海關監督的旗昌洋行買辦吳健彰,在1854年遭貶,其罪責中就有:“名為捐資,實取償於關稅”;“有廣東貨船到滬,因系該道舊識,免其納稅,約銀四萬兩”;“該道於關稅多少,任意祥報,其隱匿銀兩悉由海道運回原籍。”買辦官僚的損公肥私可見一斑。
第四,鴉片戰爭後,社會動盪,農民起義在南方漸趨擴大買辦們經營起來的家業面臨著被農民起義摧毀的威脅,所以他們一方面主動接近清政權以尋求武力庇護;另一方面出錢出力加強清政權建設。當太平天國起義後,僅以上海一隅的買辦紳商為例,除每年向清政府提供約二百萬兩白銀做為軍餉之外,還直接參與鎮壓起義的活動。
由於上述原因,在對外關係立場上與清統治集團大相徑庭的買辦勢力卻日趨接近清政權,為其觀念滲入統治集團、進而分化這個集團奠定了基礎。
清朝統治者對買辦的態度如何呢?
五口通商後,湧入中國的外國人日益增多,涉外事件顯著增加。清統治者對這些有礙體面的“夷務”一籌莫展。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道光皇帝曾想利用買辦的特殊地位與外國人交涉,力圖控制外國勢力在華髮展。1845年他令兩廣總督:“不拘資格,即行升調”那些“洞悉夷情、深通韜略”的人。咸豐登基後也想利用買辦達到使“外夷就範”的政治目的。但事與願違,皇帝們不但未能如願,反而為買辦勢力迅速與東南一些地方官結合提供了條件。
東南一些地方官在與買辦接觸中,日趨信任和依靠他們其主要原因:
一是,買辦勢力在東南地區經濟中所處的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他們經濟實力增長不但影響著進出口貿易,而且成為華商的投資者也間接影響著內地貿易。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只有海關與常關貿易收入穩定,是清政府救急的重要來源。買辦是海關、常關收入過程中重要一環,因此以上繳糧餉多少為主要政績的東南地方官不得不對買辦另眼看待。另一方面,買辦紳商是東南地區捐輸、捐納的主要承擔者。如前所述,他們沽名釣譽所出的大量白銀成為地方財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此外,買辦紳商在沿海鴉片走私貿易中要用數量可觀的白銀賄賂各級的地方官,這筆財物在地方官額外收入中佔有重要地位。
二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原因。五口通商後,西方列強為了擴大在華權益,經常利用一些特殊事件擴大事態、挑起武裝衝突,以迫使清政府作出讓步。“青浦事件″“泥城之戰都是這類事件。東南地方官為了緩解衝突,維護所轄地區,只好求助於與列強有關係的買辦出面協調中外關係。僅以“青浦事件”中買辦吳健彰升遷一事便可說明問題。1848年3月,3名英國傳教士在上海附近的青浦與當地漕勇發生鬥毆,英駐滬領事阿禮國藉機擴大事態,在提出各種無理要求的同時令英艦“奇爾得號”封鎖吳淞口,切斷南北海運。江蘇巡撫陸建瀛忙派買辦吳健彰前去調解,滿足了英方慾望。事後吳健彰便取代了原上海道臺鹹齡。
買辦勢力要發展離不開地方官的幫助,地方官要維持地方穩定以便向上爬也離不開買辦勢力的支援。雙方在越來越密切的合作中,買辦觀念便逐漸滲入一些地方官頭腦中,改變了他們原有的閉關觀念。買辦勢力與地方官結合形成新的社會因素就象出現在清政府“肌體”上的一個異化“細胞”,這種細胞一遇適宜環境就會迅速擴散。農民起義和列強給清政府的壓力正是該“細胞”發展的適宜環境。
以咸豐皇帝為首的清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是握有實權的對外強硬派。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給了強硬派掌握的中央財政集權體制和戰爭機器以毀滅性打擊。
從經濟上看:1851年至1853年為鎮壓農民起義清政府所耗費戶部“奏撥軍餉及各省截留各籌解多至二千九百六十三萬兩”,這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3/4。由於收支不平衡,咸豐年間戶部存銀僅相當道光年間的1/5。為鎮壓農民起義,咸豐皇帝不得不令各地“以本省錢糧,作為本省之軍需。”此後,清政府協、解餉制度發生重大變化,財政大權逐漸落入地方,強硬派再也無法像以往那樣控制全國經濟了。
從軍事上看,在南方擔負著鎮壓太平天國主要任務的清軍南、北大營分別於1858年和1860年被太平軍徹底摧毀,十幾萬清軍先後被殲,強硬派能控制的南方機動軍事力量喪失殆盡。1860年,英法聯軍為使強硬派徹底屈服,調集數萬軍隊、百餘艘戰船第三次北上大沽海口,在大沽至北京一線擊敗了以僧格林沁為主帥的十餘萬北方清軍主力。至此,以咸豐皇帝為首的強硬派在全國的主要軍事支柱都已失去,實力一落千丈。
強硬派由強到弱的過程恰好是妥協勢力由弱到強的過程。妥協勢力不失時機地抓住強硬派每個弱點、每次失利,迅速填補思想和權力真空,他們經歷了先地方後中央的發展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