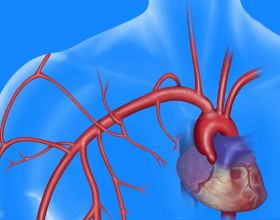冥冥中,很多人很多物很多事,總會在不經意間被撞見。有的普普通通,遇見不久歸於平淡;有的出乎意料,遇見一次終生不忘。
突然加班
你在哪裡?在老家;你在哪裡?正聚餐;你在哪裡?超市買菜;你在哪裡?剛到親戚家。問答的人,一個是單位的李院長,一個是我。只要是休息時間,遇見她的電話,第一句是“你在哪裡”,獲知人沒出平邑和費縣界,第二句就是“抓緊回來加班”。
這種聲音上的遇見,從偶爾變得越來越頻繁,甚至發展到逢休息必遇見的程度。這種遇見是疲累、無奈卻無法拒絕的,但不管正在幹什麼,終究逢“遇”必“見”。暫停手頭一切,驅車或小跑,趕緊回單位。
一架豆角
上下班,出門閒逛,總要在巷子中的一處宅院外經過。院子的主人,殺羊賣肉是主業。有時買的羊多,就圈養在那處宅院中。家中的一層層羊糞,成了宅院的累贅。僱人鏟走,開支不少。宅院的主人就想到了種植蔬菜。
在宅院外,那家主人圍起一塊菜畦,寬不過兩米,長約十米。在那窄菜畦裡,我見過油菜苗,見過菠菜苗,可能是蔬菜本身高度的問題,我的視線沒被這麼震撼過。這次,與我的視線迎面相撞的,是一架豆角。豆角的秧子並不算太旺盛,近半米長的豆角齊刷刷懸掛在綠秧上,凸出在綠葉外。青綠泛白的豆角,就這樣陪伴著紅磚牆,以讓人很難相信的存在,洗刷著注視它的眼睛。
莊稼,在城鎮的街巷中照樣可以存活,而且可以像在農村莊稼地裡一樣,活得精神飽滿,活得情趣盎然。“人勤地不懶”這句言語中說的,才是關鍵。看上去,菜畦的主人得七十多歲了,無論早晚冷熱,只要他覺得該侍弄了,就到菜畦旁忙活。有時是扶苗,有時是撒糞,有時是鬆土。匆匆經過的我,遇見許多次。
中午即將下班時,突然接到母親電話,那邊非常著急,說“順順找不到了”。一句話炸過來,比身邊落了炮彈還令人震驚。遲鈍了幾秒,我撒腿就往家跑。一邊跑一邊接電話一邊脫隔離衣,跑到醫院門口才把隔離衣脫下來。
小兒子熙順剛兩歲四個月,是那種特別淘且行動敏捷的孩子,經常是眨眼就不見了。給他盛一碗飯的工夫,他就能跑出去幾十米。我家住的那處小巷,約一百多米,其間有條岔道。順著岔道往西二三十米,又是條小巷,小巷南通國道,北通鎮中心小學,小學前是條寬敞的柏油路。而從我家出來,順著小巷往北,也是那條柏油路。岔道西的小巷、柏油路和國道,過往車輛都多。一個沒大人照看的小不點兒在路上毫無規矩地亂跑,後果可想而知。不僅如此,母親那十萬火急的“找不到了”後果多嚴重,誰也不知道。母親沒結束通話電話,那邊傳來她問路人見沒見到一個小孩的聲音,我的心裡更毛了。
好在最後是虛驚一場,小傢伙被安全找到了。但找到他的位置,讓我們很不理解。他沒去超市,而是轉向去了鎮中心小學的方向。那個方向,他平時從不肯去。
單位正前方,正衝院門,是塊三角地。在我們這地方,對三角形的土地有些偏見,認為這地方不適合建住宅,也不適合建商鋪。三角地便成了小鎮的廣場。八角樓、左寶貴石像、紫藤蘿……除了地塊呈三角形,與別處的廣場大致相仿。
雨後散步,閒逛至廣場,眼前豁然開朗。之前的花壇,與樹木花草一起,被割韭菜般移除了,換之以幾個黃土堆。黃土堆上隨意安置了幾塊山岩,巖邊襯托上幾棵不足一米的針葉松,坡嶺的形態就這樣被嫁接到廣場上。原先那個大樹成片、樹蔭斑駁、夜晚黑漆漆的所在,沒有了樹的遮擋,顯得十分敞亮。
心中思量,三角地一直在變,又一直沒大變。以前,廣場中央有個圓形的人工噴泉,後來被拆掉了。年復一年,痕跡越來越淡,直到淡成跳廣場舞的處所。雨後散步遇上的,還是那處廣場。廣場三個邊上,依然有三條大路。改建廣場的資金,在其中一塊石頭上以書法字型雕刻了出處,是當地一家罐頭廠的名稱。但是,我留意的不是企業名稱,而是那句公益性質的廣告語:有罐頭的地方,就有地方的罐頭。我們這處小鎮,叫地方鎮。
粉豆子花,是農村老家的叫法,這種花應該叫紫茉莉。小時候,我們時常將這種花的黑色種子捻開。黑色種子比黃豆粒略小,只是更圓。種子外皮粗糙,有幾條略高的脊和許多黃米粒大的小疙瘩。捻開或砸破外殼,裡面露出的是雪白的粉面,看上去比麵粉更細膩也更潔白。
粉豆子花紫紅色的居多,也見過黃色的,還有白色的。花形像小喇叭,只是不大,也沒啥香味,我並不太喜歡它。
那次去超市,在超市西側路邊,有一小片紫茉莉正在盛開。紫紅色的花朵,與在別處見過的一樣,和小時候見過的也一樣,只是恰好碰到我心情好,領著孩子湊近觀瞧。那些紫紅色的花朵裡,有幾枝黃色的。紫紅與黃花的枝條間,是兩種花的過渡色,紫紅與黃色駁雜的顏色。細看,其中的幾朵竟然是一半紫紅一半金黃,十分少見。
那棵花,估計是紫紅色與黃花互相傳粉結出的種子長成的。小兒子沒啥耐心,吵嚷著要走。我只得心存敬畏,拍照留存,隨聲遠去。
生活中,幾乎時刻都有“遇見”。只是,每一種“遇見”,都是偶然中存必然,必然中又有偶然成分。細琢磨,似乎皆有因果。
來源: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