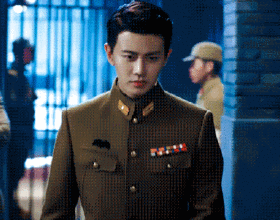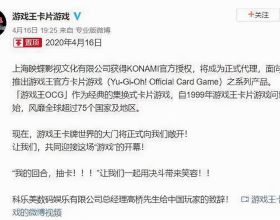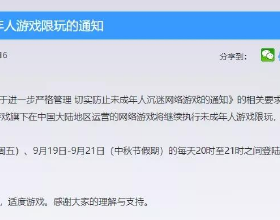“要是沒有天災的話,種糧食的收益,總體來講,還是很穩定的。”劉松是東北的種糧大戶。自從2013年成立合作社種植玉米以來,他除了2016年“玉米價格1元錢3斤(溼糧),沒有掙到錢”以外,基本上每年都有收益,一垧(15畝)地的淨收益,從最初的2000~3000元,近年隨著玉米價格上漲,能達到7000~8000元,最高甚至1萬元。
目前,劉松擔任黑龍江省綏化市北林區樺澤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該合作社種植糧食的面積達到1.05萬畝。其中,七成是土地流轉,三成是生產託管。這兩種模式,前者是為自己種地,最終收益歸合作社;後者是幫農戶種地,合作社收取一垧地5500元的託管費用,承擔從種到收的全部生產環節,最終收益歸農戶。
玉米、水稻、小麥,並稱三大主糧。以2016年這個標誌性時間節點為界,玉米與口糧(水稻、小麥)呈現不同運勢。這一年,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取消,代之以“市場化收購+補貼”新機制。從2004年起,尤其是在2008年下半年至2015年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的加持下,玉米價格氣勢長虹,走出了超過10年的牛市行情。2016年,玉米價格經過短暫調整,觸底後強勢反彈,尤其是2020年走勢陡峭,甚至超過小麥、水稻,也超過臨時收儲時期的保護價,創下歷史新高。至於口糧作物,雖然也有起伏,但走勢平穩整體向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逐漸興起壯大。玉米,或者準確來說糧食的“瘋狂”,除了體現在產量、進口量,包括價格,以及由價格延展開來的“囤糧客”外,還體現在種糧大戶流轉土地的面積上。儘管“大國小農”仍是中國的基本農情,但這樣的現實正伴隨土地規模化的演進,而悄然發生改變。
在不觸及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的前提下,農業的規模效應除了體現在土地流轉,還有生產託管為主的社會化服務。這背後既是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現實註腳,還是中央對於糧食安全的高度重視。比如,“越是有糧食吃,越要想到沒糧食的時候”“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決不能在吃飯這一基本生存問題上讓別人卡住我們的脖子”。
興起壯大的種糧大戶
從2009年開始,劉松就經營起了糧食貿易生意,在村子裡建起糧庫,收購玉米、水稻。直到2013年,他才開始介入產業鏈前端的種植環節。
當時的劉松,也有著自己的盤算:收購糧食每年只有冬天才有活幹,留不住人。再加上國家每年還有玉米臨儲收購政策,“只要能種出來,國家儲備庫就收”。這種方式既簡單直接,又有利可圖。於是,他立即著手成立合作社,“夏天種地、冬天收糧”。此舉也直接為合作社成員提供了就業機會,否則“青壯年勞動力就都走得差不多了”。
劉松所在合作社流轉土地的面積,從最初的100多畝,增長至如今的1萬多畝。短短7年時間,就實現了上百倍的增長。當然,短時間內如此大幅度的增長,也是符合市場理性的。
從投入成本來看,合作社在跟種子、化肥、農藥等農資供應商談判時,有著很強的議價能力,能夠儘可能地降低成本;同時,規模化種植以後,便於使用大型機械進行作業,以及由專業組織提供社會化服務,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實現糧食增產。
在銷售方面,玉米收穫集中上市後,價格相對較低,不著急賣糧的農戶,一般會先囤上幾個月,待來年糧價上漲之際再賣。當然,也有糧食貿易商會藉助“金主”提供的托盤資金,根據時機,選擇是否多囤一些。靠著做糧食貿易起家的劉松說:“這可比直接種地賣糧的收益好很多。”
土地規模化種植所帶來的收益,也吸引王漢返鄉創業。早在2011年,王漢就回到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創辦紅彤彤農業專業合作社,並擔任負責人。經過10年的發展壯大,包括今年剛流轉過來的8000多畝地,合作社旗下種植規模達到2萬畝。其中,託管當地種糧大戶土地約1.3萬畝。
王漢稱,當地農村勞動力流失嚴重,大部分人會選擇外出務工,把土地流轉出去,這為合作社進軍種植環節以及為種糧大戶提供託管服務提供了機會。再加上農機作業等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成熟,基本上所有的種糧大戶都採用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模式。“規模化種植以後,合作社可以開展小麥良種繁育推廣、優質專用小麥訂單生產,既能保障質量,同時又能增加收益。”
受多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影響,王漢2021年種地收益微薄。雖然前半年小麥產量、市場價格都很穩定,收益還可以。但到了後半年,玉米損失較為嚴重。靠著保險公司理賠,再加上種小麥的收益彌補,綜合算下來,每畝地只能掙100元左右。王漢稱,“自然災害是農業生產最大的變數,農業保險可謂是‘最後一道防線’。今年地方保險公司正在試點將租金、農資等成本也涵蓋在內,遭受自然災害損失後,保額將大為提高。要是將來大面積推廣的話,種糧就更有保障了。”
大規模種地超過10年的趙元俞,是山東省聊城市高唐縣的種糧大戶。2007年,他從規模種植棉花起步,頂峰時期棉花種植面積超過900畝。後來由於棉花收益不高,開始改種小麥、玉米。“以家庭農場形式(規模化)種地,收益還不錯。要不然也不會從500畝,壯大到5000多畝,2022年有可能超過1萬畝。”
在高唐縣當地,土地流轉率很高。雖然要求家庭農場“適度規模”,但如果運營能力跟得上的話,也支援流轉土地的規模擴大。趙元俞稱,之所以當地種糧大戶多,最主要還是種地能賺錢,尤其是2020年玉米價格上漲,大家都賺到錢了。同時,農業規模化的好處,還能夠有效抵禦市場風險。比如,2021年,農資價格上漲,仍能夠以相對合適的價格,買到高階產品。不過,2021年的玉米產量,要比往年差一些。他說,“往年玉米畝產量能達到1400斤以上,今年就只有1000多斤,這主要是受自然災害影響,往年10月份玉米就全部收穫,今年收穫期雨水多,到11月還收不完,玉米也受潮黴變,農戶直接就放棄了。”
劉松、王漢、趙元俞,是國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興起壯大的一個縮影。伴隨土地流轉面積的增長,土地規模化、集約化水平有明顯提升。根據2020年第7期《中國社會科學》刊發的《農民與土地漸行漸遠——土地流轉與“三權分置”制度實踐》一文,2017年,全國流轉到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耕地面積約佔同年全國流轉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32.53%,比2011年提高了10.76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社會化服務需求也日益上升。首輔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首席經濟學家陳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十九大報告中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應該是指合作經濟組織及其服務體系。合作經濟組織不僅是互助合作的載體,也是受託提供公共服務的最佳選擇,還可望成為農村社會治理的樞紐組織。
下一步是“大戶之間的競爭”
近些年,農村勞動力外流,僱工成本增加,再加上地租的大幅上漲,而糧食價格卻並非一路上漲,種糧大戶仍然面臨風險。
劉松直呼“沒有掙到錢”的2016年為例,玉米實行“市場化收購+補貼”後,價格出現過斷崖式下跌。這導致前一年種玉米的大戶,雖然豐收卻最終虧損,一年到頭“種了個寂寞”。
對於種糧大戶來說,農業種植的成本,主要包括地租、農資(種子、化肥、農藥等)、生產環節服務(機耕、機收、打藥、施肥等)。地租佔農業成本的大頭,達到40%左右。以玉米為例,東北地區地租漲幅最大。黑龍江的劉松稱,2013年最開始流轉土地,價格是一垧地4500元,2021年就到了1萬元。2022年,地價還不確定,可能得1.3萬~1.4萬元。山東的趙元俞稱,一畝地的租金從2019年800元,漲到2020年的900元,再到如今的1000~1200元。雖說合同是5年一簽,但租金還是隨行就市。
2021年以來,化肥價格持續上漲。據中國化工資訊中心資料,1~8月,國產尿素、國產磷酸二銨、氯化鉀和複合肥平均出廠價同比分別上漲31.4%、41.4%、23.2%和25.7%。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習銀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年的玉米價格,前者對普通農戶斤糧成本增加預計0.1元左右,後者為規模農戶斤糧成本增加預計0.2元以上。
事實上,近年來成本的快速增加,與種糧收益增加基本同步。布瑞克·農產品集購網研究總監林國發告訴第一財經,小農戶規模小,對成本增加的感受並不明顯,主要是種糧食的機會成本較高。
至於種糧大戶,林國發稱,他們勝在流轉土地規模大,即便每畝淨收益微薄,也有較為可觀的總收益。再說,雖然也會遭遇自然災害,一方面存在一定的機率,另一方面還有農業保險,再加上好年景時的收益彌補,總之有一定的抗風險能力。
對於地租上漲,趙元俞認為,“這是大勢所趨,已經降不下來了,除非退出種地。下一步就是大戶之間的競爭。這麼高的地租,要想掙到錢,必須加強管理,做到增產增效。稍微一疏忽,某個環節做不好,就有可能賠錢。”在王漢看來,“這也是合理的。雖然肯定會侵蝕種糧大戶的收益,但如果錢都讓大戶賺走了,小農戶沒有受益,也肯定不長久。地租上漲,要是能接受就付,要是覺得高,可以由其他人來種”。
與別人“每年種地之初直接付給農戶租金”不同的是,王漢採取了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合作社在每年6月1日前兌付租金。否則,老百姓有權收割小麥。“正常年份,當地小麥收割時間在6月5日左右。不管合作社經營好與壞,都會在此之前支付租金,打消老百姓、村委會、地方政府的顧慮。”
之所以形成這種模式,老百姓也願意接受,這背後是精明的現實考量。王漢解釋稱,如果在種地之初就給農戶付租金的話,按照今年流轉土地的規模,合作社得提前支付接近1000萬元。對老百姓來說,可能每家每戶也就到手2000~3000元,起不到關鍵作用。但是對合作社而言,由於小麥生長週期8個月,就相當於閒置了這筆資金,無形之中增加了財務成本。
最重要的是,每畝小麥的價值遠超租金。土地流轉的租金,一般是每畝700~800元,每畝小麥產量1000斤左右,國家最低收購價多年維持在每斤1.1元以上。在固鎮縣,早就形成了“一年兩季,收完小麥種玉米”的種植模式,從歷史來看,受地理和氣候因素影響,小麥非常穩產,極少有受災年份。再加上小麥、玉米屬於常規作物,質量好壞都能銷售掉,無非是“好的好價、差的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