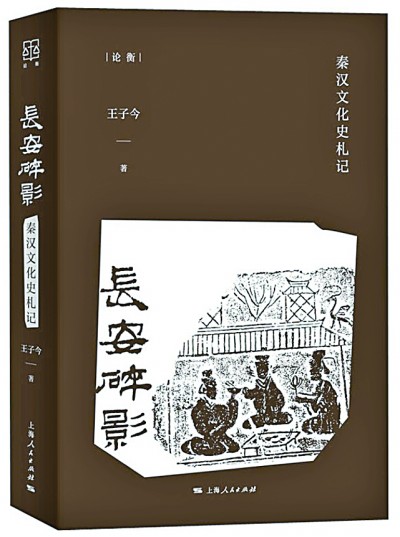茂陵出土的漢代“眾芳芬苾”瓦當。
王子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書者說】
上海人民出版社“論衡”書系推出不少好書,周振鶴《天行有常:周振鶴時評集》、王振中《從黃山白嶽到東亞海域:明清江南文化與域外世界》、譚徐鋒《察勢觀風: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郭永秉《金石有聲:文獻與文字斷想》等,都得到很多好評。2021年8月,兩種拙著《長安碎影:秦漢文化史札記》《上林繁葉:秦漢生態史叢書》得附驥尾,也有幸隨之面世。有朋友吩咐撰文,談一談《長安碎影》是如何勾勒“中國文化少年時期的情狀和精神風貌”的。受命援筆,說幾點想法。
此前我曾經出版過兩種隨筆集,《秦漢聞人肖像》和《秦漢文化風景》。落筆殺青前後,深知如果試圖透過一些零碎散漫的文字向讀者描繪一個偉大時代的文化風貌,無疑是妄想。但是從嚴肅的史學論著視角來看,儘管有若干種以秦漢為主題的鴻篇鉅製出版,我們對秦漢時期文化史的認識,其實還是片斷的、區域性的、淺薄的、不完整的。也許用看似碎小散亂但儘可能細緻生動的畫面,能夠讓讀者從不同視角比較真切地瞭解所關心的歷史文化物件。《長安碎影:秦漢文化史札記》用一“碎”字,與這樣的想法有關。
“方春”季節
漢代瓦當有“方春蕃萌”字樣。《秦漢文化風景》曾收入短文《方春蕃萌:秦漢文化的綠色意境》,從這一瓦文出發,討論了秦漢人愛護生態的開明理念以及秦漢人心境中的自然意趣,對秦漢文化風格也有所涉及。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魯迅對我們民族文化在當時表現出來的時代精神,有這樣的描述,或可概括為“豁達閎大之風”(《墳·看鏡有感》)。秦漢時期,是中國文化的“方春”季節,是中國文化的“少年”歲月。梁啟超《少年中國說》關於“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就曾經回顧“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
魯迅關注秦漢遺存,尤其重視漢畫,以為“頗可供參考”。他希望透過這些文化跡象求得“涵養”,實現“藝術”的“真切,深刻”。對於藝術創作,也曾明確建議“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魯迅是在書信中與對方討論“中國精神”時發表這樣的認識的。他讚賞“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沈雄大”,認為“倘取入”現代藝術,“或可另闢一境界也”。這樣的意見,是對“漢代”文化精彩內涵的深入體會。
“少年時代”
所謂“閎放”和“雄大”,其實既可以看作對秦漢社會文化風格的總結,也可以看作對當時我們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說明。而進取意識、務實態度、開放胸懷,也是這一時期社會文化的基本風格。
當時的人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比後來一些歷史階段的人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樸,更多的剛強。而我們國民性中為近代激進學者所深惡痛絕的虛偽與懦弱、曲折與陰暗,以及魯迅在記述兒童表情時用較和緩的文字所說的“拘謹,馴良”“精神萎靡”,似乎在秦漢時期還並沒有明顯的表現。如果追溯“我國民少年時代”,應當重視秦漢文化的考察。
李大釗在《“今”與“古”》(一)一文中介紹了“倍根”的說法,“他說我們稱為古代而那樣常與以崇敬者,乃為世界的少年時期”。又引“聖騷林”說:“古代的世界,是個只有少許的花的春”。
理解秦漢時期乃中國歷史“少年時代”和春天季節的意義,可以參考如下史論。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寫道,“(漢代)足以生國民宏大優美之思想”,“比而論之,其學術文藝,猶有千門萬戶之觀。”“自漢以降,則為我國文化中衰之時期。”“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翦伯贊《秦漢史》重視戰國以來“中原諸種族鼓其青春健壯的歷史活力,企圖擴充套件他們的天地”,而“四周諸種族向中原壓迫”的情形,以為歷史的合力,“造成了當時中國史的緊張性,並從而觸發了中國史的全面運動。”他把當時“中原”與“四周”的文化交匯比喻為“卵黃”和“卵白”,以為漢文化正如這種“血肉相連的”“有機構造”,在這一時期形成了。“當秦之時,中國的歷史,正在發生一種適當的溫度,來孵化這個雞卵。所以到西漢之初,雞雛遂破殼而出,是為漢族。”
“方春”季節、萬物“發榮滋長”、“適當的溫度”,使得秦漢新的文明“破殼而出”。秦漢的進步,借用李大釗《史學要論》中的話,正是“活的歷史”,“有他的永續的生命。”
秦漢人的“童心”
對於歷史的觀察和文化的理解,貴有“童心”。發現歷史人物的“童心”,也很重要。
《左傳》有“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之說。《史記》沿承了這一記載。《魯周公世家》:“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也是較早使用“童心”這一語彙的文獻。不過,《左傳》以批評的語氣言“童心”。《史記》卻沒有表現否定性傾向。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就司馬遷與漢武帝進行比較,注意到這兩位歷史名人的共同之處:“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所謂“幼稚”“天真”“好奇”“好幻想”,可以理解為“童心”的表現。也許漢武帝和司馬遷所生活的時代,有一種社會共同的“童心”。
在秦漢時期的歷史文化遺存中,可以看到若干長安人童年生活的生動畫面。
《長安碎影》中《童話“金屋藏嬌”》《漢代神童故事》《長安的“少年”和“惡少年”》幾篇,就未成年人生活這一文化主題有所討論。相關話題,在拙著《秦漢兒童的世界》《插圖秦漢兒童史》中已有探討,收入本書,希望筆調有所變換之後,能吸引更多讀者關注。上述文章,分別涉及宮廷制度、情感生活、文化教育、行政方式,以及更廣闊社會層面“少年”的表現。“惡少年”又稱為“悍少年”“暴桀子弟”“輕薄少年惡子”,其心理有臨近青春期的叛逆。“惡少年”“悍少年”的行為往往破壞都市治安,甚至成為“盜賊惡少年”。所謂“少年”“任俠”風習,也是遊俠的社會文化基礎。
長安碎影
集於《長安碎影》的34篇小文,正如一篇標題所說《咸陽——長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一些內容是講述“長安”地方在秦漢時期的文化優勝地位的。
若干故事,涉及秦孝公、商鞅、孟嘗君、燕太子丹、秦始皇、秦二世以及劉邦、項羽、賈誼、司馬遷等人物。其中《咸陽與郢的聯絡及“秦客公孫鞅”使楚》《孟嘗君在咸陽》,提示了透過文物研究新發現的歷史文化資訊。關於咸陽、長安的秦漢建築遺存,本書中有“冀闕”“秦城”“漢寢”等討論。《大漢奇華》一文,則評論了陝西出土漢代玉器及其研究。
《長安碎影》前有短序,說到書中《踏行秦始皇直道》一文的寫作緣起。這是我主編的“秦直道叢書”面世之後,發表於《光明日報》光明悅讀版的“著書者說”。秦始皇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紀念”。司馬遷行走直道,為我們留下的有關這一工程的真實記錄,是值得珍視的文獻遺存,而幾代學者的多次考察,也收穫了交通考古的成果。文中分析了早期史學有關帝制時代皇權與民心的理性判斷。一句“固輕百姓力矣”,使我們感受到史學家的批判精神。秦漢歷史“青春期”的粗暴兇殘等跡象,是司馬遷時代就有所指摘的。
序文中,回顧了1990年暑期我們西北大學考古專業77級四位同學徒步考察秦直道南段的情形。好友張在明有詩作:“最憶當年子午巔,熱血四人正青年。探秦反把秦皇罵,一吐塊壘震萬山。”在明的詩句,保留了我們當年考察記憶中印痕至深的畫面。隨後,筆者寫道:“感慨世態變幻,彈指一揮,時隔竟已21年。”後來幸得友人指出,“21年”實為“31年”。一錯竟然10年,老人著書,不免見事晚、智識淺,而又如此粗心,實在是太慚愧了。
(作者:王子今,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