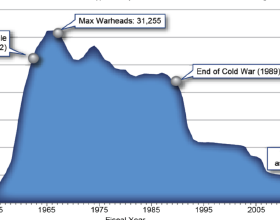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張穎,編輯:趙普通,原文標題:《一個場記的自我修養》,頭圖來自受訪者
電影是集體的藝術。每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都堅固地運轉,才讓大銀幕的光照到更遠的地方。
過去幾年,我們和電影從業者們走得很近,透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了電影行業鮮活生動的模樣。也曾經記錄過電影美術的故事 電影美術:銀幕落下無人喝彩,今後,還會有更多崗位裡更多的電影人被我們持續關注下去。希望下一次電影散場後,燈光亮起,字幕滾完,他們的名字會被你看到。
那麼,電影場記們的故事,開始了。
1場1鏡1次:入畫
“3,2,1,action!”
提到場記,最容易聯想到“打板”。每個場記入行基本都經歷過打場記板的歲月。
學體育的顏伊凡在專科畢業後,跟著朋友們“瞎混”過。在做網劇的朋友把他叫進組裡打板,雖然沒有經驗,但顏伊凡覺得這份工作好玩而且自由,就幹了起來。
做電影的場記是在2019年。顏伊凡進了院線電影《半個喜劇》的組,他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一個電影團隊的工作可以如此認真:前期籌備時,劇組就已經把戲排了四五遍,把存在的問題剪出來,然後重新調整;到了拍攝期間,每天收工後,導演組和演員都要把第二天的戲走一遍,反思、再創作。
“這種嚴謹的工作態度,讓我發現了創作型團隊的魅力。”顏伊凡說。在嚴格的劇組工作,也讓顏伊凡發生了一些變化:拍攝的每個鏡頭都要檢查一下,時刻關注著現場的陳設,不會的地方就一點點學。
當天的拍攝素材剪出來,如果有不接戲、穿幫的地方,他會覺得是自己工作的失職。“一開始肯定會犯錯,慢慢十天半個月就修正過來了。”正是因為要特別細心地對待這份工作,顏伊凡覺得自己幹成了一件事,這種感覺還不錯。
譚博是理科生,畢業後在煙臺的富士康做電子的研發支援,機箱的可靠性測試之類的工作和電影行業完全不沾邊。輾轉到武漢後,他一邊工作,一邊看了大量紀錄片,那段時間他從電影裡獲得了不一樣的感受,對這個社會的諸多現象,有了很多想說的話。
思考性和表達欲,也是很多人做電影的初衷,有了這個初心後,譚博參加了慄憲庭電影學習班,認識了《東北虎》的導演耿軍、《春江水暖》的導演顧曉剛等電影人。
“那時我很慚愧, 他們都有自己的作品和獨到之處,而我的創作力好像是不夠的。”譚博選擇從執行做起。
2016年初,他進了耿軍導演的《輕鬆+愉快》劇組,沒有從業經驗,就只能吃苦耐勞。站在什麼角度、怎麼打板,當時的譚博並不知道,只能透過上網、看書的方式學習。拍攝雖然不容易,但組裡的氛圍很好,他很喜歡耿軍的語言風格,“特別輕鬆愉快,就找到了做電影的樂趣。”
相比之下,學編導的劉婷婷已經算是科班出身了。原本在電視臺工作的她,因一次去橫店探班的偶然經歷,進到了劇組。“那時候也沒有正式入行,只是做一些類似編劇助理的文字工作,記錄他們開會要改什麼劇本。”劉婷婷說。
當時的她跟著拍了很多香港電影的場記師父,學著如何做一名場記。直到懷著一顆崇拜和學習的心,進入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劇組,劉婷婷找到了做這份工作的意義。
拍攝現場她看到袁和平和梁朝偉等主創,是如何熱情認真地對待電影,也發現王家衛導演的習慣是用他的獨白說話,“拍很多的畫面,配上他的獨白,但當時拍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這些鏡頭是幹什麼,直到呈現出來,驚歎原來還可以這樣!”劉婷婷提起那個時刻,還是感慨“特別神奇”。
而實實在在地參與過這樣的影片,她覺得就是值得的:“看到這部戲得了獎,想到這部片子我參與了,更有一種很神聖的感覺。”
外行身份,僅憑“喜歡”入場的他們並不知道,這份看似不起眼的工作,會讓自己投入得那麼多。
1場1鏡2次:困局
劉婷婷剛入行的時候,還是用膠片拍攝的年代。每個場記脖子上都掛著一塊秒錶,他們需要掐著秒看這一條拍了多長時間,算計膠片夠不夠用。
那個時候,她會在劇本上畫各種圖。人物A在左邊,B在右邊,A的左右手拿的東西分別是什麼……拍下一條的時候,物件要在它該在的位置,不能穿幫。
後來技術進步了,有了Qtake,現場每個人都能隨時分到訊號,手上拿著iPad,每一個部門都能監看畫面,連場記板也變成了電子的。場記的工作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打板的工作很多是攝影組的跟機員和打板人員來做。更多的時候,劉婷婷跟在導演身後,與各個部門溝通,來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不管技術怎麼進步,這份工作還是需要不斷學習。譚博在姜文導演的《邪不壓正》組時,為了更好地工作,甚至試著默寫劇本。“每場戲實際拍攝的時間是不一樣的,比如上一個鏡頭是在北京的影棚裡拍彭于晏跑出來,下一個鏡頭接的可能就是在雲南拍的戲了。”為了接戲的問題,要對劇本爛熟於心。
到了《烏海》拍攝期間,作為場記的譚博對於工作已經很嫻熟了,他知道現場該做什麼,哪些東西可以提前準備,“比在最初在耿軍導演那裡熟練了很多。”
不過和任何一份工作一樣,做得越久,能獲得的成就感閾值就越高,瓶頸期也就跟著來了。
做了五年場記,顏伊凡覺得該學的東西學到了,再幹下去好像“也就這樣了”。“因為從一開始可能就是好奇,覺得挺好玩的,然後是不服輸,想把它做好,做著做著,學著學著,好像都能勝任工作了,就想轉型了。”他說。
畢竟在很多人看來,場記是非常基礎的工作,但有了做場記的經驗來打底,很多人可以轉型做現場執行導演或者統籌。去年,顏伊凡嘗試做統籌助理,之後也打算慢慢地往統籌轉。
而譚博在上個月剛轉行,在一家品牌的廣告公司做專案經理。轉行的念頭,經常會在一個片子殺青和下一專案找來之間的空檔冒出來。在組裡的時候,譚博忙著工作,不太會想別的,而一旦殺青回到在北京的住所,“這個工作到底要不要堅持”的聲音就會反覆想起。
拍電影的工作,讓大家沒有辦法穩定下來。“在劇組裡工作的最基層的人,包括很年輕的小夥子們,都還處在一種漂泊的狀態。”譚博說。
更現實的層面是,場記的收入並不會隨著經驗積累而發生大的變化。一個專案拿到的錢平均到每個月,和普通上班族也差不了太多。一旦要考慮這些現實問題,很多因理想和熱愛而來的人,也不得不轉身離開了。
1場1鏡3次:重場戲
“你做了這麼多年的場記,有沒有想過轉做副導演、執行導演、統籌?”很多人問過劉婷婷這個問題,她當然想過,也嘗試過。
她發現那些工作自己也可以做,但直到今天,她依然是一名場記。“有一個前輩,已經六十多歲了,做了幾十年的場記,場記就是她的身份。”劉婷婷說,每部電影的幕後都有不同的職位,沒有誰比誰更高貴,在場記這個崗位上,如果能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對影片拍攝有所幫助,那就是成就。

細節決定了一個場記的上限。要記錄下能讓剪輯和DIT看得懂的東西,鏡頭和服化道、演員是不是連續,這些都不是簡單的工作。上一個全景鏡頭演員的衣服釦子是解開的,下一個近景演員因為冷把釦子扣上了,這樣的穿幫鏡頭,劉婷婷不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
“雖然現在各個部門,像道具組會盯自己的道具,服裝組會盯服裝的,但我還是要注意這些細節的東西。”對於這份工作,她很執著,甚至調侃自己太軸了。
有次在拍一個鏡頭時,攝影老師出於畫面好看的考慮,想把原本放下去的窗簾升上去,劉婷婷跑過去制止:“不行,剛那個鏡頭窗簾是下來的,現在升上去會穿幫。”然後去和導演協調,依照導演對鏡頭的要求來決定。
不管最後有沒有觀眾能注意到這一點,作為場記,這些細節就是劉婷婷的工作,能把每一個細節都做好,就是最好的場記。

當然,辛苦總是伴隨其中。在“女的當男的用,男的當牲口用”的電影劇組,工作強度經常大到身體上吃不消。拍《繡春刀2》的時候,劉婷婷連續熬了一個多月的通宵,拍完後神經衰弱,別人大聲叫她的名字會把她嚇到,殺青後在家躺了半個月不想動彈。
“拍《飛馳人生》的時候,在新疆無人區或者公路上,根本就沒有廁所,對女生太不友好了。”劉婷婷調侃自己現在已經養成了憋尿的習慣,“感覺腎不太好了。”
可是這些,都不能成為她放棄這份工作的理由:“我為什麼不能幹一輩子場記呢?”
小時候,劉婷婷很喜歡劉德華,在文具盒和書皮上貼滿了劉德華的貼紙。去年她進了饒曉志指導、劉德華主演的《人潮洶湧》劇組做場記,和她崇拜的華仔一起工作。在拍攝現場,她用自己的專業與劉德華溝通工作,這讓她覺得特別有成就感:“我平等地站在了偶像面前。”
電影上映後,劉婷婷去影院看完了片子,聽著周圍觀眾的討論,她覺得很驕傲。“雖然我不是導演也不是攝影指導,但我的名字出現在片尾字幕,我參與了這部電影。”
而離開電影,進入廣告公司的譚博,獲得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生活,並且意外地有了一些新的感受:電影是影像的藝術,廣告或許也可以。譚博發現自己過去幾年經常侷限在文藝片裡,也需要換個方式,開拓一下眼界,積累一些做廣告的創意。
“有點像緩兵之計。”譚博說,這些嘗試也許同樣能為他之後繼續做電影服務,“如果以後有我欣賞的導演、喜歡的片子找我,我還是會去的。”
電影製造了很多夢境,讓一些人能夠光鮮亮麗地站在大眾面前,接受關注和掌聲,但更多人,躲在了幕後,默默地守護著每一個鏡頭。
對於這些“螺絲釘”來說,他們堅守於此的原因卻非常簡單,如三位電影場記所言:熱愛大於一切。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張穎,編輯:趙普通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立場。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絡 [email protected]
正在改變與想要改變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