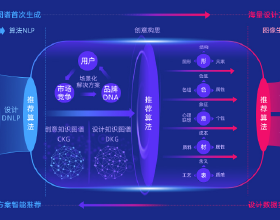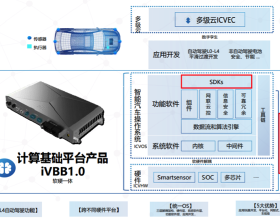文/朱雲漢*
把中國定位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有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衝動:不斷地找尋新的敵人。服務於總統的國家安全團隊把自己的任務界定為,找出各種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來源。政客喜歡找出敵對目標,因為打擊敵人可以轉移公眾對國內問題的關注;國防工業喜歡敵人,這可以讓他們賺更多的錢;政論家與媒體喜歡敵人,因為他們可以賣出更多的暢銷書,吸引更多的觀眾鎖定他們的新聞頻道。
一山不容二虎
從小布什上臺,到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推進全力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圍堵政策,中間相隔了17年,讓中國獲得了一個難得的和平發展歷史機遇期,在比較寬鬆的外部環境下提高自己的綜合國力,並初步建立自主科研生態體系。
過去30多年的快速全球化給美國帶來可觀的經濟紅利,也為美國的跨國企業提供了在全球市場擴張的巨大商機。尤其是中國躍升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平臺,讓美國許多跨國企業可以專營附加值最高的產品或生產環節,而把利潤微薄的製造環節轉給境外供應商代工。
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商品源源不斷地鋪滿美國零售商的貨架,亞洲的主要貿易伙伴用它們賺到的美元外匯大筆地購入美國政府債券,讓美國經濟可以長期在低通脹與低利率的軌道上執行,也讓美國的中低收入家庭與中產階級群體可以維持日常消費的實際購買力。
維護戰後美國主導的多邊國際經濟體制,符合美國跨國企業與金融集團的根本利益。所以奧巴馬時代不可能把拆解全球分工體系、裂解中美經濟依存關係這種兩敗俱傷的做法,作為戰略圍堵的招數。
2016年9月4日,出席G20杭州峰會的30多位國家領導人與國際組織負責人齊聚西湖畔,這是奧巴馬任內最後一次亞洲行。他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外交出擊,就是推動全球戰略再平衡與重返亞太,他一心想要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並集中精力來對付中國崛起的挑戰。中國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G20框架下的積極作為,完全超出了美國的預想。G20杭州峰會成為中國躍升為世界經濟與全球治理議題引領者角色的里程碑,在這場設定全球議題的重要峰會上美國反而成為配角。
奧巴馬任內在中國周邊部署戰略圍堵,給中國添了不少麻煩。奧巴馬的團隊在幕後挑起中國與菲律賓的南海領土爭端,並一手導演所謂南海國際仲裁案,但白忙活一場。2016年,新當選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將美國的勸阻置之腦後,主動與中國修補關係並重啟雙邊談判,擱置南海領土爭端。2015年,儘管華盛頓竭力阻止傳統盟國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卻讓自己落得個灰頭土臉。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不顧華盛頓反對,堅定不移地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韓國與澳大利亞也在截止日之前提出申請。所有美國盟邦中只剩下日本仍徘徊在亞投行門外。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目睹此情景不禁感嘆,這是美國失去國際經濟體最後責任承擔人地位的開始。
四重矛盾的疊加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釋出的購買力平價GDP排名,2014年中國的實體經濟規模首次超越美國,2016年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也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這兩個指標的歷史性跨越,讓美國首次感受到自己的霸權地位面臨挑戰。而美國國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就是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維護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獲益,絕不允許任何可能的挑戰者出現。這是激發美國對華戰略全面轉向的最根本原因。
從奧巴馬時代到特朗普時代,美國對華戰略進入一個戰略對抗迅速升級的通道。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中的鷹派充分利用了美國政治精英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心理,全面激化中美關係中的各種潛在矛盾,在媒體上大肆妖魔化中國,包括對美國的“科技竊取”與“政治滲透”,甚至啟動情報與司法機構,對美籍華人以及與中國有合作往來的機構和專業人士進行盤查,刻意製造一種麥卡錫時代的肅殺之氣。
在很短時間內,四重長期累積的矛盾全部被啟動與激化,構成強大的疑懼與敵視中國的政治能量,把中美關係帶入戰略對抗升級的軌道,雙方要在短期內妥協,和解與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未來要重新回到建設性交往的軌道,必須克服以下障礙。
第一層是美國社會內部矛盾的外部化。美國國內全球化受益者與受損者之間的分配矛盾已經累積到沸騰點,要找到外來威脅作為宣洩口。特朗普把受損者的挫折與不滿導向兩大替罪羊:中國與非法移民。
第二層是全球產業價值鏈龍頭地位之爭。如果中國甘於長期屈居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在核心技術領域長期依附處於頂端的美國,那麼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平臺,可以給美國帶來長期低通脹與低利率的紅利,談不上威脅。但現在中國在所有核心技術及新興科技領域尋求追趕與超越,這對仍想獨佔全球產業分工鰲頭的美國自然構成威脅。
第三層是國際領導地位之爭。中國並沒有直接挑戰美國霸權的戰略意圖,在地緣政治上構不成直接威脅。但美國的心態是“一山不容二虎”,決不容許自己失去對全球安全、科技、貿易、金融、貨幣體系的支配地位。美國深信強者必霸,當中國綜合國力正快速逼近美國時,美國自然難以容忍。
第四層是社會體制優勝劣敗之爭。過去主張“建設性交往”的美國外交精英,曾假設美國可以在全球化中引導中國向西方模式靠攏、將中國吸納進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但這個一廂情願的假設破滅了。中國展現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對篤信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優越性與普世性的西方精英來說,如芒刺在背。中國正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構建歐亞大陸為主體的國際合作模式,並與沿線國家分享自己的發展經驗;而美國自身的政治制度正面臨國內社會的嚴重撕裂,所以對中國帶來的體制層面的競爭坐立不安。美國的國家機器鉚足勁兒阻撓中國正常參與美國所主導的全球與區域的安全、貿易、科技和金融體系。美國不僅有強烈遏制中國之衝動,還有很大機率會不時採取不理性的做法。
這場戰略對峙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將是一場經濟韌性、政治耐力與整體心理承受能力的中長期較量,不會因為美國政府換屆或政黨輪替而在短期內消退。美國政治精英需要折騰5年或10年,才可能在付出相當的學費之後,開始調適基本心態與重新判斷形勢,接受中國是一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新興大國,也才可能重新認識到中美之間在許多全球與區域問題上尋求合作與妥協是唯一的務實選項。
這場戰略較量可能不至於演變成一場漫長的對抗。美國兩黨統治精英的底氣是不足的,他們長期被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忽視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真正需求,早已失去多數美國民眾的信任。隨著與中國戰略衝突的戰線拉長,他們將發現自己越來越難向美國民眾解釋:為何需要對一個遠在太平洋彼岸、對美國不構成生存威脅的國家,進行一場看不到盡頭且代價高昂的衝突。
準備面對一場百年衝突
就客觀而言,中國沒有爭奪全球霸主的野心,中美之間沒有領土爭議或歷史仇恨,中國對美國不構成直接的生存威脅。美國感受到的中國“威脅”,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適應與意識形態框架塑造的。何況中美都具有保證相互毀滅的核威懾力量,也有保證經濟相互重創的金融威懾。中美之間即使爆發僅動用傳統武器的區域性軍事衝突,也將觸發全球性金融災難,這是阻止中美走向全面軍事攤牌的重要因素。
儘管中美之間爆發全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極低,但是中美關係長期陷入“修昔底德難題”的可能性卻不能排除。就是說,雙方可能陷入一場類似美蘇之間的冷戰,讓世界經濟體系分割為兩個板塊,讓所有國家都難以適從。這場21世紀的“冷戰”,將不再以兩大集團軍備競賽與代理人戰爭為主軸,而是在貿易、產業、科技、金融、通訊網路與數字資產等領域爭奪龍頭地位,並在發展模式話語權、國際經濟規則、產業與技術標準、全球與區域多邊體制運作,以及國際公共產品提供等領域爭奪領導權。它與過去冷戰的相似之處就是“零和”思維,把自己的“所得”建立在對方“所失”之上,或是不在乎兩敗俱傷,只要能殺敵一萬,寧可自損八千。
2019年5月,中美貿易談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啟動極限施壓政策,擴大加徵懲罰性關稅,並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全面封殺華為。為遏制與圍堵中國,美國不惜犧牲短期經濟利益,也不在乎本國高科技產業的全球市場嚴重受損,把中美關係推上“新冷戰”的不歸路。特朗普不斷抬高貿易談判要價,意在讓談判受挫。他們所營造的“反中”與“防中”氛圍,在短時間內席捲美國政界與輿論界,壓制了各種基於務實或理性的意見,更讓國會兩黨要角與媒體評論人身不由己地附和他們的主張。
他們成功地激發了美國社會三種深層的恐懼情緒,因此這場經濟戰夾帶了極高的不理性成分。
一是害怕美國百年帝國基業的崩塌。國內製造業空洞化、政府與民間過度消費、不斷以債養債,再加上其在世界各地樹敵與積怨太多,全球軍事部署無法收斂,國力早已透支。這些結構性脆弱問題長期被掩蓋,主要是因為其霸權地位賦予它的各種特權(尤其是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華爾街作為全球金融體系龍頭)。支撐這些特權的基礎一旦鬆動,所有危機都會爆發。
二是源於自己的陰暗霸凌歷史、害怕冤冤相報。自從美國登上國際體系權力頂峰,不論是對其鄰國、盟邦,還是其他涉及利害關係的國家,美國經常利用其不對稱的權力關係欺負其交往對手。
三是基於種族偏見。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曾直截了當地指出,美國政治人物對中國的許多不公平指控,以及美國主流媒體妖魔化中國的傾向,都與他們對黃面板人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與偏見有關。不能排除西方人對“黃禍”的深層恐懼再次啟動,從而成為影響中美關係走向的不理性因素。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與美國政界重量級人物的互動中得出結論:“美國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政策統統開始把與中國全面敵對競爭作為核心原則。”一種新的思潮正瀰漫美國政策圈,將中美關係限定在零和衝突的框架裡。他明確指出:“美國對中國發起的攻擊是一場在錯誤的戰場上發起、以錯誤的方式進行的錯誤的戰爭。”他認為,中美關係原本雖然棘手但仍處於可控範圍內,但如今的風險在於,它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變為一場全盤衝突。他刻意用《中美即將進入百年衝突》這樣一個驚悚的標題,就是想喚醒美國朝野精英的理性思維,不可盲目地附和特朗普,繼續以錯誤的方式進行錯誤的戰爭。
客觀來說,美國社會內部對於與中國進行一場漫長的全面衝突,缺乏共識與思想準備。美國社會各個群體願意承受多大的代價來阻止中國正常參與全球經濟與推進自己的科技、產業和國防升級,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認真思考、評估與辯論過。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並沒有一套深思熟慮的戰略來進行長期抗戰,他們只是成功地鼓動了“反中”情緒。他們試圖讓美國選民相信,特朗普發起的對華貿易戰會讓中國臣服或損失慘重,而自己可以毫髮無損。然而很多企業則要求立刻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的懲罰性關稅,因為關稅是由美國公司支付,而不是中國。
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一廂情願地打算設下一道“鐵幕”,把中國隔離於全球經濟體系之外。但美國各界很快發現,這道“鐵幕”最後會罩在自己身上,卻無法阻擋其他絕大多數國家與中國進行正常貿易、投資合作與科技文化交流。
事實證明,發動貿易戰沒有讓特朗普在與民主黨的政治競賽中佔到任何便宜,反而導致許多群體遭受了實質性損失,尤其是仰賴中國廉價消費品的中低收入家庭;仰賴中國生產的裝置或零部件的美國廠商,也是叫苦連天。2018-2021年,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份額不減反增,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不減反增。最早從新冠危機中恢復的中國製造業,在全球供應鏈中彰顯了超強的韌性,迅速成為抗疫物資的全球最大供應來源。
2020年總統大選中險勝的拜登,在是否應該主動結束對華貿易戰的問題上,進退兩難。一方面,他的經濟智囊都認識到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是失敗的,尤其從2021年上半年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反覆發作,導致全球供應鏈緊張,各類原材料、商品以及運輸價格節節升高,取消對華額外關稅有助於舒緩通脹壓力。但是拜登的政治基礎相對脆弱,民主黨擔憂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可能被共和黨奪回多數席位。中美貿易戰在短期內仍將陷入僵局。
美國的有識之士遲早會領會到馬丁·沃爾夫的警告:“任何企圖阻攔中國經濟和技術崛起的嘗試幾乎肯定會遭遇失敗。更糟糕的是,它會引起中國人民深深的敵意。”橋水基金公司的創始人達利歐看得比較清楚,他提醒美國決策者,如果要運用手邊的籌碼使中國讓步妥協,“宜早不宜遲,因為時間站在中國這邊”。隨著中美戰略對抗的戰線拉長,這種暫時被壓制的務實意見將逐一湧現。所以,只要中國沉得住氣,見招拆招、適度反擊,但不主動升級這場衝突,不主動與美國經濟剝離,這場衝突肯定不會延續百年。
美國霸權的兩面性
在奧巴馬時代,美國霸權的兩面性隱而不顯,因為傳統上美國外交精英非常重視價值論述與道德外衣包裝,刻意掩飾其霸凌行徑的陰暗面。而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則毫不遮掩美國的超級大國“流氓行徑”,讓我們更容易認清美國霸權的真面目與其國際角色的兩面性。對美國霸權本質的理解應該從下列四個角度來檢視。
第一,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與公共產品的提供物件,並非真正全面開放、包容與一視同仁,而是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歧視性,以及基於文明種族優越感的等級秩序。在貨幣、金融、貿易與科技領域,與美國有戰略利益衝突的國家長期被排斥在外。
例如當歐洲戰事已經結束,美蘇對戰後歐洲秩序安排的分歧開始浮現時,杜魯門總統斷然中止了透過《租借法案》為蘇聯提供戰後重建所需長期融資承諾,於是蘇聯隨即放棄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創始會員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也長期被排除在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與世貿組織之外。
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有明確的階層秩序。與美國關係最緊密的盟國是“盎格魯-撒克遜”集團(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它們構成西方世界的核心,享有最高等級的軍事與情報合作關係。其次是由美國的歐陸盟國構成的第二層核心圈。然後才是日本、韓國、土耳其、沙特等第三層非西方國盟友。最後才是更外圍的依附者或順從者。親疏關係不同的國家,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內之地位、待遇與發言權一向是有明顯差別的。
第二,美國的國際領導角色,是它的意識形態與國內權力結構的延伸。戰後美國所願意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是根據它的主流社會精英的意識形態框架,以及國內強勢利益集團的需求,而非國際社會的實際需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崇尚大市場小政府,美國政府也傾向於將國際公共產品的範疇極小化,排斥各種可能限制跨國企業與跨國資本行動自由的國際規約或監管機制,甚至主動要求現有的國際機構(例如世界銀行)減縮其業務與功能。同時,美國扮演的國際領導角色最終也要符合國內強勢利益集團的需求,特別是軍工集團、華爾街、能源集團、醫療集團、高科技集團等的需求。例如,美國牽頭的TPP談判,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帶上談判桌的條文與鉅細無遺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國的跨國企業、跨國銀行僱用的紐約大律師事務所草擬的。這些大律師事務所刻意將提案的複雜規則與專有名詞之晦澀,連一般的商務仲裁法官都搞不懂。將來在執行規則條文時,如果出現爭議與糾紛,還是得找這些受僱於跨國企業的大律師來幫忙解釋,貿易糾紛打官司也是他們承攬,這些大律師兩頭通吃。
由於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治的框限,美國對現有全球治理機制不能應對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社會與生態危機等問題不予關心,也無法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包容性、可持續發展的需求。美國只對反恐、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攸關自身利益的領域有興趣,而在企業壟斷、金融系統性風險、租稅逃漏、科技變革的社會風險、疾病控制、糧食安全、移民權利保障、難民收容、氣候變化、海洋生態環境惡化、水資源稀缺等領域,美國對全球協作平臺不足或監管機制嚴重缺位的問題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美國推動制定的國際規則,主要用來約束其他國家,而放縱自己選擇性適用。它不時濫用霸權地位,公然破壞規則和秩序,並處處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以國家安全為藉口,以其國內法管轄權來凌駕國際規範,也就是惡名昭彰的“長臂司法管轄”。在國際關係領域喜歡強調,“自由國際秩序”的精髓是“以規則為基礎”。美國常將自身利益或國內政治需要凌駕於國際規則之上,不時丟擲“美國例外”論,肆意曲解國際規則,“自由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難以鞏固。例如,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按規則任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因長期國際收支失衡而要調整固定匯率,都必須與其他成員協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總統突然宣佈停止履行美元與黃金兌換承諾,事前完全沒有與其他成員協商,就一腳把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設計踢翻了。
最近幾年,在推進全球租稅正義的目標上,美國自私自利的做法也讓各國傷透腦筋。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拒絕簽署《共同申報準則》(CRS)的國家,成為這個全球打擊逃漏稅的國際新規約下的最大漏洞。
這是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因為最早啟動全球追繳漏稅的就是美國。2010年,美國通過了《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FATCA),俗稱“肥咖”條款。根據這個法案,美國要求外國金融機構(FFI)向美國國稅局(IRS)提供美國納稅人的賬戶資訊,以強迫美國公民和綠卡人士申報海外賬戶與海外所得,對於不配合的FFI,就其來源於美國的所得徵收30%的扣繳作為處罰。
美國利用FATCA給傳統的避稅天堂以沉重的打擊。包括瑞士、百慕大與開曼群島,在面臨失去進入美國金融體系的威脅下,被迫配合美國政府的要求,主動向IRS提供美國納稅人的賬戶資料,並嚴格審查有美國背景客戶的開戶資訊。美國又陸續與一百多個國家與地區,在FATCA框架下籤署雙邊資訊互換協定。在美國強勢推動FATCA的刺激下,歐洲各國政府也開始積極追查本國納稅人隱匿在海外避稅天堂的賬戶,讓傳統的避稅天堂遭遇第二波打擊。G20在2014年正式推出CRS,這套更完整而標準化的全球金融機構境外背景客戶賬戶資訊交換的國際規範,目的在於落實租稅正義,讓富人藏匿在國外的財富與投資收益無所遁形。從2016年開始,陸續有108個國家與地區簽署這項國際規約。中國也從2018年開始全面執行CRS規定,有義務將外籍人士在本地金融機構賬戶的基本資訊、總金額流動情況提供給國外稅務機構,中國政府也可以藉此掌握中國公民在國外金融機構賬戶的基本資訊。
自CRS2016年陸續上路以來,全球的富豪階層與他們的會計師,都忙著重新配置他們的資產並轉移他們的金融賬戶。這些千方百計想要隱匿財富的富豪,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一個新的避稅天堂,那就是美國。這是因為美國拒絕簽署CRS。美國給出的荒謬理由是,美國已經與絕大多數CRS簽署國之間有雙邊資訊互換協定。而美國要求其他國家鉅細無遺地提供美國納稅人的海外賬戶資料,但其他國家政府想要從美國金融機構拿到資料卻會面臨百般刁難。美國刻意讓自己成為CRS體系下的最大漏洞,這樣,它可以替代傳統的避稅天堂國家,吸引大量離岸財富湧向美國,既可讓美國財富管理相關服務業大發不義之財,又可鞏固美元地位。
從2015年到2017年,美國的金融機構與會計師都忙著將客戶的錢從傳統離岸避稅天堂(比如巴哈馬、瑞士、百慕大等),轉移到美國岸上天堂(比如特拉華州、內華達州、懷俄明州和南達科他州等)。2017年,美國離岸金融規模為全球第一,佔22.3%,而2015年時,美國佔比還僅為14%。
對於美國經常破壞規則的行徑,所有參與美國主導的多邊組織的會員國基本上都是儘量忍讓。西方國家選擇遷就與姑息,是因為它們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畢竟享有參與核心與分享決策權的特殊待遇。非西方國家更不願意挺身而出,因為可能有遭遇報復與孤立的風險。
第四,美國霸權兩面性最詭譎的悖論就是:它既是國際秩序的來源,也是國際體系不穩定的來源。西方主流學者說美國是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對美國也是國際公共之惡的主要來源卻避而不談。
美國把國家安全利益的邊界無限延伸,而不斷找尋潛在的敵人就是他們的利益所在。
(1)美國給世界製造的首要公共之惡,就是它對國家安全利益的極限追求,以及隨時可以以國家安全為藉口,踐踏文明底線,其結果就是給其他地區與國家制造各種更大更深的不安全。其最明顯的公共之惡之一就是:放任跨國金融機構在全球各地資本市場興風作浪,並不斷增加各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放任美國跨國企業在全球利用市場壟斷地位追求暴利。在華爾街利益集團驅動下,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強迫各國開啟資本市場,解除金融管制,還把金融管制全面鬆綁與“金融產品創新”模式推廣到全球,在全球各地製造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讓華爾街將有毒金融資產推銷給各國銀行與保險機構。不但美國爆發本土性金融危機,歐洲也被殃及,至今歐洲尚未從歐債危機中脫困。危機爆發前,歐洲的監管機構與金融機構都被美國華爾街洗了腦,購置大量美國機構發行並被美國三大信評機構評為“優質”的衍生金融資產。金融危機爆發後,歐洲人才發現這些金融產品都面臨違約風險,最後被迫打三折、兩折進行清算。
(2)美國在貿易談判時,強推偏頗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條款,維護美國跨國企業的暴利與市場壟斷地位,阻礙創新與知識分享;不斷要求延長美國藥廠的專利年限,讓它們能繼續以天價販賣這些製造成本極低且投資早已收回的專利藥品。美國佔據許多多邊機構的主導地位,長期阻撓這些機構承擔新的職責來應對新興全球議題,並阻礙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與新治理機制的創設。其次,讓許多領域的公共產品供給長期處於短缺狀態。
(3)美國長期提供劣等的公共產品。例如,對於網際網路域名的分配與管轄機制,或是長期壓制多邊組織對新興全球議題的研究與討論。
(4)以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缺失日益明顯。但美國為捍衛美元霸權,極力阻止特別提款權(SDR)逐步取得超主權貨幣功能,極力防範任何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如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歐元或其他貨幣結算。美國還長期拖延IMF認股權比例與投票權調整的方案。儘管發展中國家非常需要基礎設施長期融資,但美國不願意讓世界銀行與地區開發銀行擴充這個領域的融資機制,試圖阻撓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這也是製造公共之惡。這樣的例證不勝列舉。
美國退位是危機也是機遇
特朗普拋棄國際領導責任,甚至主動削弱與拆解現有多邊體制。現有的多邊體制面臨嚴重衝擊,WTO首當其衝,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可能分崩離析。全球化程序也可能受到嚴重干擾。
不過,危機也可能變為轉機,美國的“退位”也可能帶來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歷史契機。
特朗普的“超級流氓大國”行徑,迫使現有多邊體制內的所有利益攸關者必須挺身而出,維護多邊主義,維護基於開放、互惠、非歧視原則的國際規約。新興經濟體也被迫認真思考,如何在這個世界秩序震盪與重組的過程中扮演更積極與建設性的角色。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最大製造業基地,更是責無旁貸,必須挺身而出,為全球多邊主義體制提供關鍵支撐。
當前,人類正處於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如果放任資本主導,壟斷性數字資本主義將可能嚴重威脅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並阻斷資訊科技將人類帶往分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可能性。所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續性都存在嚴重缺陷,只是過去沒有任何新的動力有可能去轉換、改革或補充它。
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國已經開始戰略收縮,這正是修補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機制的契機。繼續搭建新的多邊合作平臺,並著手修正經濟全球化的遊戲規則,讓全球化的果實能創造更大的普惠效果。
(編輯 季節)
¨ 本文摘編自朱雲漢著《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一書,中信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朱雲漢,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顧問、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