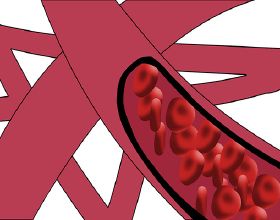我爸爸是一名農村的屠夫,從我記事起,每逢過年過節我爸爸就去給本村和鄰村殺豬,六、七十年代,農民飼養的豬是不可以隨便殺的,只有過年過節時,才以生產隊為單位分別向大隊、公社上報殺豬申請,大隊、公社依據生產隊人口多少批准殺豬的數量,當時豬肉的價格是一等豬肉每斤0.84元,二等豬肉每斤0.77元,劃分豬肉等級的依據是豬肉肥標(簡稱肥標)的厚度,那個年代人們都喜歡吃肥肉,肥肉標厚度達兩指以上為一等肉,肥肉標厚度低於兩指的為二等肉。農民除了年節殺豬,所飼養的生豬都得交售給國營食品站,生豬交售給食品站時重量必須要達到130斤以上,重量達到了豬太瘦也不要,達不到要求就得拉回家繼續餵養,那個年代也出現過個別農戶實在養不起了,可又不允許自宰賣肉,就動用歪門兒,打斷豬腿、推倒豬舍,製造意外現場,上報大隊和公社申請宰殺賣肉,公社派獸醫站的獸醫現場檢視,確認後給出據證明,方可持證明僱傭屠夫宰豬賣肉。農民把生豬交售給食品站時,首先由站裡的專人檢驗確定等級,然後稱重,食品站依據肥豬等級和重量結算兌付現金,除了支付現金外,還依據所售生豬的重量發給4至6斤的購肉票和一定數量的飼料票,食品站收購的生豬絕大部分調撥給各大城市肉聯場,本地食品站每天也殺一、兩頭豬並賣肉,老百姓憑購肉票購買,非農業戶按人口定期供應一定數量購肉票,農民不享受肉票供應,只能靠交售生豬獲取購肉票;飼料票與糧票有相似之處,可持票到糧站購買糧食,但是不同的是,飼料票只能買毛糧、粗糧如:玉米或高粱,而糧票購買的是成品糧,而且是粗細糧搭配;再說說農村屠夫殺豬賣肉的收費標準,屠戶殺一頭豬收取養豬戶1.5元錢,豬小腸(腸衣)白送給屠戶,然後屠夫把小腸賣給供銷社採購站,以質定價,每掛小腸最高價0.75元,最低4、5毛錢不等,也就是說屠夫殺豬賣肉一頭豬的總收入大約兩塊錢左右,我盼過年過節,盼爸爸多殺豬,每次殺豬收穫的豬腸都是由我去交售給供銷社採購站,一掛豬小腸重約2斤,有時一天殺5、6頭豬,小腸總重量就是10多斤,我把小腸裝在挎籃裡,送到距離我家4里路程的馬頭營供銷社採購站,那時我十一、二歲用手臂負重10多斤很吃力,路上需要歇幾歇。回到家把賣的錢全部交給爸爸(媽媽在我八歲時就病世了),爸爸接過錢把元以下的零頭錢給我作為獎勵,我就用於上學買文具。
屠夫有工商管理所頒發的執照,沒有執照是不允許殺豬的,每年的年末都必須到工商管理所換照,換照地點是距離我家十五里地的“新寨鎮工商管理所”,1970年的春節之前,到了換照的時間,我爸爸徒步去工商管理所換照,連續跑了三趟也沒有給辦理,據我爸爸回來講,工商所不想給爸爸換照了,原因是削減屠夫人數,可是在我村周邊方圓十幾裡共有四個大隊,在這四個大隊中包括我爸爸在內只有屠夫3人,其中有兩個大隊的殺豬活多年以來都是我爸爸完成,怎麼一下子就取消了我爸爸的屠戶執照呢?我爸爸是一個老實厚道人也不會爭辯,為此在家悶悶不樂,多少年來,殺豬收入是我家的主要經濟來源,我爸每年大約殺豬一百多頭,總收入就是200多元,在那個年代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這可是不小的數字呀!那年我12歲,看到爸爸愁眉苦臉、失魂落魄的樣子我也很著急,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吃過早飯後,我對爸爸說:“爸爸,你把準備辦執照的相片交給我,我去工商管理所給你辦執照。”爸爸說:“我去了三趟都沒有辦來,你去了就能行嗎?”我說:“讓我去試一試吧”。我執意要去,爸爸只好由著我了。
我出發了,冬季裡寒風刺骨,前兩天剛下了一場雪覆蓋了鄉間土路,一路上深一腳、淺一腳不知摔了多少個跟頭,終於到達了工商管理所的所在地新寨鎮,這是一個較大的集鎮,我是第一次來這裡,那天是大集,街道上有許多擺攤賣貨的人,經向人打聽,很快找到了工商管理所辦公地點,該工商管理所是一個單獨小院,朝東的外門掛著一個“新寨鎮工商管理所”的牌子,院內三間平房,門框上有一個木牌寫著“辦公室”三個字,我走進辦公室,看到裡邊有兩個年齡都在50歲開外的人,其中一個人看見我走進門問道“小孩兒你來幹什麼?”我回答:“我是閣樓坨公社石橋頭大隊屠夫李樹本的兒子,我是來給我爸爸辦殺豬執照的”。“你爸爸怎麼沒有來?為什麼讓你一個小孩來呀?”我說:“我爸爸已經來過三次了都沒有辦回去,我爸爸年歲大了又是老寒腿,走路困難,我就替他來了。”對方聽完我說的話把目光轉向室內另一個人,帶有爭求意見的口氣說:“所長,這小孩大老遠的來了也真不容易,你說咋辦?”對方回答:“是呀,你給他辦了吧。”那人從抽屜中拿去來一個空白執照,不大一會兒就寫好了,貼好相片遞給了我,我接過執照說了一聲“謝謝大叔”愉快的走出辦公室,就在我出門的一剎那聽到其中一個人說了一句“這種情況我們只能破例了”。我一刻不停的原路回家。
我回到家時已經是午飯以後了,我把辦好的執照交給了爸爸,爸爸拿著執照看了又看高興極了,還問了我辦照前後經過,聽完我的敘述,爸爸說:我的好兒子真行,餓了吧,飯在鍋裡熱著呢,爸爸給你端去。”在爸爸扭轉身之際,我看到了爸爸擦眼淚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