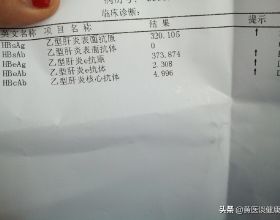原創:安超 縉雲優生活
李菊老人
與李菊老人的相識是在2020年春,初見她時有恍如隔世之感,她生於1914年,在解放前還生活了35年,她應該是縉雲縣還在世的最長壽老人。
她的記憶還很清晰,我問她是否清楚宮前村石板街和包公殿的歷史,她說始建於何時她也不清楚,但自她記事起這兩者就已經存在,她告訴我老一輩人稱包公殿為栵樹廟殿,上殿的十大閻王塑像很是可怖,她的母親每年都要去村邊的幾座廟宇裡上香,故而兒時的她對此印象十分深刻。
她的聽力也還行,能聽明白你附在她耳邊說的話。我讓她說說過去的往事,她就慢悠悠地跟我講起了她的人生。她的父親叫李玉庭,父親年少時是看(發“育”音)牛廝嘎,成年後就去做長年(長工),十幾歲就去富陽烤紙(造紙業),三十幾歲才成家。母親名叫蓮花,是管溪村人,母親會抽索麵。父親成家後家境好轉,買了田和屋,還養了幾頭豬,家裡人吃用無憂,她是家中的長女。
跟那時大部分的農村少女一樣,她沒有接受過教育,日常基本上都待在家裡,出門也是跟在父母身邊。“好男不當兵,好女不看(發“貌”音)燈”是農村的行為準則。她在17歲時,由父母安排,嫁給了五里牌村的呂澤高(小名賣囡),丈夫比他大4歲。
民國相較於清朝,社會風氣雖然有了很大改變,但婚姻大事基本還是延續父母之言媒妁之命。她在未出嫁前,對自己的夫家情況一無所知,即便是她的父母也未曾去過,這點確實有點反常。一貫的做法是,男方長輩會去女方家裡看新娘相貌,女方長輩會去男方家看家境,在成婚前,新郎新娘往往連對方長什麼模樣都不清楚。
一頂花轎將她送到了五里牌村,命運不曾給她以眷顧,她嫁的是一個清貧之家。丈夫還有個哥哥,已經成親,婆婆公公都還健朗,三個家庭蝸居在20餘平方的房子裡(這麼小的面積一戶人家都很寒酸)。螺螄殼裡做道場,婆婆棲身二樓(二樓低矮),靠兩腳木梯爬上爬下。一樓要安放兩張床(中間用布隔開),兩個灶臺。
說起來,她所嫁的夫家跟她還有親戚關係,她的婆婆是她母親的姑姑,但兩家人平常並不走動。五里牌村人很詫異地問她:你娘咋姑姑家都沒來過嗎?她家是沒屋住的呀!她回答道:沒來過,都是親眷,想著嫁到親戚家總不會受委屈。
公公是個很和氣的老人,在溪頭的太和堂裡坐診,到九十歲才過世。公公原有兄弟數人,長毛反(太平軍進入縉雲)時,村裡人都逃跑了。公公的大哥腿腳不便,對眾人說:我這麼個殘疾人,長毛應該也不會為難我,就留了下來。長毛來到村裡,把他吊起來,燒死在家裡,這件陳年往事是她的婆婆告訴她的。
她的老公呂澤樵讀過書(可能是初小),年輕時也去仙居挑鹽謀生,他日常吃得不多,力氣比別人要差點,所得也就很微薄。家裡租種了2畝田地(俗稱種田腳),種田、割稻都要找人幫忙。年成好的時候能夠按租賃時談好的比例交租谷。遇到年成不好,交不足約定數量稻穀的時候,割稻穀那天要把田主請到稻田,讓他坐在田坎上看著那丘田能收上來多少斤稻穀,使他明白確實是交不齊租谷,讓他酌情減少。遇到這種情況,按照鄉間的慣例,種田腳人(佃戶)在這天中午要燒一頓好吃的午飯供應給田主吃。
抗戰的時候,有個官太太逃難到了五里牌,她邀李菊一起去管溪村看房子,太太對她很好,很客氣。太太在管溪租好了房子,也住了段時間。抗戰勝利後,太太要回去了,問她願不願意讓丈夫去紹興的中國銀行任職。如何取捨,她心裡著實有點迷茫,為此她特意去問了村裡有名的鄉紳汝和太公。汝和太公提議讓她丈夫出去試試看,看他能不能吃得消。
在丈夫去紹興的年月裡,家裡、田裡的所有事情都壓在了她身上。家裡有3個小孩要照顧,田地裡的活也不能少,燒灰、種麥……原先不會得慢慢也就學會了。她丈夫在紹興也陸續寄錢回來,家裡的生活逐漸好轉,她也去購買了4塊田地,面積分別是80把、60把、30把、20把(80把為一畝),100把田買來本想豎屋,沒成想就解放了,丈夫也從紹興回到了壺鎮,在溪頭染布店裡做會計。
家裡生齒日繁,靠著丈夫的些許工資,日子過得很艱難。在飢餓的歲月裡,家裡的孩子割了村邊溪頭人田裡的麥苗煮了充飢。丈夫是個老實人,在染布店裡工作了十幾年,被人算計,說他貪汙,為此還賠了一筆錢。丈夫內心苦悶、鬱鬱寡歡,沒幾年就得了咽喉癌去世了,那一年是1974年。文革結束後,他的冤屈也得到平反,經濟上也做了補償。
在聊天過程中,我問了她關於1942年時期奮勇隊的事情,問她是否知曉。她卻跟我說起了1949年初,發生在五里牌村的一件大事。她的情緒很高,說她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天上午,村裡來了一群土匪。通往五里牌的村邊道路上來了數群人,都是來五里牌搶劫的。
她認出好多個都是周邊村莊的人,嶺背上、東山、管溪……家裡的被子、印花布、丈夫從紹興買回來給家人的衣服,只能眼睜睜看著被他們從家裡全部搶走。棉絮被給一個管溪人挑走,連給家裡老人置辦的壽衣也被搶走。村子裡有個人見勢不妙,逃到路邊的荊棘叢中躲起來,躲了一會,以為土匪已經離開,就探出頭來東張西望,結果被沿村搜尋的土匪一槍打死。
老人的家族都有長壽基因,她的兄弟姐妹基本都活到了八九十歲,她的晚年生活主要靠家中的兩位兒子、兒媳照料。我在2020年冬天時還去看望過她兩次,今年春天我數次去看她,卻見房門緊閉,鄰居說她去了孫子那裡。五月的時候我再去她家,鄰居告訴我老人已在四月仙遊。還記得上次告別時您說的“再會”,可惜今生終不復再見,寥寥數語,以作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