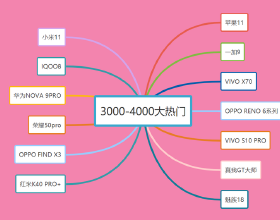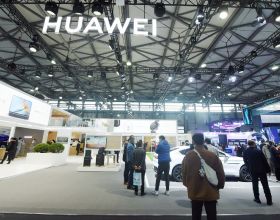大西馨大尉,原部隊番號為第四二野戰道路隊,以下是他的回憶錄:
軍官室建在土丘上,我吃著美味佳餚慢慢地喝著酒的時候,忽然看見窗外的山丘上有200多個男人向這邊走來。我想“一定是那幫傢伙來了”。仔細一看,他們都沒有戴帽子,穿著破爛不堪的衣服,一個個面黃肌瘦,有的扶著夥伴的肩膀搖搖晃晃地朝這邊走過來。即刻,我產生了一種危機的念頭:“這一些人能為我按時完成任務?"“哪裡?不是還有百來個農民的嗎?反正都得聽我的,殺他兩三個,也沒關係。”我想著,便不再憂慮。
這群男人是被俘虜的抗日軍,從5月份開始近半年的時間,在鈴木中隊那溼淋淋的地段修築道路。昨天軍司令官飯村中將誇獎了鈴木中尉“乾得很好”後,這些俘虜在千葉高地掩埋了200名戰友的遺體,今天又邁著沉重的腳步來到了我的中隊。
收容俘虜的簡陋房屋是10天前完成的,寬1米,長50米左右,兩側是2米的睡床,只鋪了些新的乾草,光照不好,又不通風,是個粗陋糟透了的簡陋房屋。他們蓋著一床半毛毯渡過了夜晚。第二天還很疲勞迷迷糊糊地躺著的時候,氣勢洶洶的日下部中士帶著二名拿劍計程車兵怒喊而來:“哎,起來。今天就開始幹活。”
東北的冬天是寒冷的,刺骨的寒風從四面山丘吹來。“把石頭裝到車裡”淺川中尉命令俘虜搬石頭。他們都沒戴手套“冷啊!”誰也不願意,大夥相互看著。“都愣著幹什麼,裝石頭。看著,這樣幹。水田兵長戴著防寒手套抱起一塊石頭扔進車裡。然後他抓住一個俘虜,狠狠地打了一個耳光子,然後急忙走向下一輛臺車捱打的俘虜憤怒地盯著水田的背影過了一會才開始搬石頭。
“從頭一輛車開始,出發!!”4個人推著頭一輛車,沿著不規則的彎曲的軌道用力地推。到了下坡處,車飛快地向下衝去。長兵上等兵叫道“哎!一個人在這把舵剎住車,不讓車脫軌,明白嗎?”
4個俘虜緊張看著,“這簡直是殺人的路、太殘酷了”,一個年輕人代替3個小夥子用木棒作剎車,他們拼命剎住車,但車還是沿著軌道飛馳。其他俘虜也學著他們,一輛跟著一輛戰戰兢兢地推車。這可是個殺人的工地,稍不留神剎車斷了、脫軌了就會被撞死、輕者也是重傷。我滿不在乎地強制他們這樣幹。
4個人咯噔咯噔地推著車。在這一片溼土的地方什麼也沒有,更看不見人群。可是兩年前梅津司令官(關東軍司令官)就命令修一條10米寬的大道。為此2萬多中國人流血流汗。
沉悶的聲音伴著臺車走著,忽然臺車脫軌了。下村上士跑了過來,“壞了,怎麼搞的。為什麼不把車子推起來?”說著拿刀鞘向4個人的腰和背打去。兩個俘虜離開臺車盯著下村上士,下村上士向後退了一步。這時跑過來3個俘虜,一齊把臺車推上了軌道。這時騎在馬上的淺川中尉都看在眼裡“哎!快點,加把勁,”他怒吼著。
推臺車的俘虜已看不清下身是什麼樣的膚色了,盡是瘡痂。紅紅凍裂開的肉疼痛難忍,俘虜們拼命地推著車,不時傳來淺川中尉和跟在車旁監視計程車兵的罵聲。
艱苦沉重的勞動是把石頭運到12公里外的目的地。俘虜們卸完石頭就在寒冷的風中吃飯。有的披著毛毯,有的纏著水泥袋,高梁放在鏟子上在寒風中吃。日本兵戴著僅露出一點臉的毛帽子,穿著毛大衣在一間屋裡吃著熱呼呼的飯。
“哎,吃完飯的去割明天做飯用的野草”下村上士狼吞虎嚥地邊吃邊喊。“這傢伙把我們害到這種程度”,俘虜們氣憤地把目光投向了下村上士,拿著鐮刀在溼地裡割草。在風雪的吹拂下疲憊地捆好野草回到簡陋房屋已是晚上。晚飯是一個罐頭盒單盛的高梁,怎麼能填飽空空的肚子。晚上,俘虜們穿著薄薄的棉襖裹著一張半毛毯躺在野草上,忍著面板病和傷口的刺疼閉著眼推到天亮。
“今天給我們休息吧,張中校提出。鐮田中尉提出不可能的條件:“日程按預定的計劃遲了一點,明天你們可得把兩天工當作一天來完成。“那麼減少30輛臺車吧。你們也知道病人那麼多,又下著大雪。”“對我來講沒有減少的權力”,說著回絕了俘虜的要求。我以三義屯為根據地,10天左右才到工地一次,我對士兵說:“不要辜負了南方的戰友,看住這幫傢伙,讓他們快快地幹活,絕不留情。他們這些人的生命無關緊要。”我的話很見成效,無論天氣好壞,工具等其他條件如何,工程都能順利地按計劃進行。
我出生於貧苦家庭,因為不愛勞動才入伍的,所以很珍惜那領章和帽徽,希望經過我的努力得到恩惠,老年以後能有所安樂”,這也是我一生奮鬥的方針。為天皇、三井、三菱工作,或利用他人的勞動成果作為我自己的成績,為了能實現我的計劃,這些俘虜們過著怎麼樣的困苦和悲慘的生活我都無所謂。
就這樣60多個俘虜因營養失調和面板病變成了廢人。街上就是陸軍醫院。但我沒讓任何一個人去過,只是有時讓浜野衛生兵隨便給俘虜甸一下傷口。每週來一次的井本軍醫讓俘虜脫下衣服後發著牢騷看一下那些瘦得皮包骨的俘虜,然後連聽診器都不摸一下,就說“唔,好的”。
一天夜裡,簡陋房屋裡江蘇和安徽來的俘虜睜著眼睛死了。逃出這充滿憎恨、飢餓、寒冷、痛苦和疾病的辦法唯有死,要活命,只有一條路,就是冒死越過了警戒線,逃出了殺人的簡陋房屋。他們一一個也沒被抓到。這當然是一條該走的道路。我拿著報告在房間裡來回走著。不能再發生這種事了,我通報了虎林憲兵隊,然後又命令衛兵梅本中十和江藤下十加強警戒。
10天后的某一天,4個俘虜在虎村西邊的村子賣毛毯時被憲兵抓獲並遣送回來。我命令把他們綁在衛兵所的柱子上示眾,不給飯吃像狗似的綁在那裡,沒多久從軍司令官那傳來“死刑”的命令,我滿意地笑了,“怎麼樣殺呢?”我憎恨地想著用砍頭的方法,又怕砍卷刀刃。我命令淺川中尉槍殺他們。殺人是我最大的興趣。
“把那些俘虜全押來,讓他們見識見識,我瘋狂地叫,然後由淺川中尉指揮清武中士等7個人執行槍決,子彈咔嚓咔嚓地壓進了槍膛,這時一個俘虜提出了“摘掉眼罩再槍擊”的請求,我想“如果讓他臨死時看著我,會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不行,”我拒絕了這一最後的請求。
“隊長,已經準備好了嗎?”“好了,”“射擊淺川中劇發出命令後,7顆子彈射向了泰然自若面帶著對法西斯嘲笑的俘虜,俘虜們最後的高呼飄向了山丘。我走到4個俘虜的身邊,看見他們含著微笑倒在了血泊中,我感覺到他們死得很乾脆。我馬上又走回來,站在那些早已充滿憎恨和憤怒的俘虜面前,指著屍體惡狠狠地說:“今天起誰還敢逃跑,這就是下場。”然後匆匆地回到了軍官室。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我所在的第四五野戰道路部隊,對那些世世代代在富饒和平土地上辛勤耕種、與兄弟姊妹們一起和睦生活的人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殺害,殺死了21人,還有許多人成了廢人。這樣的罪行只不過是我所犯下罪行的一部分。我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混蛋?把接受帝國主義的宣傳當作自己的光榮和榮譽,而從不切身反思自己的一切行為呢?為什麼這樣不斷地慘殺無辜的貧民百姓?我對中國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