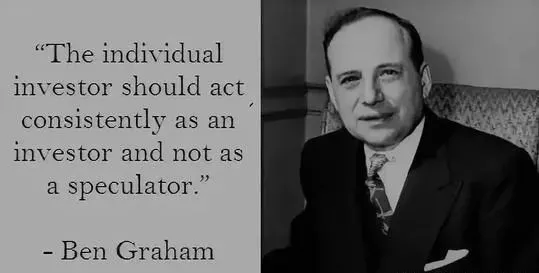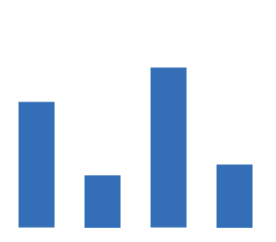來源:養基訓練贏
在很大程度上,《聰明的投資者》是一場大型勸退,格雷厄姆反對了大部分投資者想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以至於這本書字裡行間都像塞滿了各種“NO”:
不好意思,這個不能碰;對不起,那個是禁止的;不不不,那個也不可以。
他反對的事情包括:投機,短線交易,預測股價,追隨市場,不做估值,情緒用事,迷信專家,違反紀律,不學習不反省,過於集中/分散持股,等等。一個普通股民的大部分日常操作,在這本書裡都是禁止或疑問專案。
這種勸退的極致,就是格雷厄姆勸誡大部分讀者放棄做積極型投資,選擇當一名“防禦型投資者”。這實質上是在建議讀者放棄擊敗大盤,放棄積極選股,放棄盯盤,放棄預測股價,放棄頻繁交易——好吧,你在投資書籍、投資論壇上學到的很多炫目“技巧”,都是格雷厄姆不建議做的。
在格雷厄姆看來,只有少數人應該做積極型投資者,大部分人安心做一個防禦型投資者即可——這樣的策略,往往是買入一攬子的股票+債券組合,典型做法就是巴菲特整天唸叨的指數基金。
這實在是一件有點“匪夷所思”的事情,因為大部分人學習價值投資,都是奔著偉大投資者去的:找到牛股,擊敗大盤,創造N倍收益,但格雷厄姆卻致力於勸你放棄這種決心,同時立下諸多“掣肘”你的規則。
就好像一個新手俠客初入門派,很期待今天是學九陰真經還是獨孤九劍,結果練來練去都是太祖長拳,聽來聽去都是“江湖生存101條守則”。
問題是:為什麼格雷厄姆要這麼做?
1、真正的戰略思維都會清晰地勾勒“不為清單”。
格雷厄姆透過一次次講述“什麼是錯的”來表達“什麼是對的”。
正如邁克爾·波特所說,“戰略的本質就是選擇不做什麼”(The essence of strategy is choosing what not to do)。當談論戰略時,人們往往透過“做什麼”來定義自己,但實際上真正決定我們是誰的是“我們不做什麼”。
如果你很清楚你的目標客戶是誰,卻不知道該放棄哪一類客戶,這個客戶定位是不完整的;如果你很明白你要當價值投資者,卻不知道應該拒絕賺什麼錢,這個投資風格是不成熟的。
“什麼客戶都不放棄”的企業,實際上沒有經營戰略;“什麼錢都要賺”的投資者,實際上沒有投資體系。
相較於你的持股清單,你放棄的那些投資機會,更能說明你是什麼人。就算你持有茅臺,也未必說明你是一個價值投資者,反而是被你一次次拒絕的那些“賺錢機會”,更能詮釋你忠於什麼原則。
這就是為什麼《聰明的投資者》那麼多NO的原因——格雷厄姆先生傳授的投資戰略,就隱藏在一個個否定句式上裡。
2、價值投資的思維體系特徵就是“否定”,或者說是“排除”、“放棄”。
很多人會說,財務分析是用來排除公司的——實際上,不止財務分析,整個價值投資的體系都是用來排除“投資機會”的。
在此容我下一個大膽判斷:任何一本掌握價值投資精髓的書,都會致力於教導讀者要學會放棄,包括放棄什麼、如何放棄、為什麼要放棄——如果沒有,這本書的水平就很值得商榷。
如格雷厄姆在書中說,“我們在選股方面,主要強調的是如何進行排除——一方面,我們建議人們不要去購買品質明顯不佳的股票;另一方面,則建議人們不要去購買價格太高而且投機風險太大的高價股票。”
對於沒有興趣將投資視為事業的普通人,格雷厄姆直接建議放棄“選股遊戲”,理由是他們能投入的時間、精力和技巧太少,這樣還企圖擊敗大盤,無異於穿著新手裝就去挑戰大BOSS,不是飛蛾撲火又是什麼呢?
這就是價值投資的核心特徵:致力於規避損失(loss avoidance)、防範錯誤。卡拉曼說,“大多數投資方法都不注重避免損失,也不注重評估一項投資的實際風險與收益的比較。據我所知,只有一種方法是這樣的:價值投資。”
霍華德·馬克斯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將投資視為一場“輸家遊戲”,認為比賽獲勝的實質是看誰犯錯更少,“因此,防守——重點在於避免錯誤——是每一場偉大的投資遊戲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的思維發展到極致,就是巴菲特的“擊球理論”——只要球沒有落入你的最佳擊球位,你可以無數次地放棄、放棄、放棄,而不遭受任何懲罰,哪怕周圍的人都在喊“揮棒啊,你這蠢貨”,你也不需要理會他們。
棒球手會因為放棄太多而出局,但在股票的世界裡,你不會因為沒買股票而遭受任何懲罰——你見過有人因為沒買股票而破產嗎?
說到底,價值投資不是一個致力於博取最高收益的體系,而是一個致力於規避損失,保全自己,儘可能活下去的體系。
某個意義上,當你感覺自己“進退兩難”時,價值投資的建議往往都是勸“退”不勸“進”。
3、格雷厄姆不僅僅是一名投資者,還是一位好老師。
一般人參與股市是為了賺錢,格雷厄姆卻不盡然——他的使命不僅僅是賺錢,還包括撰寫價值投資的《聖經》,為股票理論大廈驅散縈繞在上空的兩朵烏雲。
一朵烏雲叫“賭博”,一朵烏雲叫“巫術”。
賈森·茲威格說,“在格雷厄姆之前,基金經理人的表現簡直就像中世紀的行會一樣,始終被迷信、猜測和神秘的巫術所左右,而格雷厄姆的《證券分析》則指導人們把這個烏煙瘴氣的圈子,轉變成一種現代化的職業。”
這是對格雷厄姆一生成就的精彩概括。沒錯,他是偉大投資者格雷厄姆,但他也是偉大教師格雷厄姆。
不妨想象下,如果:1、你經歷過1929年級別的股災/經濟危機;2、民眾普遍將股市視為賭博、陰謀詭計和撞大運之地;3、你要構建一個可供普通人使用的投資框架,甚至開創一個新學科。
你要如何為普通人寫一本投資書?沒人能做得比格雷厄姆更好了。
首先,格雷厄姆將“安全”放在最核心的位置。
如前文所言,價值投資的核心特徵力求“安全”、規避損失,投資者要始終將“保護自己”作為投資的第一要務,代表這一思想的核心詞彙是“安全邊際”——這是格雷厄姆歷經1929年股災後提煉出的智慧結晶。
將“安全”置於核心的意思是,你必須放棄很多、很多、很多看似“唾手可得”的投資機會——如果一個機會能賺大錢,但你根本看不懂,請放棄;如果一個機會能賺大錢,但你無法最大限度保全自己,也請放棄。
在變幻莫測的股票世界,如果你無法確保自己身處“安全環境”,你的心就只能捲入永恆的隨機性漩渦,禍福不定,喜憂無常。
其次,格雷厄姆質疑了一些錯誤但流行的投資方法。
如果你真的想要驅散那兩朵名為“賭博”與“巫術”的烏雲,那你就無可避免地要進入“戰鬥姿態”,公開挑戰那些錯誤的、似是而非的投資觀念。
格雷厄姆在書中質疑了多種投資方法,包括道氏理論、牛熊輪替、趨勢交易、預測(股價+短期業績)等等,就連今天流行的“賽道論”都曾受到他的質疑:
“具有明顯前景的企業,未必能為投資者帶來明顯的獲利”;
“即使是專家,也沒有什麼可靠的方法,可以從最有潛力的產業中挑選出最有前途的企業。”
這兩句話可視為格雷厄姆對“錯誤方法”或“錯誤心態”的終極勸告:
1、“告訴你不要投機,對我們而言十分簡單;但聽從我們的建議,對你來說卻十分困難。”
2、“像這樣掉以輕心的態度,難道不會受到懲罰嗎?”
最後,格雷厄姆只教“可傳授”(teachable)的東西。
如果一種投資方法很妙,但對悟性或天賦要求很高,格雷厄姆會持保留態度;
如果一種投資方法很好,但在操作過程中容易出錯,甚至引入覆滅風險,格雷厄姆會選擇避而不談。
在《聰明的投資者》一書裡,教師格雷厄姆只教 “值得傳授”且“能傳授的”的東西。
巴菲特在1995年股東大會上說,“格雷厄姆更像一個老師——他沒有想要賺很多錢的衝動,他對此不感興趣。所以他真的想要一些他認為是可教的東西(teachable),作為他的哲學和方法的基石。”
“他覺得你可以坐在奧馬哈讀他的書,然後應用——買統計上便宜的東西,你不需要對商業或消費者行為有任何特別的見解,或任何類似的東西。”——就這個意義而言,格雷厄姆實際上是在努力為讀者降低投資的難度。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聰明的投資者》裡看不到多少成長股投資、定性分析、集中持股、長期持股的原因。
4、尾聲
如果說《聰明的投資者》是一場對普通人的勸“退”,那格雷厄姆對專業人士的態度會有所不同嗎?
不,完全一樣——他依然是各種勸“退”,依然強調性格特質、堅守原則的重要性。
1974年,80歲的格雷厄姆在CFA協會的一次論壇活動上發表題為《價值的復興》的演講,他在演講最後對分析師們做了一些忠告——不妨就以此作為本文的結尾。
“讓我以一個經歷過許多牛市和熊市的80歲老者的幾句話作為結束語。
作為一個分析師,做那些你知道你能做好的事情,而且只做那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能透過圖表、占星術或你自己的一些罕見的、有價值的天賦來戰勝市場,那麼這就是你應該做的事。
如果你真的擅長挑選未來12個月內最有可能成功的股票,那麼你的工作就應該建立在這一努力的基礎上。
如果你能預言經濟、技術或消費者偏好的下一個重要發展,並衡量其對各種股票價值的影響,那麼就專注於這一特定活動。
(注:這基本都是格雷厄姆歷來反對的事情)
但在每一種情況下,你都必須透過誠實的、不欺瞞的自我檢查和對業績的持續測試來證明自己,你有能力產生有價值的結果。
如果你相信——就像我一直相信的那樣——價值投資在本質上是健全的、可行的和有利可圖的,那麼就請你奉行這一原則。堅持下去,不要被華爾街的時尚、幻覺和對快錢的不斷追逐帶入歧途。
讓我強調一下,作為一名價值投資分析師,你不需要天才,甚至不需要卓越的才能就可以成功。你需要的是,第一,相當好的智力(reasonably good intelligence);第二,健全的操作原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堅定的性格。
但作為金融分析師,無論你選擇哪條道路,都要保持你在道德和智識上的誠信(hold on to you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integrity)。華爾街在過去十年中遠遠沒有達到其曾經值得稱讚的道德標準,對其服務的公眾和金融界本身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70多年前,我在這個城市上小學時,我們要在作業本上抄寫各種不同的格言,第一句就是"誠實是上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現在它仍然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