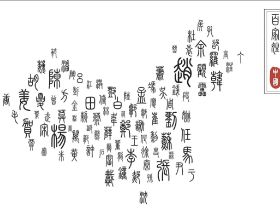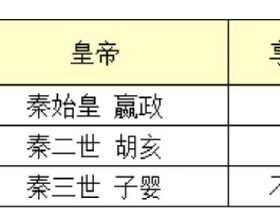人生世間,吃五穀雜糧,吃喝拉撒,樣樣必須。飯吃進去,吸收了營養,渣滓不出,清虛不來。人類有了文明,知道遮羞避醜,排除廢渣,得有廁所。
生產隊時,家家戶戶都有自己廁所,專一解決一家人大小便的地方。廁所是書面語和官方的稱呼,我們這一帶的農村,有叫毛司,茅房,茅坑,茅廁等叫法。毛司的叫法,大概在宋明時就有,《金瓶梅》第86回“令秋菊攪紙倒在毛司裡”,這裡的毛司,就是現在的廁所。
農民們廁所大部分搭在山牆頭,半撇廈,土坯牆,斷幾根檁條,再苫芭茅、稻草或搭幾塊石棉瓦。廁所後牆外,埋口大陶缸當茅池,與便槽相連。也有磚頭砌的茅池。若兩山牆沒地方,或不合適,毛司後院或恰當的宅基地上單獨建,結構和做法相同。
農村廁所只有一個蹲位,無男女之分,更沒有廁所門一說。若遇一個人正在解得暢快,另一個人來,裡面的人,只需咳嗽一聲,或嗯下,外面的人,會意迴避,轉回去等一會兒。擦屁股老農的磚頭,瓦塊,土疙瘩,婦女們用廢紙舊報,年輕的媳婦姑娘後來的一毛多一包的灰白粗糙的衛生紙,小學生們大多自己舊作業、舊課本紙張。城裡人如廁,也有專一的手紙。曾在一本書看到,中國兩晉時,貴族入廁,淨手用籌,是用竹子專一製作,不是一般百姓能享受的。
那時農村都是旱式的茅池,春秋冬在裡方便,還呆得住。最難受的是夏天,裡面臭味熏天不說,腳一踏入,轟的一聲,一群綠頭蒼蠅從糞堆上飛起,嗡嗡亂舞,碰人臉面。水火無情,只得硬著頭皮、憋住氣大便。正解得痛快時,一兩隻蒼蠅落於露出的屁股上癢癢的,頭皮發麻,用手驅趕,失急慌忙解了,倉皇逃去。遇到夏天下暴雨或秋後連陰雨,滿池滿槽黃濁的糞水,大便時,就要靠自己揣摩和把握準,否則,投彈會濺一屁股糞水。小朋友們,還好說,找個隱蔽之處,瞬間解決,但大人們內急時,卻不得不進廁所。
晴天,路過一個茅池,同樣驚起一群蒼蠅亂飛。一池的金黃色的糞湯,蠕動著一層白色的蛆,令人噁心。那時我想,這麼汙穢的東西,蠅蛆們卻甘之如飴,令人困惑。也許天生萬物,各有各的生存之道。莊子曾說道在屎尿。世界上大如高山,小如芥末,差別雖大,但蘊含的天地之間變化的深刻道理卻是一樣的。下暴雨,茅池雨水灌滿,糞水四溢,白蛆亂爬,濁臭四躥,如廁叫人無處下腳。
炎夏還是茅池的蛆蟲繁衍興旺的時候,有一個很形象的口頭語,稱之為“螞蝦魚娃亂汪汪,一個夏天長滿缸”。實際上,蛆是蒼蠅的卵產在糞便上變成的,蛆長成了一定時候,又羽化為蒼蠅。為了殺死這種蒼蠅和蛆蟲,大人或我們常常從野裡割的貓兒眼草,扔進茅池裡,貓兒草釋放一種毒汁,殺死蛆蟲蒼蠅,使這個骯髒而熱鬧的世界,安靜一段。
毛司雖然是我們小朋友怕去的地方,但也有找樂的時候。看到那個長得好看的年輕姑娘,特別是新媳婦入廁時,幾個調皮的小朋友,一起故意從毛司門口過,企望一睹春光。有次,一個來生產隊參觀的穿著時尚,年輕漂亮的年輕女隊員入廁,幾個小朋友裝著不知,闖入毛司門口,女隊員見是幾個毛頭小孩,大方地問道,你們小朋友,怎麼沒去上學?搞得他們一臉尷尬、懵懂,哪裡還顧得看“春光乍洩”?
雖然茅室是個令人討厭的地方,吃喝拉撒,卻是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只要還有一口氣,誰也不能免俗。在沒有化肥的年代,種糧全靠土肥,莊稼一戶花,全靠肥當家,社員把糞便看得稀奇。看到哪兒有泡禽糞,立馬撿回,扔在糞堆上。人糞看得更為金貴。往生產隊裡交土肥換工分,只交家禽糞,不交人糞,自己留下,自留地用。下地幹活,半晌歇息,離家近,解手還回自家廁所,這恐怕就是“肥水流外人田”諺言的來源吧。
我上中學後,暮春初夏時節,按母親的吩咐,放學後,閉著嘴巴,屏住氣,用糞舀子,從茅池裡掏出黃泥漿一樣的糞湯,氨味刺鼻,臭氣熏天,裝兩個半桶,一搖一晃地挑到自留地,澆灌在韭菜行,辣椒、茄子根上。幾天後去看,韭菜肥嫩墨綠,辣椒、茄秧茂盛肥壯。
時代在飛速發展。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多年,農民的廁所,由原來茅草棚,改為磚木結構,講究一點的,還安了門,分了男女廁所。
廁所的變遷,也是文明進步和提高的一個標誌。現在國家推行農村廁所革命,將旱式廁所改為水衝式,地面、牆面都貼了印花瓷磚,變得寬敞、明亮、舒適,一改過去簡陋,溼暗、骯髒的面孔,衛生條件,大為改觀。沒有了過去解手燻得頭悶,入廁不再是過去像一種軟刑,而是一種釋壓享受。名稱也變得文雅,上廁所叫去衛生間,洗手間,上大號,城市廁所門口標上簡寫的漢稱WC,廁所也體現出與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