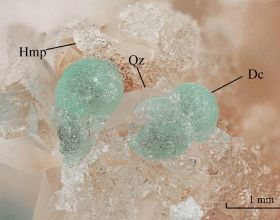上一章我們說過在晉武帝的“儲君之議”中各方勢力因為彼此的政治利益大致分為了兩派:
一方主張司馬衷是最合適的儲君人選,其代表人物是楊元后及其背後的楊氏家族、賈充之妻郭槐;另一方的則意欲將晉武帝胞弟司馬攸推上皇位,代表人物是張華、和嶠、李憙等。
雙方你來我往的爭鬥了十餘年,晉武帝雖然不願將皇位傳給齊獻王司馬攸但由於太子司馬衷智力上的硬傷而心儀皇子秦獻王司馬柬處在一個“爹不親孃不愛”無人支援的尷尬地位而搖擺了十餘年。
這十餘年裡晉武帝對齊獻王的態度則一直是兩派爭鬥的平衡點。而關於齊獻王因為有前車之鑑晉武帝對其可謂既用之亦防之。
比如在代魏之初齊獻王就曾受命作為全國軍事力量的總統帥。(《晉書·齊獻王傳》: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彼時的齊獻王權傾內外,位極人臣。而晉武帝之所以會這麼做我認為一是齊獻王的確有能力,二來則暗藏了晉武帝的小心思:特意做出寵信胞弟的姿態給王太后看。
齊獻王雖然推讓了哥
哥賜予的特殊恩禮但還是積極的參與到了朝政中去並且提出了不少善謀良策。(《晉書·齊獻王傳》: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
這種種表現都顯示出齊獻王為人精明強幹富於權謀並且正值壯年。因此在武帝諸子難當大任的情況下是極為合適的儲君人選。
但齊獻王越是如此晉武帝則防之愈深,特別是其在朝中深得人心的情況下。由此帶給晉武帝的憂慮和壓力可想而知。
不過在晉武帝踐祚之初由於文帝臨崩遺言尚猶在耳,文明太后仍在人世且新朝初立正是用人之時所以武帝對齊獻王還保持了一定的親善,顧及了兩人之間的兄弟情義和臉面。
同樣的因為齊獻王所帶來的種種壓力晉武帝雖然冊立了司馬衷為儲君但內心也在不斷猶豫徘徊,甚至在煎熬中自我麻痺。有個故事頗能論證我的此觀點。
《晉書·和嶠傳》雲:(嶠)後與荀覬、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覬、勖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
這段記載可以說非常生動地記述了晉武帝極其複雜的心境:所謂“明詔”即荀覬、荀勖二人說的“明識弘雅”,也就是說晉武帝是非常希望司馬衷真的如他所願的那樣“明識弘雅”是個智商線上的可造之材,是一個合格的儲君人選。
可這又不是事實。所以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理性與感性之間晉武帝迫切地需要外部傳達出與他內心所願相和的聲音來鼓勵他,支援他。
而和嶠不合時宜的實話實說則異常殘忍地擊破了晉武帝構建的脆弱的理想、夢境,所以晉武帝才會龍顏大怒不悅而起。
真正讓晉武帝下定決心力保司馬衷上位的恐怕是皇太孫司馬遹的逐漸長大。更確切的時間節點為公元281年,晉武帝平定東吳統一天下的第二年,即司馬衷被立為皇太子的十四年後。
司馬遹生於咸寧三年(公元277年),因為機靈聰慧甚為武帝所愛。
《晉書·愍懷太子傳》載:幼兒聰慧,武帝愛之,恆在左右。
不僅如此對於這個皇長孫武皇帝可謂絲毫不吝溢美之詞,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對他的器重和讚譽:(帝)謂廷尉傅袛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晉書·愍懷太子傳》。
有這麼一個未來可期的孫兒無疑令晉武帝看到了讓自己的血脈穩坐江山的希望。
而公元281年發生的另一件事兒無疑對穩固司馬衷的儲君之位起到了定海神針的重要作用。這一年愍懷太子五歲,某天夜裡宮中突然發生大火,晉武帝登上閣樓觀望。此時愍懷太子卻拽著晉武帝的裾袍將其拉入陰暗處。
對於小孫孫的這個舉動晉武帝感到非常詫異所以就問愍懷太子為什麼要這麼做。愍懷太子答道:夜裡宮中突然失火事發倉促,萬乘之君應該時刻防備異常的事情發生。
《晉書·愍懷太子傳》:(太康二年)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暗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促,宜備非常,不宜令照人君也。由是奇之。
此次事件的發生讓晉武帝對這個小孫子更是刮目相看。也更加堅定了未來社稷交到愍懷太子的手中,雖然中間還隔著他痴憨的父親。
如果說這還不能令人信服的話我再列出幾個例子。其一:①在晉武帝駕崩的前一年有人說廣陵有天子之氣,武帝便將愍懷太子冊封為廣陵王,食邑五萬戶。(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晉書·愍懷太子傳》)。
此為晉武帝逝世前最後一次大規模分封、改封皇室成員,意義極為重大,而將愍懷太子的封地設定到有“天子之氣”的廣陵則是其中一個極不尋常的重要訊號。
結合晉武帝此前的種種言論其目的至少有二。一方面是愍懷太子的確出眾,另一方面則是晉武帝要告訴眾多反對司馬衷的朝臣自己此時堅持不換儲君更多的是為愍懷太子將來繼承帝位鋪平道路。
②愍懷太子司馬遹於公元290年八月,即惠帝登基僅僅四個月後便被立為皇太子,皇儲身份確立之速也是事出有因,何者?此乃惠帝遵奉了晉武帝臨終時的安排。
《晉書·愍懷太子傳》之復皇太子之位策文載: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則明確指出了晉武帝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惠帝之臨天下,不過為愍懷守位耳。但顯然武帝的這一設想太過理想化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政權能否從司馬衷手中安穩的過渡給愍懷太子。
其二則是晉武帝對待反對司馬衷的朝臣的態度。晉武帝乃精明強幹之君,此前對於要求改立儲君的朝臣其自然也知曉他們是出於公心所以儘管心中不痛快但也併為嚴加苛責甚至懲罰。
然而在公元281年之後晉武帝在此事上卻一改往日寬厚之風突然性情大變,利用荀勖、馮紞等賈充一黨以強硬的鐵血手腕及史無前例的懲處力度對擁護支援齊獻王的朝臣們做出強硬回擊。
【關於荀勖、馮紞讒言齊獻王的緣由,一方面是荀勖馮紞為賈充死黨,二來荀勖、馮紞以諂媚得晉武帝之寵為齊獻王所不容,懼怕將來齊獻王掌權對兩人不利,故欲齊獻王就藩以絕朝臣之望,這在太康初年這個特殊時期正中晉武帝下懷所以便順水推舟借力打力。】
據《晉書·武帝紀》所載:(太康三年)春正月甲午,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張華的這次外放究其原因是此前晉武帝問張華自己百年之後誰可以做託付之人。而張華是齊獻王堅定的支持者便實話實說觸怒晉武帝,加之荀勖、馮紞藉機讒言晉武帝便對張華做出的打擊報復。(《晉書·張華傳》: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
【關於這個“可託後事者”我認為有兩層含義:一是江山之託付,即被託付者繼承江山社稷成為新的皇帝;二是新君之託付,即被託付者為顧命輔臣。從後來張華的政治思想的巨大轉變來看此處我本人更傾向於武帝所指張華所答皆為後者。但即便是讓齊獻王成為顧命大臣也是晉武帝所不能接受的】)
雖然後來張華被召回京但自此終武帝一朝其也徹底喪失了參與朝政的資格。(《晉書·張華傳》: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由此可見張華為此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沉重,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不可謂不深刻,而這同時也可以看做是晉武帝殺雞儆猴對支援齊獻王朝臣的一次警告 。
在敲打了朝臣一番後晉武帝緊接著便採納了荀勖馮紞的建議責令有關部門制定禮儀開始著手準備遣送齊獻王就藩的事宜,卻不曾想這一舉動遭到了朝中大臣們的強烈反對。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當朝勳貴,滅吳主將之一的王渾、王濟父子、李憙、劉暾(tun)、曹魏後裔曹志、晉宗室扶風王司馬駿等等。他們各顯神通運用各種手段妄圖令晉武帝收回成命。
本想有了張華的前車之鑑朝臣們會識相的遵從聖意,遣送齊王攸就藩之事會順風順水的晉武帝怎麼也沒有料到齊王在朝中的擁躉們會如此油鹽不進再次給他帶來如此巨大的阻力,因而武帝心中積壓的怒火也就可想而知了。
《晉書·曹志傳》載: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這個“等”指庾純子旉,太叔廣、繆蔚、郭頤、傅珍及史書未全部記載的人)以為齊王宜內匡朝正,不可之藩……乃奏議曰:“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鄄城縣)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
此事《晉書·庾純附子旉傳》記載的更為詳細:齊王攸之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lue)等奏:“旉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是議主,應為戮首…秦秀、傅珍前者妄虛,幸而得免,復不以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兇慝(te),猶復不忍,皆免其死命,秀、珍、旉等併除名”。
這段記載說明了當時負責禮儀制定的太常是反對齊王就藩的橋頭堡陣地,如果細究此次事件裡也夾雜了不少“私貨”,即“正臣”與“佞臣”之間的較量、纏鬥。
何者?前文所述晉武帝乃利用荀勖、馮紞與齊獻王之間的矛盾順水推舟、借題發揮來打擊後者;而荀勖、馮紞一向黨於賈充,乃賈充的爪牙。上述名單中秦秀“性忌讒佞,疾之如仇,素輕鄙充”;劉暾“父毅疾紞奸佞,欲奏其罪,未果而終”(皆見其本傳),雖未明見其與張華、任愷、庾純、和嶠等人相善,但至少在反對賈充、荀勖、馮紞為首的佞臣這件事上他們的政見是一致的。
此次事件若成功留下齊獻王(或者說此舉能讓司馬攸留京執政甚至是登上皇位)張華、庾純、和嶠等正臣勢必會受到重用並藉機懲治賈充佞臣一黨;而若將齊獻王逐出京城並藉此來打擊誅戮朝中“正臣”,無疑則會讓佞臣一方在將來的政治鬥爭中佔據優勢。這也正是劉頌急切的想要報請廷尉誅殺秦秀、庾旉等人的原因。
精明如晉武帝自然也看出了其中的門道,所以他才會“奏留中七日”,然後雷聲大雨點小的對秦秀、庾旉等人法外開恩僅做免官除名的懲治。(而被除名的諸人在不久後便又被武帝陸續起用)。故此番決策必然是他經過了深思熟慮後的決斷,這也更加說明了晉武帝此舉主要是針對齊獻王的發難。
太常博士諫齊獻王歸藩是朝臣借用政府機構層面帶給晉武帝的阻力,除此之外還有個人層面的勸諫,這裡也能看出晉武帝與朝中大臣就此事交鋒的有多麼激烈。
如:《晉書·向雄傳》載曰: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這段記載有幾個細節:一是“固諫”,說明向雄不止向武帝諍諫了一次而是多次並由此引起武帝不滿,即所謂的“忤旨”;二是“起而徑出”這在等級尊卑觀念極強的封建社會是異常失禮,甚至“目無君上”的欺君行為,而此行為往往潛藏著丟掉身家性命的巨大風險。何況向雄在西晉王朝是個既無高位又無殊勳無足輕重的人物,敢這麼做是需要十足勇氣的。
向雄不是唯一因為諍諫齊王歸藩憂憤而亡的,與之相比另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也在此事件中絕命而去,那就是武帝的叔父——扶風王司馬駿。
扶風王司馬駿乃宣帝第七子,《晉書·宣五王傳扶風王駿傳》說他“幼聰慧…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儁望”,自八歲時歷任軍職,武帝踐祚後受封為汝陰王,邑萬戶,先後鎮守壽春、許昌、關中。咸寧初年(公元275年)平定羌虜樹機能之亂後入京,同年以功改封扶風王。
這履歷今日觀之亦可謂光鮮亮麗,然而就是這麼一位有名望,有身份,有功勳的親王在得知齊獻王要被責令就國後不遠萬里上疏切諫,晉武帝依然冷麵駁之,最後老王爺在羞憤之下發病而亡(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見其本傳)。
然而這還不算完,我前面說過眾臣為了勸武帝收回成命可謂用盡了渾身解數。前面提到的王濟不禁自己上言規勸還多次搬出婦人到武帝面前哭訴,企圖打動武帝在此事上的鐵石心腸。
《晉書·王濟傳》載:齊王當之藩,濟既陳情,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桑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忤旨,左遷國子祭酒。
透過上文論述我們不難發現此次由晉武帝保立太子而引發的“齊王歸藩”在武帝朝絕對算得上排名前三的重大事件(個人愚見:終晉武一朝凡大事者三:其一立晉惠為儲;其二平滅東吳;其三即為此)。
而這番政治鬥爭的結果亦可謂慘重:齊獻王、扶風王、向雄因此事相繼憂憤而亡;張華因此事斷送了自己在武帝朝的政治前途;十餘位參與此事的朝中大小官員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懲處,甚至險些丟掉性命;此事件中“正臣”集團因為皇權對“佞臣”群體的加持而再次遭遇挫折,失敗。
如今我們回過頭來再去分析會發現在這場鬥爭中其實沒有真正的勝利者,儘管武帝由此徹底穩定了痴兒司馬衷的儲君之位,儘管在惠帝登基之初的日子裡楊賈聯盟暫時掌控了朝局,哪怕這脆弱的聯盟很快變成了對彼此血腥的殺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