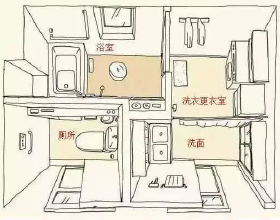2001年,郭寶昌導演的電視劇《大宅門》熱播。在此後的20年裡,《大宅門》的光彩並未因時間而褪色,反而在越來越網劇化的電視劇領域不斷吸引年輕觀眾,密集的鑼鼓點、蒼涼的胡琴聲,也總會“盤旋”在B站少年們的移動終端上。20年來,《大宅門》有了自己的三代觀眾,實在了不起。劇中白景琦在劇情關鍵處愛念的“看前面黑洞洞,待俺趕上前去,殺他個乾乾淨淨”(京劇《挑滑車》),在今天就像接頭暗號,成為觀眾們見了郭寶昌最愛聽他念,也最愛和他一起唸的一句響噹噹的臺詞。
2021年,一部關於京劇的通俗理論著作《了不起的遊戲》出版。做了半輩子影視導演的郭寶昌要寫京劇方面的書,是“因為京劇太美,割捨不下”。如果說在電視劇《大宅門》中,郭寶昌是以一種“反潮流”的態度,將傳統藝術強行地“植入”現代影視——這一創舉不但讓電視劇有了文化厚度,也讓京劇這種傳統藝術有了現代神采;那麼,寫這部書,郭寶昌同樣“反潮流”:他反的是一提京劇理論“動不動就什麼斯基,什麼耶夫的嚇唬人”。他說,他要用中國人自己的語言,說中國人自己的事兒!
用一本書把京劇的美展示出來,郭寶昌是有底氣的。他5歲開始看京劇,看了70多年,70多個流派創始人的劇目,他在現場看了有40多個。這樣一份驚人的看戲記錄,使得他更容易感知用西方戲劇理論討論京劇的種種不適。當然,他能寫這樣一本書,並不僅僅因為他看的戲多、思考的時間長;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從進入藝術實踐至今,就從來沒有動搖過。
20世紀50年代,蘇聯斯坦尼表演體系盛極一時。在其強大的“體驗學派”面前,即使梅蘭芳都猶猶豫豫地說自己的表演也算“體驗”吧。但當時在電影學院導演繫上學的郭寶昌卻有疑問:同樣是無實物表演,京劇《花田錯》裡面搓麻繩、納鞋底,表現的是動作的美啊;斯坦尼的無實物表演,是要訓練演員在舞臺上集中注意力。同樣的無實物表演,兩者內涵完全不同,怎麼能用“體驗”去硬套呢?20世紀80年代,郭寶昌開始拍電影。在向西方學習的思潮中,他在拍完電影《霧界》後發現:現代光影技術所能呈現的時空,並不比京劇舞臺更自由。在當時,“寬銀幕”是被認為最能呈現空間的無限性;可他發現,戲曲舞臺的邏輯是人的心中有宇宙——因為這個邏輯,演員在舞臺上跑個圓場,觀眾就可以理解為他跑過了萬水千山;而電影再怎麼展現,都是用鏡頭去捕捉“宇宙中的個人”,銀幕再怎麼“寬”,時空都被鏡頭限制住。因此,在那之後,雖然以歐美為代表的強勢現代技術、藝術觀念在20世紀90年代全面擠壓中國文藝,郭寶昌反而能在電視劇《大宅門》中帶著中國美學風格強勢迴歸。
郭寶昌對於傳統文化的自信,不僅體現在他將傳統美學引入現代藝術載體,也體現在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傳統藝術創造性發展的探索。在拍攝完電視劇《大宅門》之後,郭寶昌對於傳統藝術如何進入現代生活、現代技術如何表現傳統藝術的實踐就沒有停止過。2005年,郭寶昌拍攝了程硯秋的代表劇目《春閨夢》。為了在電影上呈現京劇舞臺藝術的特點,郭寶昌上來就將《春閨夢》的角色從原來的12個刪成了兩個;在攝影棚中,攝影師侯詠用純手工的電影美術,重新在膠片上創造出了京劇的舞臺感。而電影中讓人震驚的畫面比比皆是。比如,十幾個武生演員是在高撥子音樂伴奏、在杜甫“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的詩句中集體起霸的。這不僅是中國京劇從來沒有過的場面,而且用簡潔的電影語言創造出氣壯山河的景象,放到世界電影中也是精彩畫面。
對中國文化的堅定自信是郭寶昌一生創作的貫穿性線索,而豐富的創作實踐又是他對京劇理論總結的基礎。在《了不起的遊戲》裡,郭寶昌把他的文化自信落到了更為艱難的理論寫作中——自信,在這裡轉化為對傳統文化的自覺。《了不起的遊戲》是郭寶昌從他多年來藝術實踐出發,在對成百上千齣戲的細緻分析、對梨園行各種掌故反覆思量的基礎上,用“遊戲”作為一個核心概念來討論京劇。
在民族復興的潮流中,《了不起的遊戲》從京劇出發所展現的文化自信,只是這個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在這個潮流中,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作者在不同方向上有不同的理論建樹。尋找中國人自己理論語言的嘗試,並不只是為了證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性,而是以更清晰的語言,把中國的藝術精神講給世界聽。
(作者:陶慶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